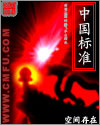中国一九五七-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饭端到一张空桌上。吕浩明说那天我提的那个建议你们研究了吗?他指将《大地》纳入绿叶文学社的事。我说大伙议了议,不大赞成。他停止咀嚼,盯着我问为什么?我说也不为什么。吕浩明不语。我说目前情况下文学社要办份刊物是很容易的事,何必一定要接收《大地》呢?吕浩明叹口气说你不知道我非常喜欢“大地”这个名字,涵盖量很大。我说叫“绿叶”也相当不错嘛。吕浩明摇摇头说“大地”气势磅礴,任何别的名字都无法与其相比。这一点我倒不否认,那天我们想到这个名字时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吕浩明直言不讳地推崇“大地”的“响亮”使我颇为自得,也多少有些歉意,似乎是自己将一件大家都看好的东西抢先装进口袋里。出于安慰我重复我的前言:其实“绿叶”也是相当不错的。吕浩明看着我说你要真的觉得“绿叶”不错,我拿它换你的“大地”可好?我压根儿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哑口无言。吕浩明又说一句换一换怎么样?
正这时程冠生端着饭过来了,见我和吕浩明俱一副不自然的神情,问你俩这是怎么的啦?我没吭声,主要是不想使吕浩明尴尬。因为我知道程冠生会怎样回答。不料吕浩明自己把用“绿叶”换“大地”意思给程冠生说了一遍,我方明白他的这一想法是执拗的,他又想游说程冠生。我想他是失策了,果然程冠生听了用刚放下饭碗的手拍拍吕浩明的肩膀,讥讽说吕会长如此精通交易之道,何不拿你的会长头衔去换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头衔呢?这才是大有气魄啊。吕浩明变了脸色,朝程冠生嚷道你程冠生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当了个副主编么?我倒要奉劝你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宗派主义时要警惕自己犯宗派主义的错误。说完端起碗悻悻离去。我和程冠生互相看看。我明白吕浩明所说警惕犯宗派主义错误的话不仅针对程冠生,更针对我。“收编”《大地》未成(也包括交换未成)使他心存芥蒂,但他为什么就不想想他有什么权力如此强加于人呢?对此倒应该奉劝他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时也要警惕自己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啊。程冠生说你何必要和他这样的人搅到一起呢?我相信你不是为个什么副社长头衔吧。我苦笑笑,无话可说。在这种时刻说一句符合客观又不失表白的话是不易的。不便说的话只能压在舌头底下。
我说S大田野来演讲我想听一听,你呢?程冠生说他也想听一听,百闻不如一见嘛。我说那就下午再去印刷厂下稿吧。程冠生说这样好,可以加一则田野来K大演讲的消息及有关反应的文章。我说就事件而言是应该的,只是版样已经划好,再做更动是挺麻烦的事。程冠生说改改看,不行就加个插页。我问你是说加个号外?程冠生说叫号外也可,叫特刊也好。我疑虑说作为号外出现是否太郑重了?太夸张了?程冠生说我不这么看,在当前形势下田野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们应该做她坚强的后盾,不能让她单枪匹马地和那些老左们干,老左们四处散布她的演讲背离了社会主义,说她是反革命,真是岂有此理。我说要不等听过她的演讲再定吧,这样有的放矢。程冠生突然想起什么,说周文祥我还有个想法。我说什么想法?他说我听说田野手里有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可以向她借用一下,在特刊上一起刊出来,影响一定很大。我听了一下子冲动起来,说这样好。想想又说这份报告属党内高级机密文件,田野怎么会有?程冠生说田野的男友是胡耀邦的秘书,她从男友那里得来。我说我们和她没有什么关系,未见得她会给。程冠生说相信她会给的,不给她就不是田野了。我说假若不给的话也有办法,可以去资料室翻英文报纸,听说纽约时报曾发表了这篇文章,找到请人翻译出来就成。程冠生说对。走出食堂程冠生问我去教室还是回宿舍,我说去女生宿舍找冯俐。程冠生笑笑说看来你们已到密不可分的地步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耳。我说没这么严重,我找她有正经事。程冠生说恋人之间还分得出正经不正经的事?比方亲亲嘴是不是正经事?我说要亲嘴也不能大白天去找人家亲呀,我去是让她参加今天的田野演讲会。程冠生说看来你很希望冯俐能成为K大的田野。我说净胡扯,她成不了田野,我也没这个奢望,我只是希望她不要在这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落伍,如此而已。程冠生说既然这样何不让冯俐去找报纸并且翻译出来,以此把她拉上战车。我一听觉得程的意见可取,便答应去同冯俐讲。
没找到冯俐,给她留个字条在铺上。去教学楼的路上碰上系总支书记范宜春,范知道《大地》的事,问什么时候能印出来。我说今天下厂,一周后差不多就能出来。范说出来一定给他一本看看,他说尽管他没参与,可毕竟属中文系的整风成果。我听出他的态度与以前有很大的变化,这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党组织态度的变化。我问范对田野演讲怎么看,提倡不提倡师生们参加。范说校党委对田野来演讲原则上不反对,系总支也是这个态度,师生们参加与否也不予干涉。我问他本人是否参加。他说他和孟广琦要为下午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做准备,就是想参加也参加不成了,可能会委派几位同志去听一听。我向他询问可否列席下午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他说你作为《大地》的主编可以列席。
教室里十分热闹,全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在,有的在写大字报,有的在争论问题,问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否是一桩历史冤案。见我来了有人立刻让我发表见解。我连忙挥手说我还有事恕不参辩。离开教室回宿舍拿记录本,准备记一下田野的演讲要点。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躺在床上看书。自从停课,李德志的全部生活是两点一线(从宿舍到食堂)。
别人风风火火投身运动,他优哉游哉当逍遥派。我从心里有些瞧不起他。我故意大声嚷:李德志起来。他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到我身上,问:到午饭时间了吗?我又好气又好笑,说刚吃了早饭又想午饭,你快成了酒囊饭袋了。他不在意我的讥讽,又重新看起书来。我说快别看书了,和我一块去听田野的演讲吧。李德志哼了声说她出的啥风头呢,迟早要倒霉的。我挖苦说这也是你那劳什子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么?他说不错。我说你没推导自己是什么结局呢?
他说推导了,同样倒霉是结局。还有你,你也是。我说去你的。
·3·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四
这天是腊月二十三日。在北方这是一个节日:小年。犯人有点像小孩子,盼着过年过节,既然不能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也是心中切望。老监号崔老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交底说狱方并不把小年当节,伙食照旧。这让大家很是失望。但这一天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在公平使用那缕阳光的问题上两个犯人发生了争执,等候的那个犯人说已经到了他照射的时间,而正照射着的那个犯人说时间还不够,先是唇枪舌剑,而后便扭打起来,如这类事情的所有结局一样,是崔老将这场战火熄灭。接着的一件事是管理员进来宣布今天有外国友人来参观监舍,交代了一些必须遵守的事项,如外国友人进来后不许乱说乱动,要有礼貌面带笑容。还有,事先要清理监舍和个人卫生等等。外国友人是安排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进入监舍的,在这之前管理员抬进了纯玉米面窝头和炒鸡蛋,交代说必须吃得文明,不许抢,谁在外国友人面前丢人现眼就处罚谁。犯人们盯着放射着金子般颜色的饭菜,眼光也像金子般贼亮,不动声色地快速往肚里吞咽。一会儿几个深褐色面膛的外国人在监狱一干人等的陪同下进到监舍(后来知道来参观的人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随从),参观的过程是极其短暂的,友人们站在门口朝正吃饭的犯人友好地笑笑,赞许地点点头,便转身出门,往别的监舍去了。大门刚刚关闭,只见姓曲的地工倒在地上直翻白眼,脸憋得青紫,一看这情形就知道是叫饭噎住了。几个人撂下碗筷奔过去,把他扶起来给他揉胸抚背,却不管用,眼见得地工的眼珠一点点鼓出眼眶,崔老吆句快报告管理员,就立刻有人高喊报告。管理员恼怒道好饭好菜也堵不住你们的嘴么?!等他知晓是有人快让好饭好菜堵死了,就命令将人抬到医务室去抢救。就抬走了。没过多会儿,管理员回来黑着个脸宣布:帮曲文曲把东西收拾收拾。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坐过监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管理员宣布给某人收拾东西,这人就已成了死人。曲地工没有抢救过来,死了。管理员走后人们议论起来,大部分人的见解是曲地工临死做了个饱死鬼,不冤。这种话用在别人身上很无情,可用在曲地工身上倒也说得过去。因为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曲地工确有些惊世骇俗。每每吃过饭后他便把吃下的饭从胃里倒回嘴里,做第二次咀嚼吞咽,像牛反刍那般。他的理论是这般在感觉上是吃下了双倍数量的饭。无论如何,对于曲地工的死我感到很难受,我是头一次看见一个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成了死鬼。而且死得这么“他妈妈的”。
近些日子狱方加紧了审讯,犯人像跑马灯似的往审讯室跑。24号监房又转走几个犯人,转北京监狱,没有放回家过年的。补进来的犯人中有个姓陈的整天哭哭啼啼,一口一个冤枉,惹得大家心里很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孝子。孝子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很感激崔老,不时以胃口不好为由将自己窝头掰一半给崔老。崔老自然能体会他的心情,每回都坚辞不受,并开玩笑说这里的人什么病都能得,就是不能得没胃口的病。不知什么原因,对孝子的审讯很是频繁,顶多隔一天便审一次,每次回监房情绪都极其低落,有时还面有泪痕,像在审讯中受到严酷折磨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