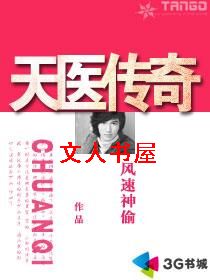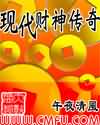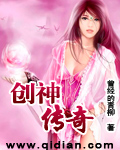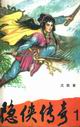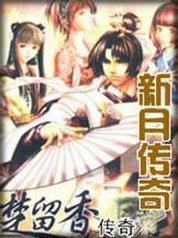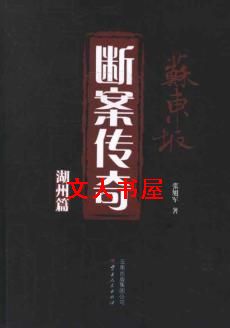传奇未完:张爱玲-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俏蘅赏旎氐拿宦湟约爸种终踉欢甑牟恍揖质顾敛涣羟榈乇摅鬃耪饷宦涔笞宓摹扳觯芽埃孀拥那保谑恰安粤埂背晌洞妗沸∷档淖苤魈狻�
不同于她的家族小说,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色,戒》,也被认为是“有所本的”,香港学者兼影评家陈辉扬在其《梦影录》一书中就说:“我一直认为《色,戒》的材料来自胡兰成,因为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故事,是根据郑苹如谋刺丁默邨一案而写成的。其中种种细节,只有深知汪精卫政府内情的人才能为张爱玲细说始末。”
而张爱玲在一九八三年由皇冠出版社集结《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多少恨》、《殷宝滟送花楼会》、《五四遗事》和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为《惘然记》一书出版时,曾在序中谈到《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由此可见她非常喜欢这些自外界获得的材料,并且从一九五年左右就写成,期间又经过三十年的改写。至于她没有提及材料得之于胡兰成,甚至在《色,戒》发表后的同年十月一日有署名“域外人”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一文的严厉批评时,张爱玲在一个多月后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的反驳文章,亦没有提到“胡兰成”三个字,只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几句话避重就轻地带开。这是由于张爱玲和胡兰成分手后,“胡兰成”三个字,似乎在张爱玲的记忆中清除。
“最是伤心终无言”,胡兰成对张爱玲的伤害,正如曼桢在《半生缘》中的感受——“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姐姐,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世钧这样的使她伤心。”在当时张爱玲的心境恐怕是“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胡兰成这样的使她伤心”。因此即使最亲近的友朋如宋淇者,都避谈胡兰成的事,在张爱玲面前,胡兰成是谈话的禁区。也因此张爱玲没提及材料得之于胡兰成,实不愿再触及情伤及因胡兰成而再度遭致“汉奸”污名的攻讦。张爱玲虽然在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两年内,红极一时,但在抗战胜利后,虽然没有被南京政府正式定为“文化汉奸”的罪名,但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文学活动甚至于私生活,都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一年多,她甚至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而事实上也没有机会让她发表。直到同年底,张爱玲借《传奇增订本》的发行,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做了辩白: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小说网·。。]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张爱玲以退为进,反驳了“文化汉奸”之说。同理,她在面对“域外人”指控《色,戒》为“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的论调时,她又再度地反驳:“域外人这篇书评,貌作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任意割裂原文,与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错会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对“域外人”提出严厉的质疑。由此可见她不愿再被任何污水所溅污,即使仅是那么一点点,她都不愿意。
然而《色,戒》绝无任何歌颂汉奸的味道,即使是暧昧的,它只借着这个有关汉奸被暗杀未遂的真实故事,来重写女性对感情的看待。这其中的种种细节,正如陈辉扬所说的,只有深知汪精卫政府内情的人才能细说始末,而活跃于汪伪政权中,曾任伪中宣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就成为张爱玲获得这令她震动的故事的不二人选。因为自一九四三年底胡兰成从苏青主办的《天地》月刊中,读到张爱玲的《封锁》时,他读其文而惊其才,透过苏青得知张爱玲的住处而找上门去,在次年二月初两人初次见面,其后两人很快坠入情网,并于同年八、九月间结婚。
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张爱玲曾悄悄到温州看望逃离中的胡兰成,但风流成性的胡兰成却又另有新欢。张爱玲在伤心之极回到上海,她在雨中的船上“面对着滔滔黄浪涕泣久之”。次年六月十日她写信给胡兰成,两人正式分手。在这短暂的热恋与婚姻生活中,他们有过两情缱绻、无话不说的时刻,胡兰成向张爱玲说出这段故事的细节,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而有关于郑苹如谋刺丁默邨一案,最早披露的是六十年代金雄白在香港出版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的一小节,笔者参考了李伟、黄美真等人的多种史料,发觉此一暗杀事件,除了中统锄奸以外,还得从丁默邨与李士群两人的恩怨冲突说起。
丁默邨是湖南常德县人,生于一九零一年,幼时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未能考入中学。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年轻气盛的丁默邨只身前往上海闯荡,积极参加青年学生运动,经由施存统的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他回湖南筹建常德团组织,并自任组长。同年十月十三日社会主义青年常德地方执委改选,丁默邨担任团书记,而在次年改选时,他却失去书记一职,对此他极为不满,并与新领导人闹翻。次年一月他谎称去长沙汇报工作,其实是远走上海,叛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二六年他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办事员。次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认为时机成熟,便积极投靠蒋介石,追随陈立夫、陈果夫的“CC派”。一九三二年他担任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小组组长,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他与李士群等在“万春坊新光书局”编辑《社会新闻》,先后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是当时国内有名的“造谣”刊物,曾多次污蔑诋毀鲁迅,相关资料收在鲁迅《伪自由书·后记》中。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日。幼年在本乡私塾读过几年书,二十年代初进入了日本人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后又转入上海大学读书,此时他生活来源主要仰仗妻子——大夏大学学生叶吉卿,由于叶家有钱,使得李士群生活无忧。这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后又转苏联特种警察学校。
回到上海的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分,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但不久他却为公共租界工部巡捕房逮捕,为了怕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妻子叶吉卿找到恒丰钱庄的韩杰,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由季云卿通过巡捕房里的熟人,将他保释出来。后来他便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从此李士群与青帮拉上关系。
一九三一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以上海为重,活动非常活跃,共产党组织屡遭破坏。一九三二年,李士群又被调查科逮捕,他眼见地下斗争处境艰难,再加上自己贪生怕死及老婆不断地施压,就向国民党自首了。起初他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就调去与丁默邨、唐惠民等编辑《社会新闻》。
一九三四年调查科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同年蒋介石为了统一特务组织,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丁默邨当上了第三处(邮电检查处)处长,与戴笠(军警处处长)、徐恩曾(党务处处长)齐名。抗战前,他一直在蒋介石手下任职,抗战开始后他曾在汉口奉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而由于戴笠对他的嫉妒,向蒋介石控告他贪污招待费,使他遭到追查。一九三八年八月调查统计局第一、三处遭撤销,丁默邨失去职务,仅在军事委员会挂了少将参议的空名,因此他闷闷不乐,托词到昆明“养病”。
李士群则在一九三三春因国民党调查科上海区长马绍武,遭共产党中央特科“红队”的伏击毙命,使他和丁默邨因嫌疑犯被捕。但丁默邨因有“CC派”的高级干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力保,很快就被释放了;而李士群因没有靠山,被解押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后经他老婆叶吉卿“赔了夫人又折财”的营救下,走通了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李士群虽被释放,但仍然被规定不得擅离南京。
不久,李士群被指派为调查科编译股编译员、南京区侦查员。一九三三年底开始,他担任“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从此郁郁不得志,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占领上海,为了扫除侵华道路上的障碍,决心建立一支汉奸特工队伍,做为消灭上海抗日力量的先遣部队。于是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