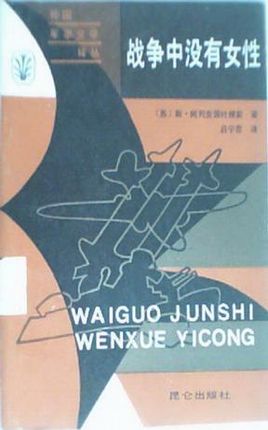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牺牲的激情。尽管,中央苏区的一切还带有新事物初创时的幼稚、简单,甚至概念化的特征,尽管父亲自己也对它的许多“左”倾极端的现象予以抨击,但它毕竟是人类大同的雏形,毕竟显现了人类追求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理想光辉。
我给父亲读报,念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后来我才知道那篇文章是断章取义。
正因为一生怀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父亲一生都唾骂争权夺利、以权势谋私利的政治小人;一生都鄙视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封建皇权意识。“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他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张劲夫同志撰文写道:“我和爱萍同志交谈过,我们当初找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都很简单明了:一是不当亡国奴,二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注:张劲夫《平民将军》)
南街村,或许只是个幻影,或许它会被周围市场经济的大潮所吞没,但“共同富裕”这一点,却让父亲那颗日渐衰老的心感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在别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甚至不可理解,但在父亲却是那样渴望和珍惜。
或许,这就是他的梦。
我记得父亲曾说过:“中华民族振兴的路还很长,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做得怎么样?能打几分?要由后面的人来判定了。”是啊,中国以后的路到底该怎样走,这个问题,是不该由他们这代人来回答了。
闲聊时,我曾问过他,你怎么概括自己的一生?他说:“没想过。”我说,说你是政治家吧,你又不懂政治,最多只是个身居高位的普通人;说你是军事家吧,按职位评,33个军事家里又没你。我想了好久,你大概算是个革命家。他点点头,好像是默认了。
我说,能够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吗?或者说,是个共产主义者?他说:“这要由别人去评价,当然,怎么评价都可以。要我自己对自己下定义,那就是追求和坚持真理;孔子讲三畏,我是三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再加上一个,不畏权势,恪守自己做人的求真、求实的本质。也就是我的座右铭‘要辨真伪羞奴颜’。这些,你叫它信仰也可以,叫它人生观也可以。”
我又说,现在革命没有了,连共产党也都不叫革命党了,我真想像不出,你如果生长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你这个革命者能干些什么?他好像是若有所思,他说:“我可以当个教员,当个中国近代史的教员。我会告诉我的学生,一生都要为国家为民族去奋斗!”
父亲的生命之路终于要走到尽头了。
2002年1月9日是他92岁的生日,全家准备要好好为他庆祝一下,可是,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病了,而且很重。
他显得焦躁不安,一会儿要起来喝水,一会儿要起来小便,一会儿要坐着,一会儿又要躺下……医生劝他说:“不能再折腾了,必须静躺,现在保存体力比什么都重要。”
但父亲做不到。他太自尊了,他根本不允许任何人摆弄他的身体,他一次又一次挣扎着起来,每次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父亲是个典型的军人。所谓典型,就是有着不同于众的特有的军人姿态和军人气度,在众多的人群中,一眼就能把你和老百姓分辨出来。他腰杆笔直,站立时从不插手或背手;坐着时身不靠椅背,不跷二郎腿;除睡觉,决不沾床;衣着简朴无修饰,但却整齐利落。言必信、信必果,承诺的事必须做到。对强者刚硬,对弱者体恤,危难时总有军人站出来。过去我当兵时也还是这样,一入伍,第一件事就是养成教育,按军人特有的习惯,站立、走路、睡觉、着装、讲话,以至一切言行举止。父亲几十年的习惯养成,你要他吃喝拉撒靠别人,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军队就要求他们,在任何场合,都要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典范和楷模,自爱、自律。当然,现在标准不同了,不再强调从行为上到内在修养的自我约束。
他是那样的固执,他不允许别人贴近他,在他眼里,生命是有尊严的。看得出,他在挣扎。很快,他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精力便耗尽了。
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无法吃饭,无法喝水,甚至不能自主地呼吸了。人们切开了他的气管,插上鼻饲管和导尿管。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
其实,早些时候我就有了预感。他的话越来越少,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目视远方。有时看见他屋里的一个小摆设,我会随口说,挺漂亮的哟!他会说:“拿去吧,做个纪念。”有时谈到一本书,我说,我先翻翻。他会说:“拿去吧,来,给你签上个名。”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只感到由衷的酸楚。
我们父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情感?他真的是我的父亲吗,还是老师?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甚至是神……说不清,也许是,也许都不是。
还是上幼儿园时,他就坚持送我去住校,一直到我上中学、参军,中间只是小学五、六年级是走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严厉的代名词,几乎就等同于批评。长大后,我们有了思想上的交流,但这绝不包含生活。当我第一次带着孩子去看望他时,因为怕孩子哭闹打扰他休息,妻子买了包糖豆让孩子捏着。这个爷爷看见他孙子时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从小就不教好。记住,要斗私!”这种严厉,对比他对我妹妹的疼爱甚至溺爱,我有时也会忿忿。我后来调回北京,就带着老婆孩子搬出去,自立门户。衣食住行从不去沾他的光,甚至家里的车我都不坐,再远再急,也是自己去想办法。对我的做法和态度,其实他是看在眼里的,但他只是说:“我赞成你搬出去。也赞成你自食其力。”有一年春节,他爬上6楼,来到了我那个50平方米的小屋,和我一家三口欢度节日。后来我分到了90平方米的房子,又是春节,他爬上了4楼,他和我妈妈商量:“他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今年春节,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过了?”他完全不像我对我的儿子那样,他几乎从来没有辅导过我的学习,了解和关注过我的生活,包括今后的前途。当我决心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立志从军,他只说了句:“人各有志!”但当我到部队时,我的信他每封必回,前后几十封,一张一页,密密麻麻。当我因为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而被冤屈挨整时,他找了许多哲学书籍寄给我,相关的页面上都加注了眉批,看得出,他的揪心和为我下的工夫。
应该承认,父亲的严厉会使我产生和他的距离感,每每想起总有一份说不清的隐隐的沉重。
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没有因为自己的事向父亲开过口,希望借助他的权势来帮助我。我不能让他小看了我,因为,我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信念,即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萌生这样的念头,都是可耻的!
也许这就是他留给我的财富,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有个名叫周立人的老同志,战争年代曾在我父亲身边工作过半年,后来这位老同志从溧阳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每年入秋都给我家送一篓子螃蟹。他去世前,没有留下别的话,只是叮嘱家人亲友,记住,每年都要代我给爱萍首长送螃蟹。他对我父亲的真挚情感让人唏嘘不止,其实我父亲并没有特别关照过他。当我动情地将这故事讲给我儿子听时,这个新时代的小伙子竟说:“在这个故事里,真正让我折服的是我的爷爷。敬仰和爱戴他的人,不是因为他曾给过他们什么利益,而是为他特有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像这样的故事很多。他身边的一个警卫员,后来安排工作,父亲说,你当领导不行,在我身边待长了,脱离实际,下基层去,好好补上这一课。这个同志很伤心,他说,我吐出的是血,可首长只看成是口红水……周围人也有说闲话的,无非是别人家首长安排关照身边的工作人员,怎样,怎样。我们听到后很尴尬,但谁也不敢告诉父亲。几年后,这位同志成了一个单位的领导,我去看他,他说:“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衡量他,不能用我们这些俗人的标准。他是我一生最敬仰的人。”
父亲退休后,1993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新一届军委成立。组织上决定任命我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我考虑再三,给上级写了报告:“……根据军官服役条令,我为国家服役已满三十年,我请求退出现役。”我的大半生都交给了这支军队,从普通士兵,直至军委领导人,他们都融入了我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军队更熟悉、更让我留恋的了,但人生似乎还有更值得我去追求和珍惜的东西。军委首长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们的子弟在部队的不少,但像张胜这样从一个兵当起的,怕也是不多的。他在工作中是有建树的,这次是重用……他执意要走,老首长知道吗?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回答的还是他在我参军时说的那句话:“人各有志,随他吧。”
事后,他只问了我一句话:“你不会饿饭吧?”
美国影片《兄弟连》里有这样一段对白:Iremembermygrandsonaskedmetheotherday,hesaid:“Grandpa,wereyouaherointhegreatwar﹖”
“No,”Ireplied,“ButIservedinapanyofheroes.”
(有一天我的小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