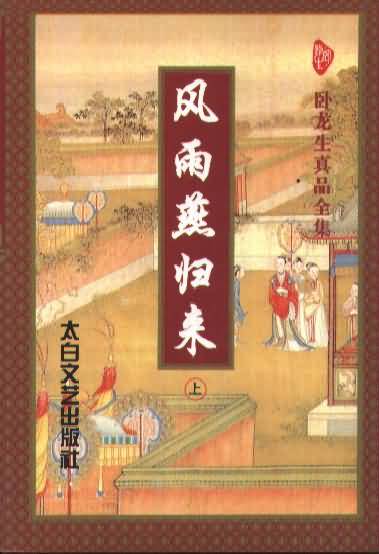风雨沧桑-第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钱他们对半分。”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挨抢警察不管,我打了他俩警察就跑出来抓我。这中央军地盘上的警察可真不咋样,这不是和满洲国的警察一样,变着法欺负老百姓吗?
出了这事以后,我再也不敢瞎溜达了,找个旮旯坐了下来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
过了一会火车进站开始检票,我随着拥挤的人群上了火车。
待我坐稳后,一打量这车厢里的人,多数都是难民和伤兵。车厢里乱成一团,孩子哭,女人叫,伤兵骂,那气味难闻得你简直都喘不过气来。尤其是那些伤兵,头上扎绷带的,吊着胳膊的,拄着大拐的,那都是横着膀子逛啊,吵吵骂骂地可那跟人要座。
有一个胖头胖脑拄着大拐的伤兵挤到我的面前,用手指我的脸蛮横地说:“你起来,老子坐一会!”
我没理他。
“咋地?老子在前方打仗腿都断了,朝你要个座,你他妈的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你这嘴干净点,你腿断了,我这腰还差点折了呢,我朝谁要座去?”
他瞅了瞅我身旁的大棒子,态度好了点。
“兄弟是哪个部队的?”
“保安四纵的。”
“四纵在长春啊,你咋跑这受了伤?”
“上前边送情报把腰摔坏了。”
“也够倒霉的了,看来你是个官吧?”
“什么官不官的,咱们都是给人家卖命的。”
“你这话有道理。”
看他拄着拐,没地方坐没地方靠的样子。我说:“你先坐会,过一会我再坐。”
“这敢情好啦,谁也不行啊,还是咱们当兵的心疼当兵的。”
我心想这话可是真扯远了,你是啥兵,我是啥兵?这时候火车鸣起了汽笛,随着“咣铛咣铛”的声音,列车开出了吉林站。
那时候的火车也没个准点,站站停停,停停站站。好在大家唠着闲嗑,时间过得也挺快。我和那个伤兵互相换着坐,倒也没觉得很累。
一晃四个钟头过去了,火车到了长春站。我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了站台。
长春在满洲国的时候叫新京,日本人在这里没少下功夫,一出车站我的眼睛就不够用了:站前那宽敞的广场、马路,来回奔驰的大汽车小轿车,穿着号衣的车夫踏着的三轮车、来回奔跑的黄包车,珠光宝气衣着华丽的女人、西装革履的富商大贾、衣襟烂缕的贫民百姓和随处可见坐在地上面前放着坏盆坏碗的乞丐。尤其是那一栋栋高楼和一座座二层日本式的黄色别墅更是叫我眼花缭乱。说句实在话,这样繁华的城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难怪赵杰曾说:“你到长春看看,那才叫开眼呢!”
但是我总觉得这新奇而又繁华的城市里,总有一种叫人不愉快的感觉。是高楼造成的压抑,是不断响起的汽车喇叭声和买卖人此起彼落的叫喊声,还是穷富差别过大而造成的心里震撼?我那时说不清楚,反正觉得没有我那土生土长的破帽子沟叫人心静,令人留恋,想到这里真想扭头回去。
按着赵杰留下的地址我打听了好几个行人,他们都带搭不理地说不知道。我心想这城里人咋这么牛气,要是在农村的屯子里,谁家要是来了个客,无论你问起谁,他不但告诉你在哪,还要乐呵呵地把你领到谁家。
打听警察,警察更是连理都不理。你再问他,他眼睛一瞪:“沾闲啥——一边去!”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叫了一辆黄包车。坐着黄包车东拐西拐地把我拉到了保安四总队司令部。
到了门口把来意和警卫一说,其中一个人转身到岗楼里,拿起了电话说了些什么然后出来告诉我:“你在这稍等一会吧,赵副官正在开会,等会就出来。”
过了一会,看样子是散会了,小楼里走出了不少的军官。我一看这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八路军部队的军官可真不一样,全是一色笔挺的毛料衣服,脚上的皮鞋铮亮,走在当院的石板路上嘎嘎直响。八路军的服装那可差远了,就连沈小丑那么大的官还都是灰拉吧唧的布军衣,裤腿上还上了两块补丁。
正在我呆呆地瞅着这些军官时,赵杰从小楼里走了出来,离老远就说:“啊呀喜山,你来了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我好派车去接你?”我心想你这不是废话,咋跟你打招呼呀?
这时我一打量这赵杰可不是往常回家的赵杰——一身得体的军官服,衬上他那笔直的身板,大分头梳得铮亮,在落日的余辉下,随着嘎嘎的脚步声,领章和肩章上的金星在一闪一闪,崭新的牛皮武装袋上挂着手枪,皮套油亮油亮,的确是挺精神。
走到我跟前时他问我:“你怎么不往前走呢?”
我指了指那四个警卫说:“我也不敢哪!”
他笑了笑说:“你怎么找到这地方?”
“费老劲了,问谁谁都说不知道,后来叫了一辆黄包车花了十块大洋。”
“十块大洋,哪有这个价,从车站到这二元纸票子他都乐不得的,这十块大洋够他一年挣的了!”
“我也不知道呀,这钱花的!”
“花就花了吧,上那个火干啥?”然后问我,“你来是有事吧?”
我不是好气地说:“有啥事,是被你们中央军撵得我找中央军,这成啥事了?”
门口的几个警卫一听抿嘴乐了。赵杰急忙说:“走吧,咱们回屋唠去吧。”
赵杰帮我提着包来到了他的宿舍。这宿舍也是一栋二层小楼,就在司令部的后院。听他说,这个院套满洲国的时候,是一个日本大佐的住宅,现在里边住的都是司令部的独身军官。
来到二楼赵杰的房间,他开开门我往里一瞅,立刻就惊呆了:这个房间又豪华又漂亮!只见进门的大客厅里铺着纯毛的腥红色地毯,墙上挂着些名人字画。
赵杰看我站在门口发愣说:“进屋啊,愣着干啥?”我瞅了瞅脚上布满灰尘的黑里伏呢布鞋,这脚还真不好意思往里迈。说实在的,这双鞋在农村还是双讲究的鞋,那还是我结婚时候买的,一直没舍得穿。这次来长春玉莲说:“你把他穿上吧,六哥那都是当大官的,别叫人家笑话。”我才狠了狠心穿了来,没想到这鞋在这却拿不出手了。说实在的人都好个脸面,我干站在门口进也不是,站着也不是。赵杰又催了我一遍,我才迈进了屋里。
赵杰见我进屋后,喊了一声勤务兵“打点开水来”,然后告诉我:“站着干啥坐下呀!”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沙发上,我知道这东西坐狠了会“忽悠”一下陷进挺老深,没坐过的人真要吓一跳。
赵杰见我用手一直按沙发,笑着说:“怎么样校长,这玩艺没坐过吧?”
“这玩艺咱没坐过。”我问他,“这套玩艺得多少钱哪?”
“咱们当兵的今天在这,明天上哪,谁有闲心买这些玩艺,这都是原来那个日本大佐的。他们跑了后,这房子就让我们占了。司令特别照顾我,让我住了这个大房间。”
这时候天已经抹黑,赵杰打开了电灯,这电灯我更是头一次见着,心想这玩艺可真好,不用油还贼拉的亮。不怪工作队的老八路同志说他们没来的时候,领导告诉他们,东北那地方好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谁去谁发呀,他们才使足了劲往东北来。
勤务兵端来了水,沏上了茶。赵杰问了我一些家中的情况,我把我来的原因和他讲了。
他说:“现在的战局谁都难说,依中央政府老头子的意思是让杜长官把八路军一气赶到苏联去。可杜长官前怕狼后怕虎,拉法一战打得他胆战心惊,命令部队以松花江为界,原地休整,这才有了暂时的消停。”然后问我,“共产党在那边得民心不?上次你回来我已经跟你说过,这共产党非常受穷人的拥护,他们也真给他们分东西啊。然而有钱人是不得意共产党的,尤其是那些地主老财。不过以我看哪,当今社会穷人太多。阿玛说得对,这共产党是要成大气候的,别看八路军打四平失了败。但这胜败乃是兵家常事,这暂时的消停给八路军有了喘息的机会。我们司令说这杜长官这次是个失误啊,等八路军再打过来的时候,这局势就难说了。”
正在这时勤务兵敲门告诉他食堂开饭了,他问什么伙食,勤务兵说了句“老四样”。他说:“这食堂的伙食不怎么样,天天晚上四个菜也不换换。咱俩今晚到饭店吃去,我也换换口味。”
我俩走出师部大院来到斜对面的一家饭馆,上了二楼,进了四号房间。这里只有一张桌子,收拾得非常干净。
老板娘听说后,急忙上楼进了屋,看到赵杰就说:“唉呀,赵副官,今个咋没带太太来呀?”
我一愣,赵杰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给她介绍道:“这是我妹夫,从老家来。”
她一听“啪”地给自己一个嘴巴对我说:“你看我这嘴,说笑话也不分个时候,这可是我说着玩的你可别当真,其实赵副官哪有什么太太,净他自己来吃饭。”事这玩艺你别太解释;往往越解释越让人怀疑。
赵杰见他没完没了地唠叨就说:“行啦,行啦,你别瞎咧了!叫你这一咧咧假的也成真的了,快给上几个拿手的好菜!”
老板娘说:“好咧!”然后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扭搭扭搭下了楼。
“这个老娘们;嘴像个破车似的。多咋也把不住。”
“买卖人吗;就是指着她这张嘴。如果像个死木撅子似的;这饭店还能开吗?”
喝着茶我心里琢磨;赵杰啊赵杰;你老婆怕你在外边吃苦;在家省吃俭用的把小份子钱都给你拿来;可你倒好;即使没有小老婆;恐怕也是有点说道。要是这样,你怎么能对得起你的老婆呢?再说这事要是叫你老婆知道;那醋罐子一翻你可就要沾包啦!
按理说;那时候有钱有势的人说个三房四妾也不稀奇。赵杰虽然有钱有势,可他却不敢这么做。因为他老婆的娘家是榆树县的大财主,她家不光有良田千顷;而且男人们还大多在外做事,最小的官就他的亲叔叔——日本人屠杀老黑沟时不服从命令的马大队长,所以赵杰非常怕老婆。
这时候跑堂的端上了菜;赵杰把酒倒好,把筷子递给我说咱们边吃边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