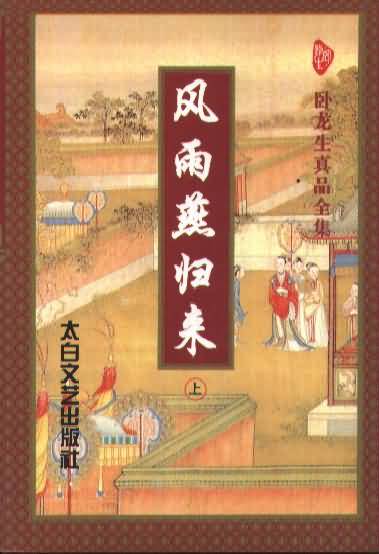风雨沧桑-第1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看你这个长官,怎么有点不识真假呢,这么大的事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行,我信你的,那路况怎么样?”
“十多年以前,老乡们上‘汤池镇’都走这条路,路面挺平整。后来日本鬼子把这里变成了‘无人区’,老百姓也禁止通行。满洲国倒台后,‘魔鬼谷’闹起了鬼,人们照样不敢走。现在的具体情况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到了‘五家屯’一打听就明白了。我估计光复三年了,这道能有人走。”
说着话的空,前边果然出现了一个岔道。我让车队停下后,找到周科长把想走小路追赶大部队的想法和他说了一下。他说:“如果道路要没什么问题,我看抄近路是个好主意。至于‘魔鬼谷’闹鬼的事,那是老乡自己吓唬自己。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能信哪些事吗。”
我们顺着小道往前走了一段,通往‘五家屯’的路虽然窄了一点,但路面还是不错。至于‘五家屯’那边的路怎么样?只能是碰碰运气。于是决定抄小路赶往‘汤池镇’。
天放亮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五家屯’。‘五家屯’顾名思义就是原来只有五户人家而得名,屯子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大山谷沟口。我们到的时候,已有二十来户人家,安排家属住宿富富有余。
经过一阵忙碌把家属们安顿好以后,我花钱雇了几个妇女做饭。趁等吃饭的空闲,我挨家走了一下,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在眼前。这些人家的房子从外边瞅歪歪扭扭,有的甚至破破烂烂。屋里却挺阔气,家家都有瓷砖炕柜,墙上挂着只有财主家买的起挂钟。更为明显的是,男人都穿着日军的毛泥军服,炕柜上叠着崭新的军被,炕上铺着军毯,冷丁一看还以为到了日军的兵营呢。我问了一下老乡:“看样子你们生活都不错,怎么不把房子修一修?”他们说:“这战乱年头,谁修那玩意。”
“那你们把钱都买些军用品,是啥意思,难道你们喜欢小鬼子部队?”他们笑而不答。
“八一五”日本投降的时候,东北的老百姓很多人趁日本人回国的机会,连捡带抢确实发了不少的洋财,有日本货的老乡到处都是。因此对这屯的奇怪现象我也没往过多的寻思。
吃过了早饭,我问了一下老乡“‘魔鬼谷’的道能走不?”,他们都说“道是有,但没人走”。看到家属们躺在炕上进入了梦乡。我和侯殿春到屯外检查一下布岗情况。
我俩走到屯子边,往南面的群山中一瞅,几架大山的山尖在云雾中忽隐忽现。山上到处都是陡峭的山崖,怪石林立的山坡,古木参天的老林子,一条峡谷弯弯曲曲延伸进群山之中。
我说:“这条谷八成就是‘魔鬼谷’。”
“二哥,这地方挺险恶呀!”
“今天晚上咱们就得穿过这条大山谷,到达‘老狼窝’,听老乡说这条谷有三四十里地长,近些年静闹鬼,也不知是真是假”
侯殿春听后“哈哈”的乐了起来,用手指着我说:“二哥呀二哥,你可真能逗。成千上万的死人咱都见过,你怎么忽然又信起了鬼?”
我笑了一下说:“我倒不是信那些胡说八道,我琢磨无风不起浪,老乡们既然有这么传说,八成是有点说道。”
“那你怎么不找老乡详细问一下。”
“问倒是问了,可他们也说不明白,都说是听人家说的。”
“那不就得了,看来是些瞎扯的事。”
正在这时,对面山坡上出现了一个赶着三头牛的人,吆喝着往苞米地里走。我对侯殿春说:“咱俩过去和他唠唠,不弄明白这件事,我这心里没有底。”
下了屯前的坡,穿过沟塘,我俩来到了苞米地。
这个放牛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背有点驮,圆盘大脸,浓眉大眼,黑红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右脸蛋上有一条伤疤,搭眼一看我就知道是子弹擦过烧伤的。
这个老汉看到我们过来后,没有反映,也没有出声,蹲在地上看着牛吃苞米秆棵上的叶。
我走上前问了一声:“大爷,放牛哪?”
他抬头瞅了我一眼:“废话,不放牛能赶着牛在这吗!”
我一楞,心想这老汉挺倔呀。同时我也看出此人并非等闲之辈,因为他在看我的时候,眼睛显得铮亮。我知道没有三十年以上内功功底的人眼睛中是发不出这种光的。我当时就断定他是个武林中人,而且武功高强、内力精湛、胆识过人。我瞅了瞅侯殿春,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又问了老汉一句:“大爷,你这牛光吃苞米秆能吃饱吗?”
“这与你有啥关系。”
侯殿春有些急眼了:“你这老汉,咋这么倔。跟你说几句话能咋地!”
“我就这样,爱咋地咋地!”
我年轻的时候好奇心特别强,一碰到希奇古怪的事就爱刨根问底,老汉这么一倔倒把我的好奇心勾了起来。
我满面笑容地蹲在他的面前,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递了过去:“老前辈,抽颗烟消消火,我这兄弟性子急。说话没分寸,您老别往心里去。”
老汉听我这么一说,脸色有点缓和了下来。接过烟卷,我赶紧划着火柴给他点燃,老汉抽了一口后笑了笑。我赶紧说:“大爷,看样子您是个见过市面的人,我们是解放军,您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以前的老八路。”
老汉一听打量了我一下说:“唬谁呢!老八路军有你这身打扮的吗。”
“您真有眼力,我们以前是中央军,现在起义了投奔了八路军,因此我们也是八路军,现在叫解放军。”
老汉听后“噗嗤”一声笑了:“你这个小军官,挺精挺灵的,怎么说话这么罗嗦。一会这个军,一会哪个军,你也不用跟我套近乎,我知道你有事问我。说吧啥事?”
“大爷,我们被大部队落下了,想抄近道去追赶,可又不知道这上里的情况,您也看到我们的队伍竟些老人,妇女和孩子。听说谷里不消停,您想要是出点事,那可咋整。您能不能把谷里的情况和我说一说?”
老汉听我问的是谷里的事,脸阴沉了下来,气色由红变青,两眼闪出凶光,喘气声也急促了起来。
侯殿春一见把枪端起来对准了他,我急忙瞪了他一眼,他才不情愿的把枪放下。
我对老汉说:“老前辈,看来您和这谷有事牵连哪。您要是觉得不好说,就当我没问,犯不着这么动真气。”
老汉喘了口长气:“刚才你叫我什么?”
“老前辈呀。”
“你已经这么叫我两次了,为什么这么叫?”
“您不用瞒我,从您的眼睛里我看出您是武林高手。我想您在这山高林密的偏僻小村住,肯定是有难言之隐。”
听完我的这番话,他站了起来,我也随着站起了身。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突然右手变指,抬手直点我胸前的命门穴。我侧身一闪,躲过了他的一击。他收手后,笑了笑说:“小军官功夫不错,看来你也是武林中人,不知你是那门那派,师傅是谁?”
“晚辈功夫属外家功,关东长白派,家师是吉林舒兰王文山,人称‘关东二先生’。”
他听后惊讶的看着我,喃喃地说:“也叫‘铁掌无敌手’,善使一条纯钢打造的三节棍。”
“对呀!您怎么知道?”我惊讶地问他。
他问我:“你是他什么人?”
“我既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侄孙儿。”
老汉听后长叹了一口气,眼中透出愧疚的目光,低声问我:“你可听他讲过一个轱辘的事?”
“听过,而且印象非常深。”
他打了个“唉”声说:“哪个不争气的轱辘就是我。”
我呆呆地瞅着他。心想,这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我怎么能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碰到当年忘恩负义的轱辘。心里不免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真想损他几句。
他见我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连连说:“惭愧呀,惭愧。想我堂堂‘大刀关胜’的后代竟办出如此窝囊的事。”说后泪如雨下。
看他悔恨交加的样子,我的心软了下来,劝道:“关爷爷,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您不要太往心里去,人没有不犯错误的,错了知道改就可以了。不知后来您看到我二爷爷没有?”
“孩子,难得你叫我一声爷爷,二先生后来我见到了。说来话长,咱们还是到家里去唠吧。”
关爷爷的家在离屯子一里地的小山坳里,两间矮趴趴的小草房,一个牛棚。院里一条半大的小花狗看到我们狂吠了起来。关爷爷喊了声“消停点,一边呆着去”,小花狗夹着尾巴,嘴里“呜呜”叫着不情愿地趴到狗窝里。
关爷爷打开破旧的门锁,把我们让进屋。我端详了一下屋里,只见这当年的轱辘依然是贫穷,满屋只有一个歪歪扭扭的破碗柜和一张用木板钉成的炕桌。他尴尬的笑了笑,自言自语地说:“我这辈子八成就是穷命了。”坐下后关爷爷给我们讲起了一段悲壮的人生故事。
关爷爷本名叫关中兴,那一年在“常山屯”被二先生撵出家门后,羞愧难当。没有继续在关东停留,穿山越岭,风餐露宿,挑着轱辘担子返回了山东老家。
回到家中后大病了一场,病好后一改常态,变得沉寞寡言。老爹问他:“中兴啊,你这次闯关东钱没少挣,怎么反倒变得蔫头格脑(没精神)的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憋在心里?”关爷爷听后,把在关东如何病倒,二先生如何仗义救人,自己又如何忘恩负义,在二先生危难之时不出手的事,和老爹述说了一遍。
老爹听后气得口吐鲜血,指着他骂道:“逆子呀,逆子!关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你不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应还涌泉之报的古训吗?你这么做叫我死后怎么向列祖列宗交代。想不倒关家几百年侠肝义胆的名声就毁在你手中。你不用在家住,我跟你丢不起这个脸。马上返回关东去,找到二先生求得人家的谅解。不办好这件事不用回来见我。”老人说完这番话后,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发送(出殡)完老人后,关爷爷领着老婆和一双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