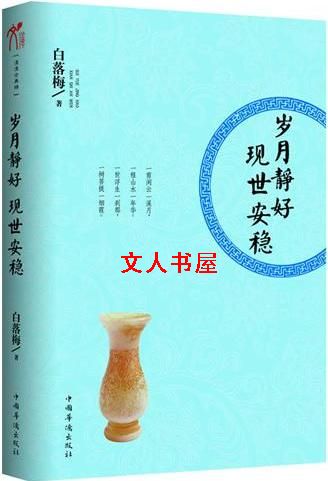岁月如歌-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有的,归云看到一间尚有伤患的病房门外,有人同那位杰生大夫说话。
那人穿一身素色旗袍,手里提了暖瓶,是位中年太太。那太太正好在问:“卓阳可来过?”“来过几次。”杰生大夫说。他们竟然在说卓阳,归云留了心在听。那太太说:“我总担心这孩子,整天跑那些危险地方。”杰生大夫安慰:“阳是个很勇敢的年轻人,上帝会保佑他平安无事的。”
“他又好几天没回来,如果您看到他,可要他再忙也回来让我看看好歹!您是不是就要回国了?”“大使馆已经安排好,一切按国际公约执行,不会受到日本的阻拦和袭击。”
那位太太叹气:“卓阳不肯走,怎么说都不肯!”“您放心吧!上帝会保佑你们的。您又带了那么好的汤给伤员,您总是那么好心!” 杰生大夫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看着他们伤的都那么重,心里总想要做点什么!他们喜欢喝这汤,我也安慰了!”
那太太侧了身,归云看清楚相貌,有些眼熟,不及确认,有人医生急急跑了来。
“杰生大夫,麻烦您来看一下高连长!”杰生大夫旋即随着那人奔跑过去。归云一听是“高连长”,一下心也慌了,跟着他们一起往高连长的病房跑。
但只她被闭在那扇病房的大门外。房门是绿色的,外面的天渐渐阴沉了,这绿,也绿得阴阴的。外面在起风,还挟着点点的雨丝,打入走廊,打到归云的身上。归云躲到檐廊下,双手抱着臂蹲下来,把头埋在肩窝里。这天的阴雨缠绵了很久,归云带了伞,但还是被困在空旷的伤病医院中。
她一直趴在高连长病床边的床头柜上写信――这是高连长临终前拜托给她的最后一件事,为他远在北方的妻子写一封丧报。高连长的妻子闺名“翠莲”,复杂的笔画使归云无法写得漂亮。但她牢牢记住高连长留给妻子最后的话——“切勿哀痛,保重身体,侍亲育儿,以待胜利之日”。她一直默念着,生怕忘记半个字。抬眼望去,病床上空空如也,人不知归处。心头空空落落,异常难受。医生见她写的艰难,要帮她写,被她倔强地拒了:“高连长要我给他写的,我一定要做到!”
高连长临终前这样对她说:“小姑娘,恐怕我要麻烦你的这件事情会让你很为难,这封信句子不多,你能亲自写给我妻吗?其实写字并不困难,难的是永远不去写。连长叔叔相信你能克服困难。”
那时候,他很虚弱,神思在消逝。但对她说了这样的大段话。她才了解,军人也是细腻的。
临终前千般嘱咐,是要和妻子诀别,也是要给这位在最后日子里抚慰过自己伤痛的小女孩最后的鼓励。所以她坚持写,要写的漂亮,要写的娟秀。但是,泪也不停流,顺着笔杆子,落在信纸上,让一张张纸变得虚软无力。这支钢笔是她为了给高连长写信时买的,在商店里挑挑拣拣,买不起美国的牌子派克,但也不想买得太差,售货员向她推荐:“这支笔是国产的,牌子老好的,叫‘博士’。国难当头,我们要支持国货。”她立刻就买了下来,回到病房对高连长说:“这是我第一次买笔,国产的,听人说不错,写起来应该好。”后来卓阳写了信,高连长夸道:“字好,国产的钢笔也好,我们中国人生产的东西不比外国人差。”最后钢笔回到了她手上,成了高连长的遗物。她望着这支黑色的,戴着镶金边的笔帽的钢笔,庄重、深沉,捏在手里重千斤。
她不断写,仍旧写不好这字,不断气馁。“你说,我来写。”背后响起熟悉的声音。回头,是卓阳,站在他的身后,一裤腿的湿痕,头发也湿了,贴在耳际。
他锁着眉,望住她一脸未干的泪迹。她慌忙掏出手绢再擦泪,擦好一看,竟就是他上次留给她的那条。他总是见到她哭得不成样子。“我要自己写。”归云仍旧坚持。卓阳低低叹了一口气,弯下腰,拿过她手上的钢笔,说:“你来说写什么,我写好一张,你压到信纸后面临摹。”他的确写得一笔好字,高连长都夸赞过。这也是一个好主意,不然她耗了整天都没办法写出这些字。归云转述了高连长的遗言,卓阳一边“刷刷”地就写好了,把纸递给她。
字是磅礴有力的,肩肩骨骨棱角分明,和他的人一样挺拔俊秀。归云把那纸压在自己要临摹的纸下,接过卓阳又递来的笔,临摹他的字。
一笔一划,沿着他写过的痕迹写。第一遍还是不像样。眼角看到他尚站在旁边看着,鼓起勇气,再写。卓阳就看着她临摹了一张一张又一张,右手用力捏着拿笔。不肯放弃,就像前线不肯放下刀枪的战士。待到最后一张写的已经像了样子,也工整了,外面的天色也微暗下来。归云执起那信纸,仔细看,再转头学生似地问卓阳:“能看了吗?”卓阳看去,是模仿他的字,但是工整,有力,仔细,干净,就点了点头。
归云小心翼翼地叠好信纸,放进信封里,站起身,对着那空空的床位说:“连长叔叔,我答应你的终于可以做到了,虽然做的不那么完美,但是我坚持到底了!”眼前又温热,咬住唇,忍下去。
“我送你回去吧!”卓阳当作没有看到她的泪。卓阳仍是骑了那辆更显破旧的自行车载了归云回去,他又没带雨具,坐在车后座的归云便撑开油布伞,笼着两人。入秋的上海,渐阴冷,雨丝打在油布伞上“滴滴答答”的,还有踩着自行车的“嘎吱嘎吱”声。都是无休止,像前线无休止的枪声。“你住哪里?”归云问卓阳。“我回报社。”卓阳说。“你先回报社吧!我有带伞,不会淋湿。”归云说,看到他浑身上下的淋湿的痕迹都未干,又添上新的湿痕。他说:“先送你回家。”“淋湿了会生病的。”归云转念一想,觉得他仍会拒绝,又说,“那到我家后,这把伞留给你,不过你单手骑车要小心!”卓阳听她一个人在身后念叨,不觉莞尔,扬了扬唇角,说:“好。”归云才放心,仔细地替他打好伞,一面注意不挡着他的视线,一面又注意尽量不让他淋湿。
遮遮挡挡,反让自己身上大半都被雨水打湿了。待到卓阳将她送到石库门门口,看到半身湿的她,皱了半天眉。她倒跑进灶庇间拿出一条毛巾递给他擦干衣服,然后目送他一手举着伞一手扶着车把手骑远的身影。他一个人骑车的速度飞快,如风。她又担心他了。卓阳回到报社,先进了报社隔壁的厢房。这厢房是莫主编拨出来给几个外国编辑和记者做办公室的,他们做的报纸叫《FREEDOM》,翻译纽约和巴黎的时事,也把中国的新闻发去国外。纽约巴黎的杂志能在上海同步发行,这群洋报人贡献不少。故莫主编鼎立支持,还将印刷房一并交付他们使用。里面无人,但挂着相片,是蒙娜。她正站在金门大桥前,做一个张扬的指挥的姿势,金发也张扬。卓阳将伞放好,也将相机拿出来摆桌上。他坐倒,闭目养神。有人进来了。“你这样累?”卓阳睁眼,是蒙娜。手里还端着一只紫砂茶壶,径直到他面前,问:“你还不回家去?不是已经和卓老师和好了吗?”“这样回去会吓到我妈,让我歇会儿,就回去。”卓阳又闭上眼睛。“阳,十月的船你不去了?”“你们洋人都要抢破头,哪里轮得到我们中国人?”“好,我也不去了。”蒙娜说。卓阳再次睁开眼,望住她。她轻轻笑,不多说,将掌中的紫砂壶一展。“今天在城隍庙的古董街买来的,最近很多中国富人在抛售古董。我不太懂这些,你看看这只壶怎样?”全壶暗紫的色彩,杂着粗沙,壶口高翘,壶身似一包袱裹着一方大印一般。卓阳看了,说:“这是袱印壶,不过——”仔细检验壶盖、壶底和壶内,“没有制作者印记,应是仿的,不过手艺也够考究了。”蒙娜点头,她得了些新的新闻:“最近古董买卖十分兴盛,真假充斥市场,不过真货也不会卖给我们洋人吧!”卓阳说:“你们洋人抢过我们的圆明园,现在的收藏界立志,就算再困难不得不出卖古董,也要找国内买家,再不能流传到外人手里。”蒙娜抗议:“那时我并未出生。如果我出生了,也一定真实记录一切。” 蒙娜挥手,“无真言,毋宁死!一切的刽子手都将得到主的惩罚。”“你们的主说要宽恕一切敌人。”卓阳说。“宽恕不代表遗忘,所以我们要留下证据,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蒙娜又说:“我听说有些日本人也在找中国古董,据说他们紧盯王老板呢!不过他们最想追缴的是一张碑帖,好像是唐朝时代流传下来的,和当时的日本国也有些牵扯。”卓阳认真听完说:“我后来也想过,王老板的确做的招摇了,卖好政府太过,难免惹人注目,后来有些收藏界人士退出了。”“所以卓老师的想法也没错。”蒙娜笑。 卓阳又沉默,算作承认,半晌才说:“我真的冲动了。”蒙娜却定定看他:“你变了很多,更加成熟了。”“每个人都不得不成熟!”卓阳看向蒙娜,“你有坚实的美利坚保护,但我们中国人要保护中国!”蒙娜喝彩,也鼓掌。她留在上海,也学习,也旁观。中国人,很坚韧不屈。她以前认为这个东方古国是孱弱的,只有艺术文化的生命力。就像景德镇的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且,易碎。只是经历了硝烟,她发觉未必。眼前的卓阳,自己认识已久,自己兄妹是他父亲的学生,以中国话讲,真的是青梅竹马长大的。他是个潇洒不羁的中国男子,亦狂亦侠,能哭能歌,有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之风。
她以为他是西式的自由主义人士。可他也是凝重的,说出那样的话,让她震动了。
她已经即将要体会到那种处在民族危难之中的紧迫感了。也只是已经即将要而已。隔着民族,那层痛苦也不过是隔靴搔痒。但是望着伤兵溃退的苦痛,蒙娜心中还是恻然的。伤病医院里所有人员开始大规模转移,场面一度再度混乱。人人都不知所措,人人都在信心溃失。这里的医生、护士和义工不知


![[网王]岁月如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2/234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