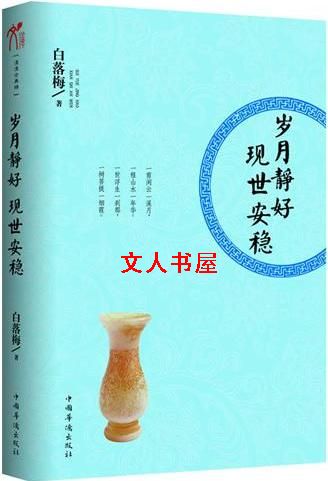岁月如歌-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未再
声明:
【文案】
。题记:
我们都不该忘记,在那段烽火岁月中,民族所受的耻辱,先烈牺牲的高贵,以及更多用脊梁活着的中国人的尊严。
烽火连年,家国飘零,人生如梦,岁月如歌!
杜归云和谢雁飞,相识于危难的一对异姓姐妹,在满目繁华的大上海落地生根。
一个幸为戏班子收容为童养媳,一个却沦为烟花地的小丫头。
当昔日的童伴再度相遇,她还是她,她却已经不再是她。
归云还可以爱,用一生的爱来偿还一段痴心的眷恋。
雁飞却已经不能爱,在万般情愁之间不惹尘埃。
家国的苦难如同人生的苦难,挣扎、抗争、热血、牺牲,是那个年代谱奏的乐章。
归云曾说:“我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点滴之墨,我唯一能为我的国家所做的,就是与她同生共死!”
雁飞曾说:“小时候没了家,大了又要亡了国,如果连假惺惺的骄傲都没了,我还拿什么活下去?”
硝烟散尽,唯有伊人仍在黄浦江畔,却已经抓不住一丝随风而逝的岁月。
谨以此小文献给淞沪抗战七十周年纪念!
特别申明:
此文虽然涉及越剧,但所有剧目出现均因文中情节需要,对于真实的越剧发展史几乎呈架空状态,所以请勿对号入座。
此外,对于杜月笙张啸林等海上大佬等人的一笔带过,很多时间与事件也与历史不符,根据情节需要杜撰,也请勿对号入座。
【正文】
孤雏篇 满目繁华何所依
一 何所依
那年的上海,似乎还在睡,似乎已经醒了。烟波浩渺的黄浦江天际,露出霞光,是撕破天边的利箭,也破开散不开的浓雾。一路照到蜿蜒流转的苏州河。上海就这样被南北一分,霞光虽普洒,但南北是有别的。南边多是红瓦老虎天窗与霞光街头接头。齐整,也料峭,朝一个地方耸立。是霞飞路上暗堡似的石库门。规整得一丝不苟,远看,也像鸽子笼。这里的人们,大多斯文,过着摩登都市里敦实的生活。男士们有体面的工作和体面的社会身份,每天按时拿着公文包上下班;女士中有独立的现代摩登人儿,不甘在男人之后的,也有安分于一所小石库门中的。这里还有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在霞光初露之际,察觉不安,他们焦躁彷徨。这一方天地太小,他们是要挣出去的。不管怎么说,这里的主人大多是新派的,家里或还留旧习,招个苏北来的女人作佣人,统称之为“娘姨”。于是在早晨,这些粗壮的娘姨用劳作开始为石库门的清晨奏序曲。
狭窄的弄堂会首先热闹,娘姨们努力而勤恳,就为这方寸间的安身之地。
她们同南北难民一致,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蜂拥来这十里洋场。大家都传“上海遍地是金子”,离开了家园,躲开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都愿意来上海拣金子。可一到上海,哪里有金子?宽宽的南京路、爱多亚路、霞飞路,条条名字嘀溜响当,座座招牌霓彩璀璨,看久了要头晕,可连容身之处都没有。这里的马路终日有扫街夫清洁打扫,整得比家里的客堂间都要干净。逃难的人有的实在太累了,把铺盖一滚,想就着这温暖的太阳在干净的地头睡个午觉,立刻就有穿制服的印度阿三来赶人,挥舞警棍,敲在背脊上,就是一条深深的红印子。于是,他们又仓皇地南北分散。有的被石库门收容,有的就被赶到了苏州河的北边。朝霞初起,也会照到这里――闸北大片空地上黑黝黝的蚕茧似的“滚地龙”。上海人要捏着鼻子叫这名儿。这里终年潮湿,散发腐败气味的小窝棚,是把几根毛竹用火烘弯成弓形,插入泥地里当作架子,盖上芦席搭成的。这种窝棚没有窗,挂个草帘当门,只能弓着背进进出出,屋子里面除了睡觉的铺盖便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总算也是个落脚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大多是无暇学习新派的,生存是更大的压力。男人们大多去码头做扛包工,或是人力车夫,都要卖力气的活儿。女人们也必须有活儿干,胆子大手又巧的编织草鞋,挂了满身,去南京路附近的人多的地方售卖;只安于住家方圆内的便聚集在某一处石库门弄堂口,拿着针线给人缝缝补补,做“缝穷婆”。世道虽然艰难,但有一席安身地,能平静度日,他们就能意足。上海滩上,也有人没有安身地。是孱弱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他们只有石库门弄堂转弯抹角处能收容。用捡来的竹竿和麻绳搭一个小小的担架,腾空搁在那些能避雨的檐廊下,乞讨些破棉袄旧棉絮,铺在上头,也能当作一个避身的小小的天地。小云的“小天地”是这大上海中千千万万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中的一个。她的“小天地”搭在四马路会乐里一个有转弯角的弄堂口。这个地方人烟稀少,是小雁找了很久,认定是个很妥贴的地方才安置了小云的。睡在这“小天地”里的小云正发烧,身上裹着旧的棉衣,破的棉被,满身都是棉絮,但又处处漏风,在这水露似的清晨,冻得抖霍霍。小小的脸颊红彤彤,是焦的,嘴唇青紫紫,几乎开裂。
她并没有睡实,紧紧皱着眉头,恍然之间渡过几个恶梦,只无力地喃喃呼唤着“小雁,小雁”。
小雁这时候正在会乐里的一个石库门的天井里升煤炉,通天的烟,熏得自己直打喷嚏。
她在给这石库门的唐倌人熬菜粥。在火旺的煤球炉上放上小铜锅,注了水,把青菜、塌菜、鸡毛菜的碎丁子与大米一起放在锅内煮。唐倌人喜欢在菜粥里加个蛋,才来四天的小雁就记得在粥将沸之时敲个鸡蛋进去,用筷子往粥里滑两下,心里却盘算怎么把这锅子可口内丰富的菜粥盘剥一点给小云带去。幽蓝的火苗在扇子上下窜动。她小小的心里也上着火,担心着睡不实的人儿,不由下了重手用蒲扇掀起一阵升腾腾的火焰。火焰逼迫人,小雁赶紧用扇子挡着眼前的烟火。她怕这烟火。那天,长春的初秋已经萧瑟得像深秋了。她的家起了腾腾的大火,远远的就像火龙的舌头,也有逼迫人的炎热。她被爹紧紧抱在怀里,奔进了断壁残垣又绫罗锦绣的“上海绸布店”。这里的料子是给女人们做旗袍的,如今被人从矮柜子里扯出来。矮柜子用来躲人。那些拿刺刀的,像进了村的黄鼠狼似的的日本兵,在街上扫荡。每个人脸上都有兴奋到了极处,五官纠结到一起的,像见到肉骨头的狗似的神情。他们躲的柜子之上,有个萝卜短腿的日本兵压在绸布店掌柜的年过四十的二姨太的身上,一下一下,起伏自己的身子。小雁听到他发出属于野兽的嘶吼,怕得要尖叫,但是嘴巴被爹紧紧捂住。
千辛万苦,爹爹带着她逃到那艘逃难船上。船被挤得满满当当,满眼皆是愁眉苦脸。
爹告诉她,这船将要去上海,上海有金条。天空里,日本鬼子的像灰色蝙蝠一样可怕的轰炸机不时隆隆开过。船上的难民都蹲下,抱着头,也抱着全副家当。她的爹爹只抱着她,将她护在自己身下。日本轰炸机阴魂不散,盘旋着,呼啸着,卑鄙地吓唬着这船上已经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船上倒是静得出奇,无人叫,也无人胡乱奔跑,屏息静气,任有日本轰炸机吓唬。他们的家都在东北,几天前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他们不知道军政界的头脑们如何焦头滥额,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家一夜间就没了,亲人也少了。日本人像豺狼一样扑进来,撕碎一切。自此以后,他们看到那上唇两撇小胡子,绿豆小眼珠子里发出绿莹莹的像坟场幽冥的光的日本人,就会攥紧拳头,咬牙切齿,恨不能狠狠咬下一块肉来。然,举家仍要生存,便带着有限的家当往南逃。最好的目的地是上海,拼死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去。终有人忍受不了日本轰炸机无休无止的恐吓。一个粗犷的东北汉子站起来,指着天空,大声骂道:“我操你大爷,小日本,你给我轰炸弹,你轰,你爷爷我化成灰都要索你祖宗十八代的命!”小雁问爹:“日本鬼子的十八代祖宗不是早就成鬼子了吗?还有命可以给这个大叔索吗?”被自己的爹喝了一声“闭嘴”。炸弹是顷刻间下来的,落在船的四周。船上的人恐慌起来,大声尖叫着寻求生机。
那只是一小会儿,船便被炸开了,小雁的意识也飞了。周围一切是混沌的,再醒过来的时候依然在船上。但,似乎是另一艘。周围陌生的人群里,没有爹。这是另一艘满载难民开往上海的船,经过原先遭遇日军轰炸机袭击的难民船时,他们发现竟还有个小女孩抓着一块小木板,漂在水面上。孩子没有死,只是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这艘船靠在了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小雁病恹恹地,迷惘地望着这码头,和码头外如云的人潮,就是没有爹。
她糊糊涂涂不认路地到处乱走。为什么上海这样大?这脚下的青石板路好像总也走不完。小雁学着一路上看到路边的小乞丐,伸着手向来往行人乞讨。有时能得一点残羹冷炙,运气好一些还会有一两个铜板,她可以买到包子吃。上海人的包子小小的,还有一面是焦的,时间长了,她听懂上海人叫这种包子做“生煎”。
生煎,生煎,为什么要叫生煎?她每天饿着肚子,衣不蔽体,漫无目的地在寒冷的街头徘徊,才叫活生生的煎熬。
谁可以把她从这种煎熬里解救出来?有一天,小雁饿得脚下打漂,一个倒栽葱,仰倒在路边。她望着眼睛上方的湛蓝的,白云朵朵的明亮天空,澄澈得没有任何污点。心想,这个爹常说的大上海,也就这片天空真的好看。当她醒过来时,眼睛上方看到的是小云那黑溜溜滚滚圆的大眼睛。那眼睛好像充满无限生气、雀跃地、欣慰地迎接她的醒来。她欢悦地叫:“爹,这个姐姐醒了!”喜滋滋地简陋的矮几上端出一碗放着腐乳的泡饭,喂小雁吃。小雁饿了多天,一碗粥吃的狼吞虎咽。但小云并不见怪,待她吃完后,还摸出一条雪白的小手绢给她擦嘴。小雁羞涩地接过手绢,看着这个小自己两三岁的小女孩,小大人似地慰贴人心。
她的眼


![[网王]岁月如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2/234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