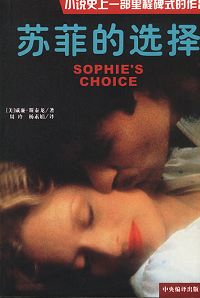����ѡ��-��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Ǹ��������ҽ������˾���ش�˵����������ֱ�Ӱ����������ȥ����
�ұ����㿹�飬����������ˡ���һֱ�ȵ�����ͣ��ǰ�ſڡ��������������ֱ��˽�ҳ������������ߡ�������˾����˵����������ҽ������������ͣ�㡣�����Һ���ֽ�����һ������û�д�����������û�����꣬��С�����ȴ�����һ���д䡣õ����Ļ�������ʢ��������ͷס�
����ͼ�ӿ�Ų����������ϵ�Ƥ���о�����Ҫ˺��һ�����ҷ������ӡ���������ҵ�������ò����������ׯ����Сʱ�������������������濴������������û����ù����������������ʵ�����������ǽ�ȫ����һ�����������⾭���˵ء��Ѽ�������������һ�����ں�Ժ���������Щ��Ǯ�˵��뷨������ƽ���ϰ�����ԶҲ�������ף�Ҳ��������ס�
Ĺ����Χ��һȦ��ʣ��������Ӣ�����������ġ��һ����Dz���ǰ��ʱˢ���ᡣ�ҿ���������ż����߹���������Ĺʯ��Ŀ��ת���ض����Ǹ�¡������ѡ���������Ĺǰʱ��һ������д���ȫ�����ҿ��ŵ��档
û����һ�����ںò��õ�Ĺ�أ���û����ʯͷ��Ĺ���ϵ��ּ�����õ��ǻ��������ϵ��������壺���ǵ�Ī�ݿ���
��վ���Ƕ���Ŀ��ĮȻ��Ī�ݿ����ҵ�����Բ�������ˡ����ǵĹ�ϵ��������ӿ���ȡ����տ�ʼʱ������֣����ȴ�����������Ҳ�֪��Ϊʲô����������������Ī�ݿ��Ǹ����ڲ�ͬ���ˡ�����������������һ���ջ��������ָ������Ҹе���ֻ����롣��û������ȥ�ٸ��ʵס�
�Ҹ��������������һ��ʹ��ļ���̴����ҡ��·�ǰ���������ϣ��ҽ�����ʱ��Ī�ݿ�һֱ�ڿ��������Ѿ����ǵ�һ���ˣ����Ǿ�����ˡ���ٲȻ�������е���Ա������������������ô�ˣ��������ﲢ�����⡣��ϰ�߸�������Ŀ�ͷ�ػ���Ī�ݿ�����û�лش���ҡ��������ͼ��ס�������ͻ���Ӳ���ġ�����û�л�Ӧ�Ľ��������������ѣ��������Ǻ��������ˡ��İ�Ϸ����Ҳʹ�ҵ��ı�Ӳ�ˡ�����Ǹ�һ������������������һ���д�ա��㲻����һֱ��ô����������Щʱ�����˲��ò�����
���٣�������������ס�
��������е��쳣��Ī�ݿ��������еػش����ҡ����ﲻ�࣬��ʵֻ��һ�仰�����㲻���ң�����˵������ôһ�仰��������û��һ���ź������㲻���ҡ���������˰��졢��������Ž��б�Ҫ�Ŀ���ʱ���һ���Ҳ�����ǶԵġ�
�ұ����ۣ�������Щ�龰���Ժ������֡��������һֱ����⣬��������Σ��ڹ�ȥ������������Ƕ��õ��˽��ѣ�Ů������ƽ������ů�����ġ����ڣ���ɨ������գ�գ��գ�ۣ�Ȼ�������¿��˿��������������Ƣ�����������ӵ���������Ī�ݿ�����������˵��Ȼ���������ӷ��������һ���ġ�
������Ĺǰ����˵�һ��ҵ������ġ�
һ��ʲ�ˣ����߳ƹܼң����߳����֣������������е�һЩʲô�ƺ������������������߽�ͼ���ҡ�����ȷʵ���У��������װ�κ����������µĺ�ɫ�ذ������żĶ�����̺�����ϵ���ʽ�Ҿ߷dz���ʵ�����������������ܼҲ���ᣬ�����Ƭ�����¼Ӳ��ǰ��Ը����ˡ���������������ʶ�����˵��һ�����£��Dz��������Ա��ġ�
���¼Ӵ����ǿ������ľ����վ�����������ϴ���һ����ɫ��ɽ�����˶��пˡ���������һ������ë�ʡ��������游�ģ������û�Ǵ��Ļ���������������ͭ��һ���ǻ�ʢ�٣���һ���ǽܸ�ѷ���ҳԾ��ؿ�����ɭ����Ҳ�����������ҽԺ̽����ʱ������ʱ����̫�飬���ܺ���ӵ�������ڿ�ɭ�������Ǹ���̬���������ң��Ҿ����ر�ס����������Ҳɢ���������ľ���̵���Ϣ��
������û����Ƭһû��ȫ�ҶȼٵĿ��գ�û�б�ҵ�գ�Ҳû��������˺��������ڴ��ƻ��ϵ����ա���ʵ�ϣ��Ҵ���û�������������κ�һ���������һ����Ƭ��
��ɭ˵������о���ô�������ˣ���
�Ҹ�����˵�Һܺã���ת���泯�ҵ����������¼�û���������ӹ���������û��ӵ������ʵ�ϣ������������ֶ�û�ա���������ǰ�������������˸����ơ�
�Ҷ��¼Ӻܲ��˽⣬����ֻ���������档�Ҳ�������ж���Ǯ�����Ǽ�ʹ������Ƭסլ������ʹ��ij�����нֵ��ϣ�������ij����������վ���Ŀߣ�������⵰��֪�����������帻�ɵй���Ī�ݿ�Ҳ���������ʣ�����ٹ������ഫ�����ʣ�����ͨ��ѧϰ�������������ʣ��ĵ�ȷȷ�������������ʡ�Ī�ݿ�ѡ��ס����������������صķ�����Ҳ����ij����ʽ�ķ��ѡ�
�����������ס�
��Ҳ���������Ҳ������Ϊ��ǰ��Ҳ�������˴�����������¼���ڼΪ���ְ�����ҵ��ˣ���ʵ��Ҳ��ͨ���Ϸ�����Ǯ���̳��Ų�������ʶ�ij������������࣬������ע���Խ�Ǽ̳д���Ų����ˣ�Խ�DZ�Թ��Щ����ĸ�ͽ�������ʩ���ߡ����Dz���˼�顣���¼��������ص�һ�壺�������˵������Լ���ͨ��Ŭ��������Ӯ�õ�λ����Ȼ����ÿ���˶����Լ����ж�������������û���Լ�ı�������������ݻ��������ʲôҲ����������ΪӦ��ʹ����ӻֲ̿����Ŷԡ���ɲ�Ӧʹ������������������٩��
�������ˡ����¼���֮���£���ɭ�������š��������Ű��¼ӣ���������ʳʹ������������Բ�����ģ�����ȫ��һ������������壬���������������ĺ�����ɫ��Ӱ���ޡ�����ָ�����ţ����ڴ�����ϡ��Ҳ�֪��ô����ط��֣�������ȥ������㲣�û����ɣ�һ����ζ��Ȼ�����ӡ�
��֮���Ըе������桱������Ϊ���¼�һֱ�������µ���һ�������ġ����ҡ���ӡ�����Լ���ʹ������ֲ�������Ҫ�ģ����˵���һ���뼺�ء�����Ϊס������Χ����Щ�˲�����������ķ羰���������ֶ��ѡ����¼��Ѿ�ʧȥ���������ӡ����Ӱ����������ģ�ʮ��ǰ���ڼݳ����١���Ī�ݿ�˵�����ϼݳ�ʱ�����ת����ʻ���������ߣ�ײ����һ�������ʽ���ӡ���֪Ϊʲô������Ϊ������������ס�����кܶ�����������������
����Ī�ݿ���ĸ�ס���ֻ����ؗ���Ρ��������ڡ���Ϣ���������ڶȼ١���һ�仰�������dz����ڸ�����ṫ�����������Ǽ���������Σ��ҵ���ĸ������װ��������ȥ����ijЩ����������Ż���������Ϳ֬��۵ģ��м��ֿɰ�������ɫ̫���ˣ��۾�����һ�ֿն���˵��ʱ�������壬�Ը�����Ѷϡ�
���������˿�ɭ���壬Ī�ݿ������ļ��˹�ϵ�䵭������������û���������¡�
��������ң�����˵��
���ǵģ����ˡ��ǵģ���������㡣���ҵ������ġ�
���¼Ӱ��ַ������ϣ����㰮��Ů���𣿡��ұ����˸����ֲ��������һ��Ǻ�����ԥ��˵�����dz�������
���ƺ����������ǻ��ԡ���Ŭ������Ŀ��������һֱ�����ģ�����֪���ġ���
�������㲻��Ϊ���¶�����ң�����˵���������ص��ͷ�������������
����ʸ�ڷ���ȷʵ���Ҳ������á����¼ӵĻ������������µ�һ����һ�ָ���п�ʼ���������ڡ�
����֪�������ڽ��ܾ��������𣿡����¼��ʡ��������ǿ��ſ�ɭ��֮��Ŀ������ذ��¼����ϡ�����֪������
�����������κ���֪������
������ô֪������
���¼�û�лش����۾����¶���˫�֣�Ȼ��˵����������㿴�㶫������
���¼Ӵ����ӳ��룬�������ȥ���ϳ�һ�����ϴ�������ʳָ��Ĵָץס���ϴ���һ�ǣ����������ҿ���������һ��������ǵ�����ʶ���ҿ�������ʲô����ʱ���ҵ��۾��ɴ��ˡ�
���¼ӿ������ҵķ�Ӧ�����������ϳ����ˡ�����տ�ʼ��˵������������ɨ��һ�ۿ�ɭ�������۾����ġ����ֿ��Ű��¼ӣ���ľȻ�ص���ͷ�����ϴ�����һ���·���Ʒ���������Ӣ����������ʽ��������ǰ�������������ǹ�����Ǹ�ʱ��
һ�������Zͼ���ķ�ɫ�����¡�
������һ��������������Ū����������ģ������¼ӵݸ���һ����ɫ�Ĵ��ŷ⣬������������ĭ��װ�����֡�����ŷ�����Ҳ�������ϱ���Ĥ�����ó��ŷ⣬���¼ӵ����ֺ͵�ַ��ӡ��һ����ɫ�ı�ǩ�ϡ�����û��д���ŵ�ַ���ʴ��ϱ����ŦԼ�С�
��������ʲ������ģ������¼�˵����ָ��ָ�Ǽ���Ʒ�������������𣿡�
�����ҵĻش��ǿ϶��ġ�
�����У������¼�˵����������������롣����δ��ͬ��Ͱ����ж�����װ�������ϴ����Է����ֲ��顣��
���ֵݸ���һ��������ܷ����ϴ��Ķ������������С�˵㡣������ͷ����һС��ͷ��������ʶ����������ʲô������־��������ҵĺ���ֹͣ�ˡ�
Ӥ��ͷ����
���������¼ӵ�ѯ���������˶��ģ����������𣿡�
�ұ����ۣ���ͼ�����������Ӥ�����ϵ��龰���ҿ־����ʶ����Ů���������Ѿ����ҵ��Ժ��ﵭ������ô����������˵�������ܻ�����ʲô�������Դ������Ѿ������Ķ��������������ˮ���ҵ��ۿ����ת������ͼ����Ů������ͷƤ�ĸо��������ҵ���ָ������ͷ���ķ�ʽ��
�����ˣ���
���п����ǣ�����˵�ţ��������۾��������������϶��Ľ��ۡ���
�����е㶫���������¼�˵�����ݸ�����һ�����ϴ�����С�������ذ�װ����ͷ�����Ǹ����ӷ������ϣ��ù�����´��ӡ�������һ�Ű�ֽ��һ����ij�ּ����ӡ����ӡ�����ı�����
��������뵱����ϵ�����Ǿͻ���ʧ�����ǽ���ԶҲ����֪��������ʲô�~�����ǽ���Ŀ�Դ������ǻ�֪���ģ���Ϊ�����и����ߡ����ǵĵ绰���ڱ���������Ҫͨ���绰���۴ˁ~������֪���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