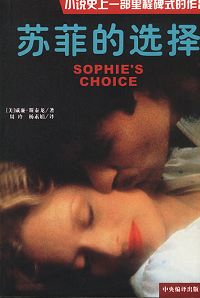别无选择-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字母y'x8'。唉,令人讨厌的是,每当他兴奋得过了头时,连我也被叫成了马基。
“马克叔叔?”
我感到有人在扯我的腿,我低头看着26个月大的康纳。“怎么啦,伙计?”
“苹果汁会让我拉肚子。”
“知道啦,”我说。
“马克叔叔?”
“噢?”
康纳以最严肃的眼神看着我。“拉肚子,”他说,“不是我的朋友”
我扫了一眼谢里尔。她掩饰着微笑,但我也看出了她的关注之情。我回头看看康纳,“可要记住哟,小家伙。”
康纳点着头,对我的反应很高兴。我爱他。他使我伤心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欢乐。26个月,比塔拉大两个月。他在我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我的心情既是敬畏,又是渴望,渴望得简直能点燃一座火炉。
他转身回到母亲那儿。谢里尔周围散乱地堆放着许多物品,她就像一头丰收时节背上驮满东西的骡子。有迷你特梅德果汁盒子和营养谷物条。有帮宝适牌的尿不湿纸尿裤(难道还有尿得湿的?)。有含有芦荟成分的哈吉斯牌手帕,专门用于擦拭饱受歧视的小屁股。有产自伊文弗洛的歪嘴婴儿瓶。有肉桂色的全麦面包,洗得干千净净的供婴儿食用的胡萝卜,掰成一瓣瓣的橘子,切碎的葡萄(切成一条条的,防止噎着)。还有一条条的东西,我想可能是奶酪。所有这些东西她都一丝不苟地装在自己的拉链袋里。主教练伦尼正向我们的队员大声叫嚷着制胜策略。我们进攻时,他就告诉他们“射门!”我们防守时,他就建议他们“拦住他!”有时候呢,就像现在,他就对这场比赛的奥妙之处提供他精辟的见解:
“用脚踢球!”
伦尼在一口气喊叫了四遍之后,扫了我一眼。我点点头,翘起大拇指,示意他继续这样干。他也想伸出手指向我示意,但是有一大堆小家伙在盯着他。我又叉起胳膊,眼睛斜视着球场。孩子们像职业运动员一样左冲右突。他们穿着防滑鞋,袜子向上拉到一直遮住护膝。即使一丝阳光也没有,多数人眼睛下面都涂了黑色的润滑脂。有两个孩子甚至把呼吸用的条形绷带绑在鼻子上。我看着凯文——我的教子,按照他父亲的指示,一脚踢在球卜,之后重重地撞在我身上。
我趔趔趄趄地向后退去。
我的日子常常就是这么打发的。我会看看体育比赛,或者与朋友聚聚餐,或者给病人治病,或者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我会按部就班地做事,一般来说感到相当体面。之后呢,嘭,出其不意遭到重重一击。
我泪如泉涌。这种事在谋杀绑架案发生之前从不会发生。我是个医生,我知道如何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保持泰然自若的神态。但是我现在就像某些自以为是的二流影星,随时随地都戴着太阳镜。谢里尔抬头看看我,我再次看到她的关切之情。我挺挺胸,强作欢颜。谢里尔变得越发漂亮了。事情有时就是这样。身为人母会让有些女人如鱼得水。这会让她们的外表出现奇迹,焕发出亮丽的容颜。
我不想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我并非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我还是照常过日子。我的确很凄凉,但不是每时每刻都这样。我并没有气馁。我依然工作,但丧失了去海外旅行的勇气。我总是想我得在这里盯紧,万一有什么新的进展的话。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理智的,甚至也许是幻想。但是我怎么也理智不起来。
令我吃惊的是悲痛偷袭我的方式。当你察觉出悲痛,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多多少少还可以巧妙地应付、对待、隐藏起来。但是悲痛喜欢藏在灌木丛后面。它喜欢冷不丁地跳出来,吓你一跳,嘲弄你,剥下你假装冷静的外衣。悲痛引诱你进人梦乡,因此使偷袭来得更加气势汹汹。
“马克叔叔?”
又是康纳。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而言,他的话说得相当好。我不知道塔拉现在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我掩藏在太阳镜后的双眼紧闭着。谢里尔觉察出了点什么,她过来准备把他拖到一边去。我挡住了她。“怎么啦,伙计?”
“大便呢?”
“大便怎么啦?”
他仰视着我,闭上一只眼以集中注意力。“大便是我的朋友吗?”
竟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伙计。你看呢?”
康纳费尽心机地思考着自己提出的问题,看那样子憋得他似乎要爆裂一样。最后他回答说:“比起拉肚子,它是我的朋友。”
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我们的球队又进了一个球。伦尼的拳头砸向天空,嘴里大喊一声“真棒!”他差点侧手翻出去祝贺攻进球的克莱格(或者我是不是该叫他克莱基——加个后缀字母y)。球员们蜂拥在他身后,激情洋溢在每个人身上。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给装腔作势的伦尼做一个安静的伙伴。
我注视着边线上的父母们。母亲们围成一堆,谈论着她们的心肝宝贝,谈论着孩子们的表现和课外活动。没人能听进去多少,因为谁也没心思听别人的孩子如何。父亲们花样可就多了。有的在摄像,有的在大声勉励着,有的让孩子骑在自己身上,有的拿着手机在闲聊,手里不时摆弄着这样那样的电子产品。上班时间他们整天埋头于工作,周末这场球赛也让他们有点专注。
我为什么要报警呢?
自从那个恐怖的日子以来,我无数次地告诫自己,不要为发生的一切而自责。从某个角度讲,我的所作所为于事无补。十之八九,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把塔拉放回家。在第一次打电话索取赎金之前,她可能就已经死了。她也许是死于意外,也许是他们惊恐万分,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谁能知道呢?当然我是不知道的。
还有,唉,难就难在这儿。
当然,我不能肯定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每一个行动都会有反应,这是基本常识。
我没有梦到塔拉——或者即使梦到了,慷慨的上帝让我记不起来了。也许我还应赞美一下上帝。换句话说,我可能没有确切地梦见塔拉,但是我确实梦见过那辆挂着移花接木的车牌和磁性标志的白色面包车。梦中我隐隐地听见了什么声音,但我坚信那是一个婴儿的哭声。我现在知道,塔拉在面包车里。但在梦中,我并没有朝那个声音奔过去。我的双腿深埋在噩梦中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当我最终醒来时,我情不自禁地沉思默想着,塔拉离我有那么近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以前再勇敢一点,彼时彼地我能够把她救出来吗?
主裁判是个瘦高个的高中男孩,一脸和善的微笑,他吹响了哨子,双手举过头顶挥舞着。比赛结束了。伦尼大喊:“噢,嘿!”那些8岁的男孩彼此之间大眼瞪小眼,都莫名其妙。有一个问他的队友:“谁赢了?”队友耸耸肩。他们按斯坦利杯冰上曲棍球的风格排成一列,作赛后的握手。
谢里尔站起身,一只手放到我的背上。“伟大的胜利,教练。”
“是啊,我是领队,”我说。
她微笑着。男孩们开始三三两两地朝我们走过来。我微微点着头,祝贺他们。克莱格的妈妈带来了一盒50包装的炸面圈,盒子外面画着基督教诸圣日前夕图案。戴维的妈妈拿了好几盒叫“玉和”的东西,说是巧克力奶,尝起来却像是粉笔。我弹了一块炸面圈到嘴里,一骨碌吞了下去。谢里尔问:“什么味道?”
我耸耸肩。“难道它们有不同的口味吗?”我看着父母们与自己的孩了在一起,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伦尼朝我走过来了。
“伟大的胜利,不是吗?”
“嗯,”我说。“我们都很棒。”
他示意我们离开。我遵从了。到了别人听不见的地方,伦尼说:“莫妮卡的遗产快处理完了。时间不会太长了。”
我说:“嗯——嗯,”因为我真的不在乎。
“我还把你的遗嘱起草好了。你得签个字。”
莫妮卡和我都没有立遗嘱。几年来伦尼一直警告我这件事。你得把谁继承你的财产落实到笔头上,他提醒我。谁抚养你的女儿,谁照顾你的父母,诸如此类的事。但是我们听不进去,我们准备永远活下去。最后的心愿和遗嘱是为死人准备的。
伦尼赶紧转换话题。“你想回家去玩福斯球?”
福斯球是专为那些没念过几年书的人准备的一种游戏,就是一些强壮得可以打橄榄球的男人在桌面上用木杆撞击短木条。“我已经是世界冠军了,”我提醒他。
“那是以前。”
“一个人就不能在他的称号上狂欢一会儿吗?我还没打算让这种感觉消逝。”
“可以理解。”伦尼转身朝家人走去。我看着他的女儿玛丽安娜在向他要钱。她疯狂地打着手势。伦尼隆起肩膀,掏出钱包,夹出一张票子。玛丽安娜接过去,在他脸上吻了一下,跑开了。伦尼看着她消失了,摇摇头,笑容满面。我转身离开了。
最糟糕的是——或者我是不是应该说是最好的是一就是我拥有希望。
这些是那天晚上我们在爷爷的小木屋里找到的:我妹妹的尸体,帕克玩具里的塔拉的头发(经DNA确认),与塔拉身体相符的一件黑企鹅图案的粉色连体衣。
这些是我们没有找到,事实上至今也没有踪影的:赎金、斯泰西的同伙(如果有的话)和塔拉。
没错,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我女儿。
我知道森林广袤无垠,树木丛生。坟墓会很小,可以轻而易举地藏起来。上面可能还堆上了石头。也许动物会发现它,把里面的东西拖到森林深处。那东西可能远离我祖父的小木屋好几英里,也完全可能在另外某个地方。
或者——尽管我只是把这个想法埋在心底——也许根本就没有坟墓。
因此不难理解,希望还是有的。这正如悲痛和希望,时而隐藏在某个地方,时而袭击你,时而嘲弄你,从来没有破灭过。我不知道二者之中哪一种更残酷。
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推测,我妹妹和一些十足的坏蛋鬼混在一起。但没有人敢拍胸脯保证他们的原始动机是绑架还是抢劫。多数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