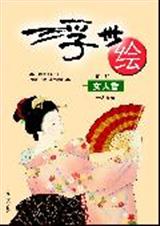玉屏香-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样一来,根本不需要迎娶哪门子的郡主。
不过江昭叶那小子竟然在灵堂中对萧钰说出那番话。倒令人意外。
难不成,他真的对她有非同一般的心思?巫师随即叹了口气,并没有否定自己的猜测。
“你听,外面在说什么?”
呼声隐隐传到沐月轩中,萧钰摆头示意韦录靠近窗户倾听。
许久。
“你到底听到了没有!?”萧钰恶狠狠地冲他吼了一声,韦录将身子半仰出去,不耐烦的对她摆了摆手:“别吵!”
“你难道不好奇他们在外面干什么吗?”萧钰眨了眨眼,“外面这么吵,一定是出事了,会不会是父王看你们欺负我,从棺木里爬出来找你们报仇?”
毕竟是相同的年纪,韦录不过也十七、八岁,听得她那么一说,猛地缩了回来:“不……不会吧……我可没欺负你。”
“你没欺负我?”萧钰将双腿抬了抬,手往他眼前一伸,“这不算欺负算什么?父王出殡之日,你却将我囚禁在此。还虐待我!”
韦录急的摆手:“我只是听命行事,不是我要欺负你!”
“那是谁欺负我?”萧钰紧接问道。
他脱口而出:“是江校尉……”
然而道出这个名字后却悔恨万分。
萧钰却得逞的说道:“呐……是你说的,江昭叶欺负我!父王定是找他报仇来了,你是他的人,必逃不过!”
“我,我没有!”韦录脑海中闪过昨日在灵堂发生的那一幕,想起那些可怖的鬼魅,不禁急喊。
萧钰心下暗喜:“你放我出去,我会跟父王求求情,让他放过你!”
“不行!”想到江昭叶嘱咐他时阴沉的面色,他故作镇静,“我,我不怕……我不怕鬼”
“当真不怕?”少女冷冷斜了他一眼,“不怕变成侧妃那样,被挖心而亡、被鬼怪吸干血肉?你知道她招惹了谁才会如此吗?”
韦录对上少女异常诡异的眼神,蓦然一惊,忍不住问:“是谁?”
萧钰附过去低声:“她招惹了我的母后!”
细密的汗水从掌心渗出。韦录的神情渐渐僵硬,灵堂前那一具尸体的惨状,他怎么可能忘记?
他初入骁军,还未见过尸骨横陈的沙场,更未见过五年前暗灵惨绝人寰的残杀!侧妃的尸体,是他迄今为止见过最令人恶寒的惨烈。
“放我出去……否则,你的下场会和侧妃一样!”她忽的厉声一喝。
韦录惊颤着拔出小刀,良久之后,终于抵不过内心的恐惧将困住少女的绳索解开。
然而,等她自沐月轩出去时为时已晚。
从“天神之光”到今夜的月食。已然为江昭叶铺出一条平坦的、直临王位的道路。
现在要将它摧毁已然不及。
“天降神谕……”少女躲在暗处望着出殡的队伍、听着那些呼声,全身的血液逐渐冰凉。
为何,连天神都要偏袒那个忘恩负义的人?
>;
第三十五章 真假画卷
当黑暗还未侵袭栗镇,月光依旧倾泻而下。追雪独自晃荡在低矮的土屋前,房中,有火光摇曳。
陈浚卸下铁甲、褪去衣袍,然而这样宽大健硕的背上却有着数道蜿蜒盘绕的疤痕。那是多年的战场生涯留下的印记,再也无法抹去。
路薛大概对此也见得多了,此时吸引住他目光的,是陈浚脊梁上的新伤,脊骨处的皮肤早便红肿。
“该死的暗灵!”他愤愤骂道。
陈浚斜了他一眼,分明疼痛,但脸上却没有表露出不适的神情:“无妨,这点小伤,我还受得住!”
“小伤?”路薛不放心道,“这万一骨头断了,你岂不是要变成废人?”暗灵那一震当真可怕,若真的将陈浚五脏六腑震裂、置他死地,那自己下半辈子还能去哪儿混?
“两位将士,这是治跌打的药。”这间房屋的邻居将药罐取来,来人是年过半百的老妇,双鬓斑白、步履蹒跚。
路薛热络的接过:“多谢大娘!”
老妇微微颔首,稍稍停下打量这这两位突然造访的将士。
一位相貌不凡,神情却十分冷淡,但还算彬彬有礼。
那位没受重伤的倒是气宇轩昂、十分热情。
不过没想到,贺生竟还会有这样的朋友?
“诶……”老妇低低叹了口气。
陈浚捉到那一声叹息,终于向她开口:“您为何叹气?”
“啊?”老妇未料想那个将士会对她开口说话,有片刻的停滞,随后才答道,“贺生每每去昆玉城,都会好几日才回来,昨日他才刚去,恐怕一时之间你们等不到他。”
“既然已来,不管等多久,我都会等。”
贺生,是除却贺楼乌兰外最清楚《玉屏卷》一切之人,身为贺楼氏右祭,所有与贺楼相关的东西没有任何能逃过他的眼。
他相信,《玉屏卷》也是如此。
这几年他们书信往来,虽不频繁,但也算是保持了联系。
现在,已经不能将解开画谜的希望寄于贺楼乌兰她们,俨然,那已经不是自己可以相信的人!
路薛见他沉思,道谢着将银钱递给老妇,送她离开后回到陈俊身侧,啧啧几声替他上药。
“何必要等,直接到昆玉城找他不更好?”路薛喃喃,“还可照看小郡主。”
“昆玉城可是骁军镇守之地,一郡首城,眼线众多。”他说着从衣袍深处取出圆润的玉佩,放在手中把玩,“父亲告诫我,在这世上,没有人会值得我完全的信任,可你和贺生,却让我将父亲的告诫抛之脑后。”
路薛朝他手里看了一眼,瞬间明白,那块玉佩是老王爷留给陈浚的东西,成色上乘、呈方形的云山雪玉被浮刻成一座城池的模样,而城池北面的皇宫被一个精细的字体代替。
瑞——这是老王爷的名。
陈瑞——当今皇帝陈显一母同胞的兄弟,亦是已经覆灭的南唐王朝的二皇子。
而这个“瑞“字,正是封号“怀瑞“的缘由。
陈显当初赐此封号只想彰显自己与胞兄兄弟情深,可却是这样两个字,将陈浚困在仇恨之中无法挣脱。
“贺楼氏那场毁灭中,除却左右祭和三姐妹,一众天官与女侍、族民要么葬身南唐帝都,要么死在逃亡途中。贺生被父亲救出,悄悄安置在羽骑,但他一心追随贺楼施来到西南郡,放弃了与羽骑并肩作战……”陈浚淡淡一笑,“可即便他没有追随父亲和我,却也不会背叛。我对他的信任,并不需要忠诚与热血,只要不背叛、不出卖,就足以换得我的信任。”
“王爷,路薛会一直追随您,绝不背叛!”他忽然跪下,将右手握拳置在胸口,“赤胆忠心,都可奉献!”
“少跟我来这套,”陈浚竟开起了玩笑,“你无端给我行大礼,反倒让我误以为你要背叛我。”
路薛垂头丧气的起身:“好不容易正正经经的给你行了个礼,却换得你这话,当真枉费了我的忠诚。”
“呵……”
疲惫的面容上终于吐出一丝发自内心的笑意。
对于陈浚来说,与路薛相识何尝不是幸事。
这个当年还在北唐国瞎混、来去如风的盗客,竟将少年时的陈浚当做猎物,对他的钱袋下手。彼时刚入羽骑的陈浚还未洗去身上王公贵族桀骜之气,不甘的费尽心机将路薛揪出来,两人在狱中大打出手,少年不过几招便败下。
随从在外头吓得胆战心惊,本以为公子会将这蛮徒斩首示众。谁知他出乎意料的将他收入麾下,从一名小小将士开始,逐渐提升为如今的将领。
只是路薛身上那副痞气至今无法褪去,成了羽骑营中嗜酒如命、不恭不顺的唯一一人。
上药之后、陈浚穿戴齐整,终有心思打量起这个简陋的屋子来。
一贫如洗——这么说也不为过。
听方才的老妇说,贺生日日酗酒,将挣来的钱都大肆挥霍出去,家中已多年未修补,若逢雨天,屋中无疑成一片洼地。
“他也真是过得下去。”探到陈浚的目光,路薛会意说道。
连油灯都分外省。
灯芯几乎贴靠底端。若不是就着屋顶星点坠下的月光,定然暗淡无比。
然而,方是这么一想,头顶的光束忽然撤去。
追雪最先察觉异样不安的嘶吼起来。
陈浚握剑起身一探。头顶的月光刹那消失在云层之后。昏暗的夜色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罩下。
*********************
清晨时分,红日东升。
延卞城俨然也在昨夜奇景的覆盖下。
向来军纪严明的羽骑亦有不小的骚动。
“定是不祥之兆。”
远离江淮故土,初次厮杀沙场的军士想起昨夜满月被吞噬,不由得有些胆颤。
“什么不祥之兆?”另一名同伴年纪比他小些,“害怕”两字写满脸上。
“谁晓得。真是不利啊,天食明月,想必是人间谁犯了大错。天神派邪魔下来惩罚他罢。”军士想到身在延卞、望月和大淮正是战事紧张之际,不由得担心起自己的安危。他望着脚下的城门,那正是战争的屠场。
杀了人算不算大错?
可那是敌军啊!
“在这嘀咕什么?”章渠从身后过来,呵斥一声。
两人随即站好,年纪小的低低答道:“昨夜的食月,恐怕不祥啊……”
章渠到底是跟随陈浚多年,潜移默化之下,行事也甚是稳重:“不祥?你们不好好守城,才是不祥!”
“是。”不敢再多说,两人躬身道。
章渠继续四处巡查,城中各处,他皆亲自一一走过,确认无异后才踱着步子回到医馆。淮军伤者不少,在羽骑到来之前都拖着了事。伤口感染愈难医治,军医为保安全将重伤之人全都挪到了医馆。
城中此时又无百姓,与军营无异。
对于突然消失的城民章渠也感到万分奇怪。这不应当是一座死城,延卞乃西南重镇,怎可能荒无人烟。
然而却又无从得知那些人消失何处。
难道,果真是食月的不祥提前来到?
“将军难道不害怕?”刘云影早便知道军心因昨夜的奇景微微动摇。一早见章渠来探望,笑道。
“自然怕。”章渠转而道,“可那又如何,王爷不在,身为军中之首,难道还要将恐惧表露出来?”
“果然是羽骑的将领,说实话,昨夜之事,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