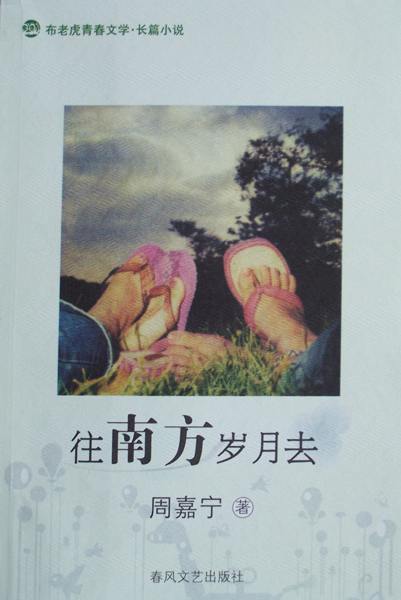南方有令秧-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率先开了口:“夫人,我本是九爷房中的丫鬟,今日把夫人的事情跟九爷说了,九爷说不能让夫人一整夜没个人在身边端茶倒水,就把我派来了。我叫璎珞。”令秧听到这里,才明白过来这丫鬟嘴里的“九爷”指的就是唐璞。“这也太让九叔费心了。”令秧为难地笑道。“夫人千万别这么客气呢,九爷说了,夫人是咱们家的贵客,一点儿都怠慢不得的。有什么吩咐我做的,尽管说就是了。”“明日见了九叔,定要好好谢他的。”令秧垂下眼睛微微一笑,脸上略有点温热。“九爷还说……”璎珞试探着看了看令秧,“若今晚夫人觉得我用着还顺手,就不必劳烦府上明日再大老远地派别的丫鬟来了,何不就让我伺候夫人,直到小如姐姐身子好了,不知……夫人的意思是怎么样呢。”令秧看着璎珞,璎珞的脸上是一览无余的无辜,像是只不过在等着她回答而已,她轻轻地眯了一下眼睛,她觉得已经过去好久了,可其实不过是片刻而已,然后她点点头。
次日令秧传了信儿回家,说只要小如病好了再回来便是,九叔家里的丫鬟伺候得甚为周到,就不必再叫家里的小丫头出来丢人现眼了。就这样,宁静地度过了两日。第三日夜里,早已熄了灯,令秧却睡不着,轻轻侧了个身,头顶的帐子隐隐地在黑夜里露出点轮廓。璎珞的声音清澈地从帐子外面传进来:“夫人若是睡不着,我陪夫人说说话儿可好?”她不作声,只听着璎珞的声音自顾自地继续着,“我们九爷跟我说,有句话儿,想让我问问夫人,若是夫人不愿意回答,便算了。”
令秧闭上了眼睛,好像只要闭上眼睛,便能真的入睡,再也听不到璎珞说什么了。眼帘垂下,眼前的黑暗并没有更浓重一分,她却听见自己在说:“问吧。”璎珞得着了鼓励,嗓音里也像是撒了一把砂糖:“那《绣玉阁》的戏里,文绣“断臂”那折,夫人还记得文绣给那坏人开了门吧?我们九叔就想问问,夫人觉得那文绣明知道自己一个寡居的弱女子,为何还要给那人开门?”“因为那人说自己贫病交加,文绣有副好心肠。”令秧轻轻地回答。“难道不是因为,听见那人说自己贫病交加,再加上又是一个风雪夜,她便想起了已逝的夫君么?九叔还有第二句话要问,那出戏里最后一折,是文绣第三次听见有贫病交加的路人叩门,已经得了一次教训,她为何还是要开门呢?”“不开门,便见不到上官玉了呀。”令秧不知为何有些恼怒,感觉自己被冒犯了。“可是她起初哪里知道门外正是上官玉呢?她究竟为何还是要开门呢……九叔还问,换了是夫人,会开门吗?”
她将脸埋进了枕头里,一言不发。
良久,璎珞静静说道:“九爷此刻就在外面的回廊上,夫人愿意当面回答九爷吗?”
四十九天过去,六公下了葬,年也便过完了。虽说因为全族都在守孝中,唐家大宅这个年也过得马虎——即便如此蕙娘也还是得忙上好一阵子:虽不能奢华,可过年全家上下的食物不能不准备;唐氏一门以外的亲友们总要来拜年还得招待;川少爷赶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回来烧香祭祖,再去六公灵前哭了一场,没过十五便急着要上京去考试,打点行装盘缠马匹,自然又是蕙娘的事情……因此,当令秧和小如总算是挨完了四十九天回来的时候,整个大宅还笼罩在“年总算过完”的疲倦里,就连蕙娘也未曾顾得上仔细打量令秧,只有紫藤笑着说了句:“这也奇了,别人都说守灵辛苦,咱们夫人怎么倒像是胖了些。难道六公家的伙食真的好到这个地步?”小如在一旁抿嘴笑笑,也不多说,其实只要细心看看便可知道,小如有些变化了。因为和主子恪守了共同的秘密,眉宇间已沉淀着胸有成竹的稳当。
只有谢舜珲,在过完年重新看到令秧的时候,心里才一惊——就像是令秧往他心里投了一块石头,所有的鸟雀就都扑闪着翅膀飞散了。虽说已褪了丧服,不过家常时候她也穿着一身白色,普普通通的白,却往她身上罩了一层潋滟的光泽。她的眼睛也一样,似乎更黑更深。她款款地走近他,然后行礼,再坐下——这一次她完成所有这些动作时,丝毫不在乎自己那条残臂,正是因为不在乎,所以没有之前那么僵硬了,某些时候因为失去了平衡,会约略地,蜻蜓点水般倾斜一下身体,反倒像是弱柳迎风。她吩咐小如去烫酒的语气比往日柔软,吩咐完了,回过头来,定睛将眼光落在谢舜珲身上,那神情就好像是这眼神本身是份珍贵的大礼,然后静悄悄地一笑,望着他,可是笑容直到她的眼光转向别处去的时候,还在嘴角残存着。
“还想拜托先生帮我往外捎点东西给人呢。”她说得轻描淡写。
谢舜珲用力呼出一口气,单刀直入道:“你明说吧,那男人是谁。”
她悚然一惊,却也没有显得太意外。反倒是慢悠悠地一笑:“先生果真和旁人不同呢。说什么都不费力气。”
他看着她的眼睛,不笑。
她压低了声音,像是淘气的孩子准备承认是自己打碎了花瓶,轻轻地说:“是九叔。”
谢舜珲像是自嘲那样短促地叹了一声:“唐璞。我为何没早想到这个。”转瞬间他又恼怒了起来,“夫人休要怪我责备你,可是这事委实太糊涂,你若真的觉得难挨,我懂,你告诉我,多少戏子我都能替你弄来,可你反倒要火中取栗,偏要去碰一个族中的男人,若真的出了事,莫说我们筹划那么多年的大事全都付之东流,就连你的性命我都救不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何不能早点想法子跟我商量一下?”他停顿了,狠狠地闷了一盅酒,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话太蠢。
“先生你在说什么呀?”她看起来困惑而无辜,“我从未觉得难挨,老爷去了这么多年,虽然有人为难过我,可是在这宅子里终归还是对我好的人多,这里是家,能在这里终老也是我的造化。我也不是非得要个男人不可,我只不过是,只不过是……”她似乎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望着他,眼里突然一阵热潮。
“你只不过是情不自禁。”他说完,便后悔了,尤其是,看着她满脸惊喜用力点头的样子。他微微一笑,腔子里却涌起一股深不见底的悲凉。这么多年,他终于明白,他究竟是因为什么如此看重她——过去的总结都是不准确的,并不是她天真,不是因为她聪明而不自知,不是因为她到了绝处也想着要逢生……真正的答案不过是,因为她无情。她身上所有让他赞赏的东西都是从这“无情”滋生出来。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那个叫唐璞的男人终结了她,她从此刻起才真正堕入人世间的泥淖之中,满身污浊的挣扎此刻让她更加美丽。而他,只能在一旁看着。他再把杯中之物一饮而尽,说:“夫人可知道,这情不自禁,怕是这世上最糟糕的。”
“我知道。”她嫣然一笑,“先生做得到‘发乎情,止乎礼’,我是个没见识心性也粗陋的妇道人家,先生就原谅我吧。我没那么糊涂,四五月间,他就又得出发去做生意了,一去一年半载。我们二人只争眼下的朝夕,他一去,就谁都不再提。”她像抚琴那样,尖尖十指拂过了平放在桌上的左臂,“先生放心,我会小心的,已经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可能不把我们二人的大事放在心上?”
“罢了。”谢舜珲挥挥手笑道,“该料到早晚也有这一天,只是谢某得提醒夫人,他是男人,在外头玩儿惯了,一时新奇也是有的。夫人却不同……”
“好了谢先生。”她宽容得像个母亲,“类似的话,想必旁人也总这么跟你说吧。我又不指望着在天愿做比翼鸟,他还能辜负我什么呢?”
这恐怕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沉溺,也是第一次尝到“享乐”的滋味。随她去吧,他一阵心酸,人生已经那么短。
万历三十三年,整个春天,令秧都是在沉醉中度过的。就连川少爷终于中了会试这件天大的喜事,她似乎都没怎么放在心上。三月十七,殿试放榜,川少爷中的是二甲,赐进士出身。消息传回家,不止唐家大宅,唐氏全族都是一片心花怒放的欢乐。休宁知县的贺贴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家里,蕙娘充满愉悦地向紫藤抱怨道:“刚刚过完了年,没消停几天,便又要预备大宴席了,不如我们趁着今年多雇几个人进来吧。”
自从川少爷踏上上京的路程,令秧便在离家不远的道观里点了一尊海灯。每个月布施些银两作为灯油钱,逢初一十五或者一些重要的日子,总要带着小如去亲自拜祭,说是为川少爷祈福求他金榜题名,真的中了以后便接着求他日后仕途的平安。听起来非常合理,无人会怀疑什么。她去上香倒也是真的,只是每次都嘱咐赶车的小厮停在道观门口等着,说上完了香会跟道姑聊聊再出来。随后便从道观的后门出去,走不了几步就是唐氏家族的祠堂了。唐璞手里一直都有祠堂的钥匙,自从门婆子夫妇被调入了唐家大宅,看守祠堂的人换成了一个耳聋的老人。令秧轻而易举地便能不受他注意地迈入祠堂的后院。曾经,她被关在那间小房间里度过了一个无眠的长夜;现今,她深呼吸一下,轻轻地推门,那个男人就在门里,她跨进来,定睛地,用力地看他,就当这是又一次永别。她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不仅仅因为偷情,还因为,如此纯粹的极乐,一定不是人间的东西,是她和她的奸夫一起从神仙那里偷来的。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她端着毒药在面前,手微微地发抖,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如今门婆子搬离了祠堂,这房间便空着没人住,她的毒药幻化成了人形,箍住她,滚烫地融化在她的怀抱中,他们一起变成了一块琥珀。战栗之余她心如刀绞地抚弄着他的浓密茂盛的头发,他不发一言,豁出命去亲吻她双乳之间的沟壑,她说你呀,你这混世魔王,我早晚有一天死在你手里。他的拥抱让她几乎窒息,他捧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