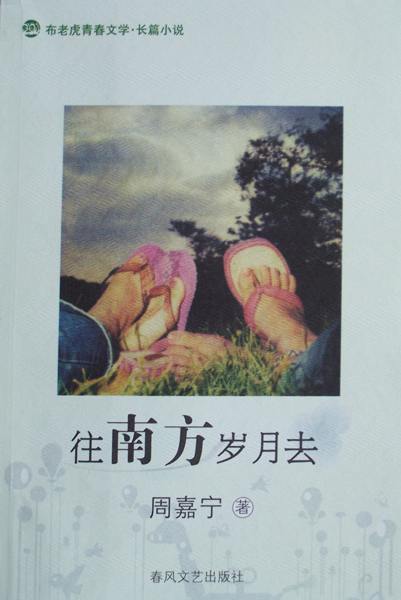南方有令秧-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舜珲站起身子,冷冷地说:“你且去吧。你那朋友的寿酒我不会去喝,我今日身子不适,恕我不送了。”说罢,转过身子看向了窗外,不理会身边一脸惶恐的小书童——小书童拿不准是不是真到了要送客的时候了。
他只是悲凉地想:那个粉妆玉琢般洁净的孩子到哪里去了?那孩子神情清冷,好像人间的七情六欲都会弄脏他的魂魄……他究竟到哪里去了?为何所有的清洁不翼而飞,却只剩下了被弄脏的无情?
万历三十一年,年已经过完了,可是令秧总还是问小如,今年是什么年。小如每次都耐心地回答:“是兔年,夫人。”回答完了,小如自己也会疑心,夫人是不是真的记性变差了?可是除却年份,倒也不觉得她忘了什么别的事情。其实令秧并不是真的忘了,她只是时常困惑——她对于时间的感觉越来越混沌了,有时候觉得光阴似箭,有时候又觉得,一个昼夜漫长得像是一生。总之,已经过了这么久,怎么依然是兔年。
小如有时候会不放心地说:“我去川少奶奶屋里给夫人借几本书来看看,可好?”她摇摇头,淡淡一笑:“罢了,看多了字我头疼。”可是小如实在想不起除了看书,还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两条胳膊就可以做的。令秧习惯了用几个时辰的时间来发呆,整个人像是凝固了。不过后来,小如终于替她找到了一件事情,她帮小如描那些绣花的样子。练习过一阵子以后,一只手臂足够应付了。小如会刻意找来那些非常烦琐和复杂的图样给她,她一点一点慢慢做,往往是一朵细致的牡丹描完了,便觉得窗外的人间一定已经度过了一千年。
“夫人,前几日我姐姐带着我去看了一出戏,不过只看了开头两折,好看得很……夫人听说过吗,叫《绣玉阁》。”小如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睛,悄悄打量着她专注的侧影。小如的娘前些日子生了场病,令秧便准了小如的假回去看看——看戏应该就是在家去的日子里。
令秧认真地摇摇头。她自然不会知道,近半年来,有一出青阳腔的新戏突然红遍了整个徽州。无论是庙会的草台班子,还是大户人家的家养班子,各处都演过这《绣玉阁》。
小如热情地为她讲述剧情,她有一搭无一搭地听,其实戏里的故事很多都有个相似的模子,只是不知为何,只要这似曾相识的套路一板一眼地徐徐展开,怎么说都还是让人有种隐隐的激动。嘴上说着早就料得到真没意思,但还是不会真没意思到离场不看。从小如颠三倒四的描述中,她大致明白了,这出戏是讲一个名叫文绣的女人,原本是小户人家的女儿,一个风雪之夜,女孩和父亲一起慷慨善意地接待了一个贫病交加的英武男人。像所有戏里的情节一样,这个名叫上官玉的男人不过是公子落难,重新回去以前的生活以后,念着往日恩情,娶了文绣。文绣就这样成了武将的夫人。夫君带兵去打仗了,然后文绣就只能朝思暮想着二人平日里的如胶似漆。不过有一天,边疆上传来了战报,上官玉死了。
“依我看,既然是打仗,说不定这上官玉根本没有死,受了伤没了踪迹罢了,这戏演到最后,上官玉还会回来,于是就皆大欢喜,男的加官晋爵,女的封了诰命,花好月圆了,可是这样?”令秧问道。
“这个……”小如苦恼地皱了皱眉头,“好像不是这样,不过我也不知道最后终究怎么样了。”
她以为小如的话音落了以后,这屋里的寂静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可是却突然听得小如的呼吸声似乎紧张了起来,然后慌忙道:“哎呀夫人,是巧姨娘来了。”然后慌忙地起身,招呼小丫鬟搬凳子,自己再急着去泡茶。令秧听见云巧说:“不用忙了,说两句话儿就走。”
那声音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笑意。
令秧继续盯着手底下那只描了一半的蝴蝶,没有抬头去看云巧的脸。她并不是真的冷淡古怪,只不过是自惭形秽。如今,她只消轻轻一转身,便感觉得出左边身子那种恶作剧一般的轻盈,然后身体就会如趔趄一样往右边重重地一偏,她能从对面人的眼睛里看见一闪而过的惊异与怜悯。她也讨厌那个如不倒翁一般的自己,所以,她只好让自己看起来不近人情,看起来无动于衷。
“你别总站着。”她并没有听见椅子的声响,因此这么说。
“站着就好。”云巧轻轻地翘起嘴角,“我只想问问夫人,夫人为何这么恨溦姐儿这个苦命的孩子?”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令秧笑了,终于仰起脸,她早就知道,会有云巧来向她兴师问罪的一天。
“我知道夫人跟溦姐儿不亲,这里头也有我的不是,溦姐儿刚出生的时候不足月,谁都担心养不活——夫人那时候刚从鬼门关回来,身子那么虚,我便把这孩子抱回我屋里跟当归养在一处。这么多年,她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玩儿什么病了吃什么药,操心的也全都是我。我疼她就像疼当归一样,他们小的时候,拌嘴打架了我都要当归让着她——因为我念着她出生不易,念着她是夫人的骨肉。也可能是一直跟着我,她对夫人生疏畏惧些;而夫人更在乎当归是老爷留下的唯一香火,偏疼当归一点,都是自然的……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夫人可以真的不顾溦姐儿的死活,如果不是恨她,夫人如何舍得把她往火坑里推,葬送她的一辈子?”云巧的手指伸到脸上,恶狠狠地抹了一把眼泪。她脸上此刻的惨淡,令秧似乎只在老爷病危的时候才看见过。
令秧感觉一阵寒气从脊背直冲到脸上,她心里一凛,脊背立刻挺直了:“你这话从何说起,我还真不明白。咱们家和谢家的婚约定下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这是好事。天灾人祸,谁也不能预料。咱们家是什么人家,这么大的事情又怎么能出尔反尔?何况,哪有一家女儿许两个夫家的道理?你们都说不愿意溦姐儿还没出嫁就已经守寡,可是你看看三姑娘,倒是夫君还活着,她过得比守寡又强到哪里去了?谢先生不是旁人,把溦姐儿送到谢先生家里,谢家富甲一方不说,她也会被人家当成亲女儿来看待,又保住了名节,这究竟哪里不好,你倒说与我听听?”
“夫人说得句句都对,云巧人微言轻,一句也反驳不了夫人的道理。可是夫人对溦姐儿这孩子,除了道理,真的就什么都没了么?云巧想跟夫人理论的,是夫人的心。溦姐儿的心也是夫人给的呀,难道夫人眼里,除却名声跟贞节牌坊,再没有第二件事了么?”
一阵哀伤像场狂风那样,重重地把令秧卷了进去。忍耐它的时候让她不得已就走了神,听不清云巧后面的话究竟说什么。令秧在心里嘲讽地对自己笑笑,也许她已经真的笑出来了,笑给云巧看了:所有的人都有资格来指责她,说她薄情,说她狠心——她知道蕙娘虽然嘴上什么也不说,但心里却站在云巧这一边,好像她们都可以装作不记得溦姐儿这孩子是怎么来的,好像她们都已经真的忘了这孩子身上背着她的多少屈辱和恐惧。这说到底其实也只是她一个人的事情,如今,她们都可以事不关己地变成圣人,没有障碍地心疼那个苦命的孩子,任何一个故事里总得有个恶人才能叫故事,原来那陷阱就在这儿等着她。
云巧终于在对面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身子略略前倾,感觉她的眼神柔软地剜了过来:“夫人,不管你怎么嫌弃溦姐儿,只求你念着一件事。这孩子,她救过你的命。”
“你这是同谁说话?”令秧尽力不让自己的声音发抖。
“我知道我冒犯夫人了,我跪下掌嘴可好?”
令秧用力地站起身子,冲着门旁喊道:“小如,送巧姨娘出去。”
“夫人不用这么客气。”云巧恭敬地起来后退了几步,才转身扬长而去。她最后的眼神里,盛满着炫耀一般的恶意。
这一年的“百孀宴”那天,令秧就三十岁了。这件事还是谢舜珲告诉她的。
虽说当日为着退婚的事情,他们大吵过一场——不,准确地说,是令秧一个人同谢舜珲怄了好久的气,可是过一阵子,见也没人再来同她提退婚的事情,又觉得没意思起来,在某天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蕙娘,谢先生这么久没来了,可是家里有什么事情?
在这个家里,现今人人都敬着她,她只要一出现,无论主子还是奴才,原本聚在一起的人们都会自动散开,在她手臂尚且完好的时候,她从未感受过这种,因为她才会弥漫周遭的寂静。这种寂静不像是只剩蝉鸣的夜晚,也不像是晨露兀自滚动的清晨,这种寂静让人觉得危机四伏。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先把这短暂的寂静打破,率先垂下手叫一声:“夫人。”然后其他人就像是如释重负,先后行礼。她若是觉得某日的饭菜不合口,哪次的茶有些凉了,或者是中堂里某个瓶子似乎没摆在对的位置上……所有的人都会立即说:“夫人别恼。”随后马上按她的意思办了,她起初还想说:“我又没有恼。”但是后来她发现,人们宁愿用这种小心翼翼的方式打发她,他们就在那个瞬间里同仇敌忾,把她一个人扔在对岸,她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能保持沉默,顺便提醒自己,不要在这种时候又歪了身子。
只有对着谢舜珲,好像她才能想高兴便高兴,想伤心便伤心,想生气就摔杯子——因为只有他并不觉得,残了一条手臂的令秧跟往昔有任何的不同。不知不觉间,他们二人也已经相识了快要十四年。虽然谢舜珲年纪已近半百,在令秧眼里,他依然是那个潇洒倜傥,没有正形的浪荡公子——他头发已经灰白,她却视而不见。
“夫人三十岁了,我有份大礼要送给夫人。”谢舜珲不慌不忙地卖着关子。
“准又是憋着什么坏。”她抿着嘴笑。
“夫人到了日子自然就知道了。”
怕是这辈子都忘不了,前年,在她自己都差点忘记她的生日的时候,谢舜珲到唐家来拜访,在老爷的书房中,送给她一个精致的墨绿色锦盒。她打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