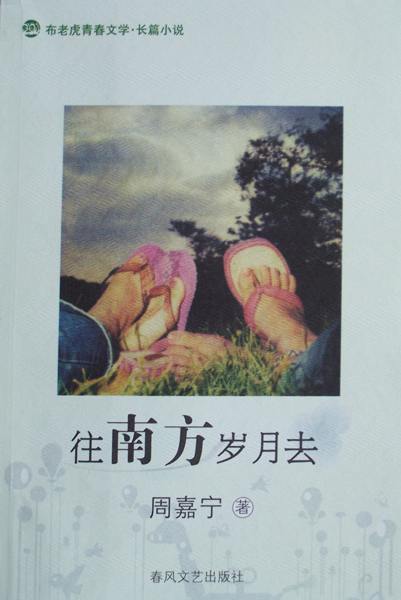南方有令秧-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夫人平日里可又跟你们说过什么没有?”令秧深深地看了门婆子一眼。
“老夫人前儿清醒了一会子,问我们听没听说过灯草成精的故事——”门婆子笑着摇头,“不过只一炷香的工夫便又糊涂了,夫人放心,老身会好生伺候着。”
令秧笑笑,松了口气。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这点省力,凡事点到为止,大家便都心知肚明。按说,有了门婆子,她才不必每天都来老夫人房里点卯,可不知为何,正是因为门婆子在这儿,她跨进这道门槛才不觉得心慌。
“可有旁的人来过?”令秧问道。
“没了。前几日是侯武去请的罗大夫,然后就在门廊上等着——也没让他进来。”
“这侯武现在跟罗大夫真是亲厚,每次都是侯武去请去送。听说私底下他还常去找罗大夫喝酒。所以连翘很怕侯武上他们家去。”
“这侯武现在可是蕙姨娘眼前的红人。”另一个婆子从她们身边经过,带着点嘲弄地笑道,“出差买办,迎送贵客,每样都是他——只怕过几日,咱们房里有事还使唤不动人家呢。”
“看您老人家说的。”令秧放下盖盅,“自从管家瘫在床上以后,满屋子里还不就只有侯武镇得住那起没羞没臊的小厮们,不指望侯武又指望哪一个。至于使唤不动的话儿,就还是少说吧。老夫人房里的事情最大,他要是这点儿事理都不明,我也早就撵他出去了。”
只见那婆子弯腰赔笑道:“夫人说得很是。”这时只见川少奶奶兰馨扶着自己的丫鬟迈进了门槛,令秧笑吟吟地站起来:“我就等着川儿媳妇来接我呢。”门婆子也笑道:“夫人今儿个要跟着川少奶奶临什么帖子?”
这便是连翘走后,令秧养成的第二个习惯。某天早上,她跨进川少爷和川少奶奶的房里,开门见山地对兰馨说:“打今儿起,你教我认几个字,好不好?”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与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于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其实兰馨是个不错的开蒙先生。起初,她们二人都以为,对方不过是凭着一时的兴致,坚持不了多久。可是三年多下来,谁也没料到,兰馨虽说教得随性,没什么章法,却也渐渐地乐在其中;而令秧一笔一画地,也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临了《兰亭集序》——“学习”这件事,对令秧而言,的确没有她自己原先以为的那么辛苦。每一次,清洗着手指间那些不小心蹭上去的墨迹的时候,总还是有种隐隐的骄傲。更何况,兰馨常常会淡淡一笑,语气诚恳地说:“夫人好悟性。”不过云巧就总是不以为然地撇嘴:“罢呦,她不过是讨好她婆婆而已,也就只有夫人你才会当真。”令秧不大服气:“她平日里那么冷淡倨傲的一个人,才不会轻易讨好哪个。”云巧笑道:“夫人如今成日家读书写字,怎么反倒忘了‘此一时彼一时’这句俗话了?进咱们府里这些年了,她可生过一男半女没有?夫人又不是不知道,川少爷房里那个梅湘不是个省油的灯,那小蹄子在夫人眼前还好,可是在房里,仗着生了个小哥儿张狂得不得了——眼看着就要爬到咱们川少奶奶头上来了。她若是再不忙着巴结夫人,还有旁的活路么?”
令秧只好悻悻然道:“什么事情一经你的嘴说出来,就真真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她喜欢这样和兰馨独处的时刻,兰馨的屋里没有孩子,川少爷更是很久也不会过来一趟——那房里每个角落都往外渗透着一种真正的静谧和清凉,喜欢搬弄是非的人自然天生就排斥这样的地方。虽然冷清,兰馨却也每天都打扮得很精致,泡上两杯新茶,研好墨,有时候再焚上一炷香。令秧便会觉得,无论如何,被人等待着自己的滋味,都是好的。
“等我死了,这方砚台,就留给夫人做个念想儿。”兰馨轻轻搁下笔,“把它从娘家带来的时候,横竖也没想过它跟夫人还有这么一段缘分。”
“年纪轻轻的,总说这些晦气的话。”令秧白了她一眼,做久了“婆婆”,她便忘了自己其实只比兰馨大两三岁。
“我可没跟夫人说笑话。”兰馨笑道,接着轻轻念出了字帖上的句子,“夫人与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于形骸之外……”
“虽说你给我讲过这是什么意思,”令秧有些难为情,“可我好像还是不大明白。”
兰馨叹了口气:“其实,这句话是在讲,他们男人过得有多惬意。他们也知道人生短暂,可是对他们来说,不一样的活法就是有不一样的滋味。拘束着点儿使得,疯一点儿也使得,他们通笔墨会说话,什么样的活法在他们那里都有个道理——不怪夫人不懂,天下文章那么多,并没有几篇是为咱们写的。”
令秧掩着嘴“哧哧”地笑:“依我看着,你的道理也不少。”静默了片刻,她还是决定说出来,“兰馨,按说,你这么聪明剔透的一个人,如何就是摸不透川哥儿的脾气呢——我不是埋怨你,只是替你不值。还是,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你就是没法中意他?”
“夫人。”兰馨的睫毛微微翘着,“今天的茶可还觉得好喝?”
她只得住了口,听了这话,好像不端起杯子也不合适。茶香的确撩人,她也只好笑道:“你这儿的茶,哪有不好的道理。”茶杯里的一汪碧绿挡在她眼前,她只听见兰馨静静的声音:“夫人不用替我担心。这几年我已经很知足。夫人愿意天天来我这儿写字儿,就已经是我最开心的事情;第二个,便是盼着咱们三姑娘能常回家来走走,在夫家顺风顺水,让我知道她过得好——有了这两个念想儿,我便再也不图其他了。”
令秧只好叹道:“也难得,你和三姑娘倒真是有缘分呢。”
令秧二十五岁了。细想,嫁入唐家,已经九年。
她常笑着跟人说,总算是老了。不过其实,照镜子的时候,她从来不觉得自己老。生溦姐儿时候的损耗这些年算是养回来一些,至少整个人看起来是润泽的。腕子上那只戴了多年的玉镯如今倒显得紧——她比十六七岁的时候略微胖了点,不过眉宇间的神情也跟着舒缓了,安静着不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总有股悠然,好像她在凝神屏息地听着一首远处传来的曲子。
所谓“百孀宴”,只是个说法,听着阵仗很大。其实真的统计下来,赴宴的不过四五十人而已。开席那日,天气晴好。送贺礼的人早已络绎不绝,川少爷一个人在中堂应付着各家的礼单子,张罗着给抬礼的人打赏派饭——所幸如今,府里有个得力的管事的——侯武,前后左右给管家娘子打着下手。令秧一大早便梳妆完毕,去老夫人房里叩头拜寿。她很小心,知道分寸,胭脂自然不能涂,她便轻轻地施了很薄的一层水粉。那粉是蕙娘不知拖谁带来的,据说在京城也是紧俏货色。只消打上一点,面色便觉得白皙匀净,看不出什么痕迹。老夫人被人搀扶进太师椅里,坐着发呆,着一身枣红色刻丝“如意”纹样的袄,滚了银边,再系一条石青色裙子,配着一头银丝和一对祖母绿的耳环,显得益发华贵。令秧事先知道了老夫人要穿戴的颜色,因此刻意地搭着枣红,穿了花青色,系着藤黄的裙子,听了小如的话,把老爷送的玉佩戴在裙子间若隐若现,玉佩的络子是墨绿色,小如非常聪明地在编络子的时候掺进去一小撮桃红的丝线,几乎看不出来,可是迎着阳光的时候,就是觉得那络子会泛着点说不出的光泽。除了玉佩和已经摘不下来的镯子,令秧并没有戴任何的首饰,就连头发也是梳了一个简单的梅花髻,银簪藏在发丛里。雪白的脖颈悄然映着满头未被任何装饰打扰过的乌发。正是因着这种简单,她看起来反倒像是一幅唐朝的画。
看到令秧浅笑盈盈地扶着老夫人坐下,满屋子受邀而来的各路孀妇们全都微微一惊:倒不是因为这唐家夫人生得国色天香——若认真论起姿色来,也不过是普通人里略微娇艳一点的,总之,女人们的眼光尤其苛刻,更何况还是一群因为没了丈夫因此必须冰清玉洁的女人。孀妇们面面相觑,当令秧大方地对她们欠身一笑的时候,她们因着这疑惑,还礼还得更加殷勤。这毕竟是做客的礼数,况且,人家唐府到底是宅心仁厚的大家子。作为宾客的孀妇中总还是有一两个人能沉默着恍然大悟的:说到底,这唐家当家的夫人,看起来实在太不像个寡妇。
要说她浑身的装扮也并不逾矩,举手投足也都无可挑剔地大方含蓄。没有一丝一毫的孟浪,可就是令人不安。也许就是脸上那股神情,悠悠然,泛着潋滟水光;眼睛看似无意地,定睛注视你一眼,潋滟水光里就“扑通”一声被丢进了小石子。那份惬意和媚态是装不出来的,她跟人说话时候那种轻软和从容也是装不出来的,这便奇怪了,同样都是孀居的女人——难道仅仅对于她,满屋子的寂寞恰恰是肥沃适宜的土壤,能滋养出这般的千姿百态么?
然后大家依次入座,并开席,只剩下蕙娘带着兰馨站着,指挥着丫鬟妇人们上菜。兰馨对这些事情委实笨拙,只好亦步亦趋地跟在蕙娘后头,冷傲的脸上难得有了种怯生生的神情。令秧的眼睛远远地追看着她,有时候兰馨一回头,目光撞上了,令秧便静静地对她一笑——在外人眼里,这笑容自然又是莫名其妙的:究竟能有什么令她愉快的事情?或者说,人生境遇已经至此,究竟还能有什么事情是令她如此愉快的?
跟着老夫人和令秧她们坐主桌的上宾,自然是族中或邻近望族里年长的孀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