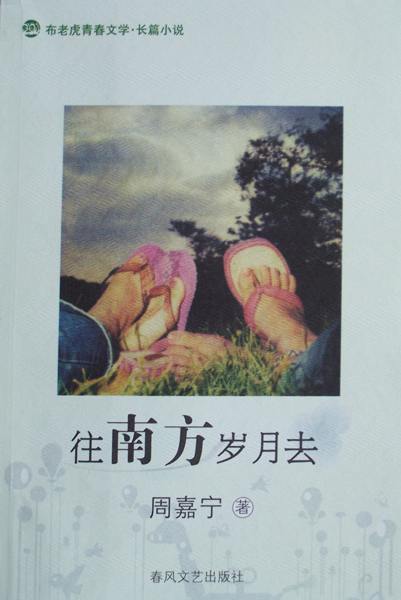南方有令秧-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她推开了。她听着他默默地摸黑下了床,听见他捡起衣服,他朝门边走的时候踢到了一张圆凳——他似乎赶紧停下来扶住了它。所以令秧确信他会守口如瓶。管家娘子默契地进来,静静地把他带了出去。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眼泪流了下来。因为有那么一刹那,应该是哥儿的脸庞贴在她怀中的时刻,她险些脱口而出:“老爷想喝茶么?”随后她好像真的看见了唐简,每次云雨结束的时候,他脸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忧伤。哥儿身上似乎也有——虽然看不见脸,可是他们手指交缠的时候她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这忧伤的源头是唐简,她的夫君,她在这似曾相识的忧伤里,安心地流着未亡人的眼泪。
她知道了一件事。她不再怕死了。
三日之后,唐璞的随从们又把令秧带到了祠堂。
六公端详着这命不该绝的妇人,清了清嗓子:“唐王氏,既然唐氏一族的香火要靠你延续,殉夫的事情,就暂且不提。”这妇人恭敬地叩了个头,清脆地回答:“令秧感激不尽。”就在此时,一只麻雀无声地飞过来,悄悄地停歇在祠堂的门槛上。
“只是现在,你须得当着列祖列宗起誓,安分守节,至死不渝。”
“令秧明白。”
“唐王氏。”十一公的嗓子里永远像是卡着一股浓痰,“你要知道,我唐氏一门有多少眼睛看着你。”
她不慌不忙地又叩了一个头:“令秧答应诸位长老,恪守本分,至死不渝,生是唐家的妇人,死是唐家的鬼。必定穷毕生之力,为唐氏一门换得一块贞节牌坊。”
不做唐家的鬼,又去做谁家的?她在心里对自己笑了笑。
再从祠堂回来的时候,蕙娘问她:“夫人怕是有好久没有见过娘家人了吧?我可以差人去带个信儿,这些天,他们若有空,过来府里住两日,陪夫人说说话儿。”
她说:“不必了。”
令秧是在谷雨的时候发现自己未见红潮的。她耐着性子等了四五天,才告诉云巧她们。管家娘子长叹一声,对着窗子双手合十,用力地拜了拜,念念有词:“当真是菩萨看着咱们呢。”蕙娘笑道:“罢呦,菩萨看着,只怕清算咱们的日子在后头。”虽然口吻讽刺,却是一脸如释重负的喜悦。云巧用力地抱了她一下,硕大的肚子顶得她透不过气,云巧含泪笑着:“我就知道你可以。我当初就知道,夫人就是有这种福气的人。”令秧默不作声,她没觉得有多惊喜,因为自从哥儿进她房里的第一个深夜,她便相信了——她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所有东西。至于她为何坚信满天神佛都会如此偏袒她,她也说不好。
传来了一阵笛声,让满屋子狂喜的女人都安静了下来。“谢先生又在吹笛子了。”云巧怔怔地看着窗棂——随着身子日渐臃肿,她脸上常常浮现这种神情,好像是没有往日伶俐了,可是令秧却觉得她愚钝些的样子更美。“好听呢。”蕙娘将五指伸展在自己眼前,像是打量自己葱管一般晶莹的手指,“难为他,把个简简单单的《点绛唇》吹出这么多故事,依我看,不比那些京城里的乐工差,这么聪明剔透的一个人,偏就不喜欢做正经事情。”管家娘子若有所思地朝向蕙娘道:“有件事我这几日总挂着,现在族中上下都盯着咱们府里的女人们,尤其是夫人,谢先生总在咱们家待着,只怕又有人要生事端。”蕙娘面不改色,但是沉默。云巧转过脸道:“人家帮过咱们那么大的忙,现在怕别人嚼舌头就叫人家走,这不是显得我们家太没良心?请他来,原本就是给哥儿请先生,旁人又能说什么呢!等哥儿亲事办了,什么时候能回族学里去念书,再请谢先生回去也不晚。”管家娘子苦笑道:“我也是想着这一层,若是咱们开口请谢先生去,真是没脸——只是这谢先生也有意思,来咱们府里两个多月了,像是越住越惬意了,昨天我看见他在后院墙根下头,跟浇园子的刘二有说有笑……”蕙娘笑了:“他自小就这样,走到哪儿,三不五日便混熟了。”“我是说,他不记挂着家里么?”管家娘子大惑不解,“他家难道没有父母家小?”
令秧好像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了,她知道身边的对话还在持续着,一直谈论着那个神明一般从天而降帮这群女人出谋划策的谢舜珲。可是听不清楚蕙娘回答了什么,然后云巧又好奇地问了一句什么……因为她心里突然掠过一缕似有若无的叹息。也许,保佑她顺利地怀上这个孩子的,不是菩萨,而是老爷。这念头让她微微一个冷战,却又迅速地柔软了下来。一夜夫妻百日恩,原来是这个意思。她不由自主地,像云巧那样,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然后又轻轻把手放回到了膝盖上,她恨这个动作。
哥儿的婚事迫在眉睫,老爷离世快要七七四十九天,难得新娘子家里的老爷夫人通情达理,同意在热孝期内匆忙完成大礼——谁也不想再耗上三年。这新妇娘家姓周,是池州人,算得一方富户。虽说比不得唐家的书香,可到底也出过两个举人。令秧听到云巧她们的话题已经转到这个婚事上来,只听得蕙娘笑道:“咱们谁也没见过新娘子,不过我倒听说是个美人儿,不然也配不起咱们哥儿。当年定亲的时候,老爷还犹豫着,觉得她是庶出,可是听说周家就这一个女儿,周家老爷太太都把她宝贝得什么似的,从小就在周家老太太房里长大,也就不提庶出的话了……我还记得,当日,先头的夫人劝老爷说:老爷想想看,若是有朝一日有人嫌弃咱们家三姑娘是庶出,不愿跟咱们攀亲,老爷会不会觉得可恶。”蕙娘停顿了半晌,“平心而论,咱们先头的夫人真是宽厚。只可惜走得太早。”管家娘子也跟着叹息,说谁说不是呢。
“走得早点有什么不好?”令秧手肘支着炕桌,慵懒地说,“活到今天又能怎样了?老爷殁了的时候她也过了三十,横竖拿不到牌坊。”一句话轻轻地丢出来,满屋子鸦雀无声。云巧急得顿足:“我的夫人,这话在屋子里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能给外人听了去的,赶明儿等哥儿的新媳妇过门了,你做婆婆的说话更不能如此没有分寸……”“我说错了不成?”令秧没有一丝笑意。蕙娘在旁静静地打了圆场:“如今夫人眼里,除却守节倒是没有第二件事。”众人只得尴尬地哄笑。一个小丫鬟就在这时候来了,说是唐璞差人送来了戏单子。管家娘子过去接了,捧给令秧,令秧怔了怔,随即笑着挥手:“你又欺负我不识字。”最终戏单子到了蕙娘手里,蕙娘笑道:“九叔倒真的有心,知道咱们家有孝在身,不好太热闹排场,又怕新娘子娘家亲友笑话,特意把他家的戏班子拿出来,哥儿喜酒的时候,想听戏的去他府上,倒真周全。”云巧像是吸了口凉气:“他家还真是财大气粗,养着一个戏班子。”令秧知道,唐璞这么做,还有一层原因,守孝自然是最冠冕堂皇的说法,但其实,即使老爷仍在,他们目前也未必有能力请戏班子。
蕙娘掩着嘴笑了出来:“叫我说九叔什么好,三天的戏,居然掺进来一个青阳腔的班子,这岂不是让人家笑话了,我们是乡下土财主不成?”管家娘子道:“蕙姨娘怕是有日子没听戏了,青阳腔现在红火得很,况且新娘子是池州人,青阳腔就是从她家乡来的,按说也不算失礼。这毕竟是九叔的人情,我们也不好太狷介……”“老爷最不喜欢青阳腔。又俗又嘈杂,也就是其中滚调还略微中听些。”蕙娘皱眉,“九叔喜欢青阳调也罢了,大喜的日子唱什么《失荆州》,造孽,这个换了,换成《结桃园》。加一出昆腔,《浣纱记》里《游春》那折,是断不可少的。”小丫鬟答应着,蕙娘又眼睛一亮,“对了,把我改过的单子也拿给谢先生看看,他可是个行家。”
令秧知道,蕙娘最喜欢听《浣纱记》,只是她也只能在戏单子上指点一阵,过过瘾罢了。到了正日子,她们几个,还不是因着守孝,绝对不能露面的。也许,能听见些隐约的丝竹声,蕙娘就可以在屋里悄声地哼唱上几句:“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令秧不懂,但是也觉得错落有致,美好得很。
每个人都热火朝天地忙着哥儿的大婚。然后就忙着给令秧请大夫诊脉安胎——自然是换了个大夫,只不过坚持对大夫说令秧受胎已有三个月。大夫自然觉得棘手,三个月的话,胎像未免太弱,于是不停地开各种安胎、调理气血的方子。时不时担忧这样弱的脉象,孩子未必能足月出生。大夫来了三四回,令秧自己也开始觉得,这孩子原本就是老爷的。
白天的事情归白天,夜里的事情,自然不同些。
令秧的贴身丫鬟被蕙娘换了,那是令秧被带去祠堂之后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令秧昏睡时候的事情。原有的那一个丫鬟,自从老爷病重之后,她父母便频频地上来府里,想把她领回去嫁人。当众人人仰马翻地围着被抬回来的令秧的时候,蕙娘没忘记做一件事,即是准了这丫鬟回家。没有别的原因,令秧从此就要带着秘密活上一生,身边那个人必须绝对可靠才行。新来的丫鬟原是老夫人房里的,名叫连翘。长得普通,也不见她跟任何一位主子多说哪怕一句话。也许是名字真的取对了,她最擅长的便是给老夫人煎药,一天几趟,什么火候,什么时辰,什么药引——任凭大夫的方子和指示如何复杂,也没出过丁点差错。后来老爷卧床不起了,煎药的事情自然也由她承担起来——常常出入府里的大夫们早已习惯直接把药方交代给连翘。只要是守着药罐,她的神情就安逸得不得了,无论需要多早起来多晚去睡,都是怡然自得,眼睛里也没有丝毫倦意。简直让人怀疑,她怕是希望府里每个人都常年病着才好。蕙娘静静旁观了几年,觉得在此时把她调到令秧房里,算是妥帖的。不知道是连翘太安静,还是令秧太粗心,从祠堂抬回来以后令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