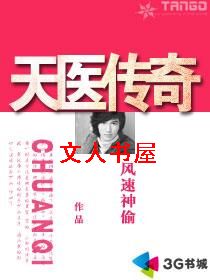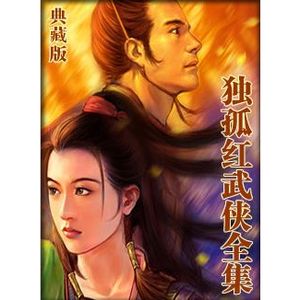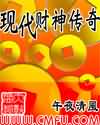忠武公传奇-第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生活,种田经商的还好说,读书人可就惨了。因为皇帝们说治国跟放牛放羊一个样,在立国后的一百多年里,根本就没有开科取士,你书读得再多再好也没有官做。赋诗填词不解温饱,回家种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改行经商十有八九要倾家荡产。也有饿得眼睛放花的读书人为了讨口饭吃,不惜失节去给皇上晋献治国良策,但皇上根本就不愿意看你用方块字写的策论,常常是把你绞尽脑汁的成果往火盆里一扔,操起一只烤羊腿一边啃着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不用看了,你说来我听听。这说明大元朝的皇帝基本上是用耳朵办公。总之,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人人皆有。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一等公民蒙古王,三妻四妾住洋房;
二等公民千夫长,封妻荫子居庙堂;
三等公民洋和尚,宝马轻裘烤全羊;
四等公民摆道场,绫罗绸缎饮琼浆;
五等公民制膏汤,江湖行走疗枪伤;
六等公民侍蚕桑,机杼声声到天光;
七等公民田间忙,春夏秋冬忍饥肠;
八等公民卖笑娼,七老八十也上床;
九等公民读书郎,望梅画饼苦夜长;
十等公民是丐帮,天天日日喝残汤。
读书人的地位如此低下,但总不能活活饿死吧?没有办法,他们只好不要斯文,改行做起戏子来,写写戏文唱唱散曲换点小钱,这便是元曲传世的由来。
大元朝立国之初,在国家管理方面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公章换了;二是诏告了全国人民,你现在不是大宋朝的人,而是大元朝的人了。一些重要的部门虽然也派了蒙古族官员,但他们根本就不管什么事,整天不是喝马奶酒啃烤羊腿,就是在衙门口的校场上摔跤玩。有时候心血来潮要履行职责,却总是把事情搞得令人啼笑皆非。当时,忠武公还是大理寺的高级评事,便常常要为一些案子的裁判与蒙古族官员发生争执。比如说抢劫杀人案吧,自古以来就是恶性刑事案件,当判斩立决。但蒙古族的官员却说,你有他没有不抢怎么办?他抢你不给不杀怎么办?罪犯不但不杀,还要当庭开释。再比如说强纳他人妻女的犯奸案,依律当判徒刑脊杖,蒙古族官员又说,美女当为英雄妻。不但当庭开释,还要奉送一张支票做彩礼。忠武公与之争辩,他就会说,要不叫他们在院子里摔一跤,看看到底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忠武公实在是干不下去,只好和其他的读书人一样,也改行当了戏子。
改行当戏子的忠武公反而成了抢手货,各个剧团都争相聘用。一是因为他有一部长及腹脐的白胡子。那时候人的寿命也就五六十岁,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好胡子,就算是有个把白胡子老头,受着“发肤乃父母所授”思想的约束,你出再多的钱他也不会卖给你。因此,戏台上的白胡子基本上都是用野麻漂制而成,失真不说,演员也不愿意戴。因为戴假的就要剃去真的,这是为世人所唾弃的行为。而老生的角色又是每部戏里不可缺少的,让忠武公来饰演那真是再好不过。二是忠武公一千多岁,戏里的事情他都知道,有些甚至还是他的亲历亲为,让他来饰演排练的环节都可以省略,大大地压缩了成本和开支。
忠武公先是在汴梁大元朝河南梆子剧团,演的第一出戏叫《李陵碑》。这部戏说的是大宋朝雍熙年间,辽国大军从雁门大举进攻宋朝。太宗皇帝派出三路大军征讨辽国。杨令公杨无敌为西路军副将,受主将潘仁美节制。本来是凯旋而归,但在班师回朝的路上,杨无敌为了掩护南迁百姓,舍身断后被十万辽兵围困在两狼山。大坏蛋潘仁美不发援兵,大忠臣杨无敌突围未果。身负重伤的杨英雄至死不降,退至苏武庙李陵碑前,毅然触碑死节。在这部戏里,忠武公因为有一部好胡子,自然是饰演杨大英雄杨无敌。演了几场之后,社会反响良好。但是,忠武公的心里却堵得慌,他找到编剧和导演说,这部戏不能这么演。杨大英雄根本就不是触碑死节,而是重伤被俘,绝食而亡。他被困两狼山,不发援兵的责任也不在潘仁美,而在监军王亻先。这些事情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你这样编导是篡改历史。
导演是个富有才气又很帅气的年轻人,要是大元朝没废科举,他弄个金科状元也不足为奇,何至于沦落到“九等公民”的境地。于是,他便懒洋洋对忠武公说,老余啊,戏剧是一门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如果照搬历史,就演杨大英雄是自己饿死的,那有什么震撼呢?潘仁美当时是北伐主帅,王亻先只是个小监军,官儿还没有杨英雄大,真实再现也是没有什么戏剧效果的。
忠武公反驳道,难道就因为要寻求震撼和追求戏剧效果,就可以黑白颠倒,混淆是非吗?我们虽然是靠唱戏混饭,但总不能昧着良心篡改历史吧?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潘仁美和他的子孙后代呢?一向实事求是的杨大英雄九泉之下也会于心不安呐。
年轻的导演气愤地说,叫你怎么演你就怎么演,啰嗦个屁呀?再啰嗦就让你去演死尸,看你还有什么话说。要吃饭的忠武公没有办法,没再反驳,但演到最后磨磨蹭蹭的就是不肯触碑。等不来**的观众们倒彩连连,气得导演干脆将剧本的顺叙结构改成倒叙,戏名也改做《杨家将》,第一场就让杨大英雄触碑而“死”,真的就成了一具死尸。佘太君带着儿子媳妇们趴在他的身上哭,鼻涕眼泪糊他一脸。尤其是那个刀马旦“佘太君”,呼天抢地的十分入戏,差点没拍断他的肋骨。后面都是杨大英雄的子孙们如何复仇的情节。而“死”后的忠武公则被安排反捧着铜锣到台下去点头哈腰地讨钱。大家都知道,忠武公对待什么工作都是十分认真的,而且因为他的老态,总是能讨到更多的钱。这样一来,他的戏份便越来越少,最后成了专职的收费员。忠武公自己也慢慢的感觉到,剧团是在利用他的老态来博取观众的同情。忠武公自然不肯,愤然离开了这个河南梆子剧团。
离开河南梆子剧团,忠武公又被一家京剧团录用。这家京剧团的看家戏是《长生殿》。说的是大唐朝玄宗皇帝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国势强盛之后,寄情声色,下旨选美。发现宫女杨玉环才貌出众,于是册封为贵妃。两人以金钗为定情信物,海誓山盟。自此,杨氏一门女宠男信,鸡犬升天,终致“安史之乱”。杨玉环香消马嵬坡。叛乱平定,玄宗皇帝回到长安,日夜思念杨玉环,闻铃断肠,见月伤心,情动上苍,玉帝传旨,两人月宫相会,永结同心。
又是因为忠武公有一部好胡子,导演自然是安排他饰演误国奸臣杨国忠。忠武公演着演着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在玄宗皇帝身边当劝农使的那些日子,想起了大奸臣杨国忠当年对他的残酷迫害,心里那个憋屈真是无以言表。于是,忠武公再次旧病复发,给导演又提了一大堆问题。一是坚决不肯饰演大坏蛋杨国忠,坚决要求饰演原本角色劝农使余最;二是严正指出剧情与历史不符,杨玉环根本就不是什么宫女,而是玄宗皇帝的儿媳妇。玄宗皇帝实际上就是一个“扒灰佬”;三是强烈要求剧情中要有李白这个角色。这个导演是个老童生,耐心地解释道,你有一部无可替代的好胡子呀,是饰演杨国忠的不二人选。《长生殿》是一部爱情戏,劝农使这个角色没有必要补入剧情,否则的话对玄宗皇帝与杨玉环忠贞不渝的爱情主题是极大的冲淡。至于说还原杨玉环的历史本原,补入李白这一角色,更不可能。谁都知道李白和杨玉环是有一腿的,这样一来,不是要给一号人物唐玄宗戴一顶大“绿帽子”?在戏剧中对一号人物正面形象的损害是大忌,万万不可。有了前车之鉴的忠武公知道言多无益,但是杨国忠这个大坏蛋他是坚决不肯演的。于是,他主动对导演说,那还是让我去收钱吧。我保证比别人收得多。
在大元朝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有些浮躁,依依呀呀的京剧慢慢的就没有什么市场。相比之下,暴跳如雷的秦腔反倍受欢迎。京剧团生意清淡最终倒闭。忠武公又跑到长安秦腔剧团去混饭。秦腔是发源于三秦大地的一个曲种,质朴粗犷,唱到情深之处,荡气回肠,令听者热耳酸心,泪雨纷飞。有时唱到情难自禁,真是要死要活,弹的唱的都不顾章法。因此,秦腔也叫“乱弹”。那时候,凡是听秦腔的,人人都要带着一条毛巾,散场之后那毛巾能挒出眼泪来。忠武公认为秦腔很对他的口味,这个秦腔剧团的看家戏又是《感天动地窦娥冤》,更对他的口味。在这处戏里他饰演的虽然只是一个错斩窦娥的昏官角色,但他一板一眼一丝不苟。这一处戏他前后唱了上百年,最终因为一次失误而被剧团除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大元朝的末年,皇帝也慢慢的有了些文化。有一回,皇宫里调演他们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大家都十分激动,心想这回苦日子算是熬到头了。因此,全体演职人员都十分卖力,忠武公自然也不例外。戏到**之处,饰演窦娥的演员正声情并茂地唱着这样一段唱词:
这官司眼见得不明不暗,
那赃官害得我负屈含冤。
尚若是我死后灵应不显,
怎见得此时我怨气冲天?
我不要半星鲜血红尘溅,
将热血俱洒在白练之间。
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得见,
还要你六月里雪满阶前。
这楚州要叫它三年大旱,
那时节才知我身负奇冤!
………………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唱到此处,按照剧情的发展,忠武公饰演的那个昏官角色应该是从桌上拿起令牌往地上一掷,大声说道,午时三刻已到,斩!但是,当时忠武公已被“窦娥”的苦音二黄散板唱得泪水涟涟,情难自禁,竟然鬼使神差地拿起令牌一折两截,涕泪横流地说道,斩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