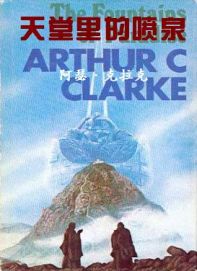男人的天堂-第8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小的时候,村里人多吸这种烟袋,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我爹晚上烦的时候把烟袋锅儿凑到火苗不大的煤油灯上去点烟一袋接一袋“吧嗒吧嗒”吸个不停的形象,忽有一口呛入肺里,便不住地咳直至涕泪交加。
我娘便止不住地埋怨呛,我爹便只顾嘿嘿地笑,我娘便逗我,贤儿是个好孩子,长大了不抽烟,我便奶声奶气地说不抽,我爹和我娘便笑个不停。
埋怨归埋怨,我娘从未真正反对过我爹吸烟。在她的心目中,有着跟村里绝大多数女人一样的观点:嘴里叼着旱烟袋,旱烟袋下面系一只做工精致用来装烟的荷包,绝对是一种标准的男子汉形象。
女人因此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既崇拜又自豪的表情丝毫不会亚于现代人对于明星的狂热,因为旱烟袋和荷包多是女人送的定情信物,不仅体现了一个女人的品味和技艺,而且显示着两个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更重要的是吸烟者抽的烟多是自家产的并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即使自家产的,也多是些烟骨和及早脱落的底烟叶子。吸烟者却说,这种烟虽差点儿,却是烟身上劲儿最足的部分,其香味绝对强过小心翼翼才能晒出来的油黄黄的二烟叶子。
其实,又何尝如此,油黄黄的二烟叶子是可以多卖钱的,一家人的油盐酱醋总离不了这些钱。
到了我该吸烟的年龄,烟袋已换成了烟斗。烟斗多用坚硬的木头制成,叼在嘴里比之烟袋又潇洒了许多。这两种物事现今已成为古董,据说一件上档次的价值上万元。
烟袋换烟斗完全是受了电影的影响,那时候轮番放映的多是英雄的故事,经常有英雄手持烟斗的潇洒镜头,就象当时的电影本身让村里人感到新颖、好奇、新潮,于是便争相效仿,如果有人能得到一只精美的烟斗必会首先在公众场合得意洋洋地使用,几乎能引起所有人的注目。
千万别不相信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不可预料的,记不清的哪天开始谁先有了第一只烟斗,村里人便纷纷通过各自的渠道和方式去挑选烟斗,而且速度快得惊人,在绝对不超过一个周的时间内,村里的吸烟者手里就都换成了烟斗:瓷的、木的、铜的;红的、紫的、蓝的;雕花纹的、镂图案的、带猪牛羊之类常见动物头部造型的,不胜枚举,品种多样,花色各异。
仔细甄别一下,做工精致的多是经济尚来得及通过求亲告友从外面捎来的,实在困难的也必备一只,不过只能自己去动手,虽做工粗糙些,但会在造型上更别致一些,论美观大方并不见得逊色到哪里去。至此时,烟的质量似乎倒是降到了从属的地位。
由于人的心眼儿跟烟斗的花色品种一样存在着差异,心眼儿多的只要看好了别人的便要千方百计地谋到手,或购买或交换或打赌讲输赢,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心眼儿少的并不是真少,只是差在反应的快慢上,回到家里反复思量或者事儿刚完,已觉得自己吃了亏便要反悔,白赚个赖皮的名声。
在我们那个地方,不讲信用是最令人厌恶的。既要反悔,便要准备闹翻脸皮,偏又碰上分明自己吃了亏却非要以为沾了便宜者涎皮赖脸地拒不肯反悔,对方再是个自称英雄敢于仗义执言者,偶有言语不和,便会孩子一样发生格斗。
格斗屡有发生,好在地点选在了野外,而且事先有了各自家人不准参加团斗的约定,即使碰破了脸磕伤了胳膊也只能自认倒霉,各自以最合适的谎言来骗取家人的信任。要不然,万一有哪家的家人参加了团斗,不闹到老婆哭孩子叫打翻了天那才叫怪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烟斗被卷纸烟所取代。
所谓卷纸烟,村里人又称之为“纸烟”:随便地找一块宽约两指长约十几公分的小纸条,譬如条件好的人往往去买那些既白且软又卫生的封窗纸,而条件差一点儿的则常常从学生正反两面儿全用尽了的作业本或者废旧报纸上撕下一片,按照标准儿整好形状,卷成喇叭筒状,放上适量的烟沫或烟丝,把口用手捻紧便可以点吸。
吸纸烟确比抽烟斗方便了许多,只要一沓儿纸片随同烟草装入荷包,便既赶了时髦又免去了时常忘却带烟斗或烟斗携带不方便的麻烦。我由于恪守了小时候的诺言,没能亲自经历抽烟袋、烟斗和吸纸烟的阶段。
事实上,纸烟和烟卷儿几乎是并行的,有的人甚至至今仍在吸纸烟,但烟早已不是过去的烟骨和底烟叶子,而往往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烤烟叶子,而且要经过香料或料酒的泡制,其味道远远超出了现在不少几十块钱一包的高档烟卷儿。
但当时的烟卷儿千真万确是在纸烟兴起之后才传入我们村的,先是七分钱一包的“葵花”“金鱼”,那是村里有身份的譬如村干部或者家里办丧亡喜事儿接待客人才能够吸上的难得的奢侈品;后来又有了三毛八分钱一包的“蓝金鹿”和五毛钱一包的“大前门”,虽仍不带过滤嘴儿,在当时却只有公社一级的干部才能抽得上,这些烟现今市面上已难得能见得到,有不少人或许因为当初没能享用到便产生了恋旧情结,时常不无遗憾地说,那才叫真正的烟卷儿,如果算上物价上涨的因素,足能够抵得上高档烟的价钱;再后来,人们更加注重卫生和健康,香烟都带了过滤嘴儿,品种也日渐丰富起来。
我开始吸烟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村里人的油盐酱醋早已有了保障,谁也不会再去在乎卖烟叶儿赚来的这俩小钱儿,烟草的种植也因效益的问题慢慢绝了迹,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对烟草的需求。
说心里话,我学吸烟似乎没有任何目的,或许原该如此,便可有可无地偶尔买一两包拿来吸,都是块儿八毛的价儿,三天也不过一包的量。
但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挣工资吃国家粮的人吸烟的档次自然要略高一点儿,在村里有人给我敬烟时,我常说抽我的吧,说着便颇自豪地去兜里掏常只剩下三五根的烟盒。
敬烟者便尴尬地笑着说还是先吸好的吧,经常碰到我的烟有不够分的情况,我便把烟盒随手团成一个团儿,装作不经意其实非常在意地扔掉,伸了手便去接试探着递过来的档次稍差一点儿的烟,然后故意拖延掏火的时间待别人提醒着才突然记起似地装作没有一丝架子地去借别人正吸着的烟头儿引火,人家自是不肯,非要忙掏火帮着点了,才满满地吸一口,在嘴里稍憋一会儿,而后慢慢地吐出去,绝不让一丁点儿的烟进入肚里。
就这样反复演着戏,不觉竟上了瘾:一旦闲来无事,就要去掏衣兜,摸出烟盒,轻轻地把烟盒屁股一弹,抽出一根燃上,深深地吸两口,心里便会感到莫名的享受;而若是兜里没了烟,心里就会急切的空落落的不停地去掏兜,象是会有奇迹发生似的,常因此而掏破了衣兜;迫于无奈,只好涎着脸去向别人暂且讨一根,而且有一句振振有词的理由,烟火不分家嘛;不分家也不能常做,沾了一丁点儿小便宜,却要搭上脸皮,不划算。
因此,我临出门前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便是检查烟火是否带齐,因总担心自己会忘记了常常在心里不自觉地念叨着“烟火,烟火”,这样毕竟向人讨烟的机会才少。
那一段时间,我吸烟还是不讲档次的,也少去关注周围的变化,同样是烟,好烟劣烟能有多大分别?只是烟抽得恰如丽萍所说跟吃了一般凶。即使这样,我也没能找到那种烟能解愁的功效或者象人们传说的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早晨空腹的时候抽醉了倒是常有——脑袋晕乎乎的恍惚一下子就突然失去了记忆,必需要好长时间才能逐步恢复过来,却还是要抽,仿佛已经离不开了。
我是一个表面温和内心特犟的人,凡事着了瘾必伴随一些不良习惯,譬如这吸烟,自打着了瘾便拼命地吸,尽管丽萍始终不断地态度并不是太坚决地反对着,我还是渐渐地养成了这样的一些习惯:
饭前必要吸一根,否则即使美味也常常没有了味道;饭后当然还要吸,否则心里就会象丢失了物件一样不安生;睡前更要吸,否则不仅觉睡不安稳,而且会整宿地做梦,早晨刚起来已累得头晕脑涨,于是披了衣又吸,常烫坏了衣被,惹得丽萍老大不高兴,小嘴儿噘得能拴住头驴;只要闲来无事或手头无活就要吸,这似乎已成了我的一个下意识动作。
有了烟瘾,吸烟常不分场合,有了想法就吸,有人结伙时吸得更多一根接一根连续不断地吸,常搞得周围烟雾缭绕,烟味刺鼻,连身上都攒满了烟味。
直接受害者自然是自己的妻小和要好的朋友或者只是在一起办公至多办公之余相互吹吹牛并没有多少真话的同事,他们也吸,只是频率不高,最大受害者只能剩下自己的妻小,女儿尚小不懂事,便只有丽萍了,她也因工作或生活方面的原因渐渐地由皱眉、挤眼、噘嘴儿、心烦意乱地坚决反对而习惯了,不再去做着意地过多地关注。
人的注意力往往会因为身份或地位的变化而发生转移,做了镇长后,她对我的管束愈见松了,因为她即使要管也已经无此精力,反而经常隔三差五地给我带回三两条高档香烟,也算是对我的一种补偿吧。
难怪人们常说穿衣穿牌子抽烟抽品牌,穿牌子抽品牌多不需要自己掏腰包,不仅省去了一大笔费用,而且这好烟终究不同于劣烟,吸到口里就是不一样。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讨厌地去过多地关注烟的来路——何必呢?那是人家的本事儿,只要有好烟吸就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儿,吸烟者自是在众人既羡且妒的目光中高大潇洒了许多。
多是因为这种感觉,我的烟也在丽萍如愿以偿地做了镇委书记后换成了档次较高的且牌子还算固定的烟,低于这些品牌的烟再绝少去抽,比这更高档的则象小时候过年吃饺子或改善生活那样抽掉了不少。
这当然需要花掉许多钱让人心疼,心疼归心疼,但我绝不能象其他当权人的“家属”那样拿去

![[综]神一样的男人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0/4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