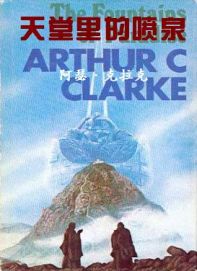男人的天堂-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指指点点时的丑陋嘲弄和唾沫星子纷飞的壮观场面,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连我自以为激情饱满的授课也变得索然无味,我不能误人子弟,便请了三个月的假,我知道自己在逃避。
到这里,必须提我的大舅哥了,因为我的所谓病假开始后,丽萍便托他照顾我。
说是照顾,不过是一日三餐自己不用动手就有了着落,除此之外,他连话也很少跟我说,偶尔的三二句,声音也压得极低,常让人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凭猜测,大概多是些下一顿想吃什么之类的话题。
刚开始,我还因为听不清无法回答而着急,慢慢地,我发现他的那些一连串的疑问句反问句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回答,他也不在乎你是否做了回答。他似乎已习惯了孤独,正常的营业之外,便是不停地整理茶箱,之后就搜肠刮肚地去想一些新鲜的吃的喝的东西。
他的食欲总那么好,只要喜欢吃的东西,即使再油腻也能百吃不厌,而且从不多辩驳。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嘴馋”一词,他认为嘴馋就是需要,需要就必须吃,何苦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而我却认为,人该注重生活质量,质量里不仅包括吃,还有吃之外的许多东西。所以,吃跟其他所有东西一样让我索然无味,自然说不清自己想吃什么。
如此的两个人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却非要放到一起,便不难理解我的情绪越来越暴躁了,常莫名其妙地冲他吼:吃,吃,就知道吃,难道连脸面也可以不要吗?
他同样会莫名其妙地瞅瞅我,懒得搭理,任我吼。
终于有一天,他烦了,就象拎小鸡似地拎着我,把我扔到他的库房里,锁了门自去。
我拼命地叫喊着,拣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他只不理,到吃饭的时候才从窗缝里塞一小块馒头和几根咸菜。我暴怒着,自不会吃,累饿交加终于昏昏然睡去,也不知过了多久。
醒来之后,体内的那股烦躁不安的感觉居然不见了,唯一的欲望就是吃东西,或许原就是饥饿把我弄醒过来。他把已奄奄一息的我从牢房一样的库房中拎出来,殷勤地招待我吃喝,我虽仍愤愤不平却已没有恶感。一阵狼吞虎咽之后,胃总算得到了满足,我美美地躺到床上,斜睨着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其实,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根本浮不起任何东西。
他咳了两声,又过了许久,才忽然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都是脸面惹得祸呀,中国人哪,太好面子了,只要过得舒心,又何必非要争个高低上下呢?
人都有个思路顺畅或阻滞的时候,只要思路顺畅了,即使再笨嘴笨舌的人也能说出一大篇哲理;反之,即使再伶牙俐齿的人也会变得结结巴巴不可理喻。
此时,大舅哥便出现了这种状态,他已打开了话匣,似乎不把话讲完已不能自制。他的表现着实令我惊疑不已,近乎木讷的他居然有如此出众的口才,虽然声音仍压得极低,语气也波澜不惊,但我仍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忙坐直了身体,认真地听他讲下去——
其实,我脑袋并不象父母所认为的那样笨得不堪,至于学习成绩不好,怪不得脑袋,也怪不得那场热病,要怪就只能怪那个发生于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的故事:
那时,学校里的公办教师只有我们班主任一个,他理所当然地还兼着这个小学校的校长,他的伙食便由每一名学生的家长轮流管,他于每年年终结算一次,付几块钱的伙食费。
因为尊师重教的传统,没有几位家长在乎这几块钱的伙食费,他们大多把管老师饭当成一项义务来看待,而且总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老师吃。
轮到我们家管饭,我便提着盛放着母亲精心准备的诸如鸡蛋蒸咸菜、油爆花生米、肉丁炒芹菜茼蒿之类的小菜和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的小竹篮去给老师送饭。
这样的饭菜,我们家连过年都不舍得吃,所以我总馋得流着长长的涎水,不断地就要用已擦得油光发亮的衣袖擦一把。实在馋得不行了,我便做贼似的掀开盖在竹蓝上面的白纱布偷几粒花生米或几块肉丁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嚼着,又总疑神疑鬼地怕大人瞧见给父母告上一状惹来一通训斥和责骂。
我实在是一个馋孩子,却又不肯承认,便常常想象其他孩子也在偷嘴借以为自己偷嘴这个极不光彩的行为找理由。
不过,那些油光光的白面馒头即使再诱人也动不得,因为破了整容易露馅,只有在老师吃过之后去取竹蓝时才能急匆匆掰一块快速送进嘴里,越急咀嚼起来越慢,而且常噎得胸口生疼。在完成了上述有关动作之后,我几乎以百米跑的速度进了校园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
校园并不算大,五个年级不足一百二十人。正是晚饭时间,民办教师和同学早已走光了,校园里静悄悄的,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手心汗津津的,心脏似乎要从嗓子眼里蹦跳而出。我怯生生地喊着老师,轻轻地推开了班主任宿舍兼办公室的那间小屋的门:班主任与我们村的小寡妇搂在了一起,正嘴对嘴地啃着……见我进来,两人旋即分开了,小寡妇两手捂着脸,似乎这样我就认不出她来,而班主任则故作和蔼地问,饭好了吗?
我放下小竹篮,逃一样跑开了。待我按他指定的时间去取竹篮时,他再三叮嘱我,一定不要乱说,连父母也不要告诉,并许诺让我当班长,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梦想。但我后来还是告诉了母亲,因为他那天吃的实在太多,根本没给我留下偷嘴的机会。
母亲自不会信我,反嫌我胡说八道,非要拖着我去向他道歉,逼我连说了三遍,我什么也没看见。
他倒很大度,满脸笑意,不停地替我向母亲求情,孩子不懂事,不要过于责备他。
到后来我才明白,母亲那时绝对已从学生家长们关于老师饭量大增的风言风语中悟出了什么。
理所当然地,我也没能当成班长。从此,我便开始恨他,因为恨,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令人讨厌,也包括曾令我崇拜不已的他说话的姿势和语气,而且眼前总要浮现出他与小寡妇的那一幕,“流氓”一词象在我的脑袋里扎了根似地疯长起来,尽管当时我根本就不懂得“流氓”一词的确切含义,但我认定必是最贬义的词便用到了他的身上。
实事求是地说,他确有一套独到的教育方法,譬如,为了鼓动学生用功学习,他在自己棉袄的内面缝了一个小塑料袋装上几块猪头肉或几粒油炸花生米,讲课的间隙便掏出来吃,说只有用功学习将来才能过上他一样的生活。
这在当时非常具有煽动性,但连这也成了我讨厌他的理由。因为讨厌,加之那场热病,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很快便由前三名跌到了倒数第一。倒数第一最没有面子,却是我当时认为的能够反抗他的唯一手段。待到离开他上了初中,我发觉自己已落后太多,在学习上已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
曾听一位老私塾先生说过,教育孩子就跟养小鸡似的,成就起来也是一窝一窝的,我们那一年级学生不仅打破了我们村多年来没有大学生的记录,而且一口气就考上了八个。
在全村既羡且妒的赞誉声中,我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但我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我决定出去闯一闯,我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混出个人样来。所以说,我当时的“失踪”完全是蓄谋已久的。
2
离家出走前一天,我心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无论怎么努力都似梦非梦似醒非醒。约莫凌晨一点左右,终于下定了决心,我便悄悄地起了床,破例把床铺收拾整齐后绕着我家的老屋转了九圈,颇有点儿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走出去”,至于要去哪里我自己也说不清,只听说南方已经改革开放了,出了村便只顾往南走。到中午的时候,我仍被那种悲壮的感觉激励着,迷迷糊糊不知到了何处,只觉两脚生疼便在路边的树荫下停了下来。要不是肚子不合时宜地乱叫,我甚至不会想到人还要吃饭,更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不名分文跑出来的。
我找了一家有门头的房子仔细看了看,才知道自己已来到了我们邻县的一个乡驻地。那时候的北方改革还刚起步,不少东西仍在统购统销,个体私营尚处于半明半暗的境地。找遍了整个乡驻地,唯一的饭店便是乡供销社饭店。
饭店的生意并不好,两个穿白大褂的女营业员正懒洋洋地斜倚在椅子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尽管饭店的正中央高高地地悬挂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巨制牌匾,她们对到来的人却没有丝毫的热气,居高临下地叫喊着,倒象是人家欠了她们钱不还似地不耐烦,虽然这样的人不多,虽然他们多是询问几句便匆匆离开。
我渐渐悟出了其中的门道,她们实在不愿有人来打扰,因为待人离去后两人又能有鼻子有眼儿地说笑了。偶尔有几个到饭店吃饭的,都是穿四个兜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吃的简单又节约,没有多少剩余。看得出来,偶尔的这几位应该算是地道的熟人,因为她们的脸上能够拢起一团笑意,虽然多少有点儿勉强,毕竟声音轻柔温和了不少,间或还能与之开几句半色不黄的玩笑。
后来,我对此进行过专门地了解,她们多是有背景的女人,饭店的效益与她们的固定工资没有任何干系,连经理都必须让她们三分。
显是我在门口长时间的徘徊观望惹恼了她们,其中的一位扔给我两个干巴巴的白面馒头,不耐烦地嚷着赶我快走,她必是把我当成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叫花子。准确地说,不是当成,而就是,那时的我与叫花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意识到,吃饭问题将是我今后必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在回家还是继续走下去的犹豫中,我来到了一座小县城。小县城有两三个乡驻地那么大,零星的几座楼房高高在上而又冷漠地矗立着。
时已华灯初上,不争气的肚子又闹腾起来,我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县供销社宾馆,宾馆门前的�

![[综]神一样的男人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0/4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