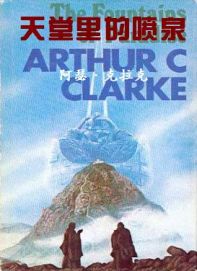男人的天堂-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说,条件好了,穿好一点儿不算什么。
她说,穷家富路,你们外面人应酬多该穿好一点儿,我一个农村婆穿好穿歹能有什么。再说了,我们儿子将来要上学要娶媳妇,哪一样不需要钱?俺可不能让他象咱们。声音里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我衣锦还乡时,阿秀的经营已初具规模,可以说,这完全是她一分一分积攒的结果。为此,她正打算退包土地,雄心勃勃地要开一家综合批发部。
不要以为她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女人,为了我,她宁肯舍了自己已成竹在胸的计划。
到校办工厂后,阿秀很快便适应了环境成为先进生产者,独对不到二百元的工资不满,她常计算并感叹着自己收入上的差距,却又唯恐影响了我常要反过来安慰我,她说,钱这东西,就是个穷种,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她第一次提到了死,她迷信,从不提这个“死”字。之后,便常提了。后来再去细品她那一段的表现,总会让人感受到一股隐隐的悲哀。
就在这时候,我母亲的一场大病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积蓄:她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而且克尽孝道,惹得同病室的老人们直夸我母亲生了个好女儿。
她私底里曾对我说,人世间最沉重的债,就是人情,金钱花掉了可以再挣,而人情却是挣不来的。所以,她绝少求人,万一迫不得已求了人,必见日里念叨着还人情。但为了母亲的病,她不惜四处求人,这也算是人情吧。
为了补贴家用,她利用闲暇时间跟人学编草编,尽管别人都夸她手巧,她却总嫌自己慢,虽才学了不长的时间,她显然已把草编当成了一个赚钱的差事,而且似乎要把全天下的钱尽数挣到我们家里。
然而,未及阿秀的草编对家境起到作用,我副校长的位子又被挤掉了:一腔热情倏然而灭,在外面的时候,还能故作平静、大度、潇洒;回到家里,便要无可抑制地爆发了出来,毫无理由的寂寞、恐惧、暴躁、竭斯底里,看什么都不顺眼,我居然把阿秀的草编踩了个稀巴烂,清醒过来自然只有尽赔不是的理儿。
毕竟是半个月没日没夜的充满了渴望的心血,阿秀好长时间没有吱声,两行清泪莘然而下,却只有到情绪总算平静下来才幽幽地说,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还是理解和信任。难以置信,她竟能说出如此极富哲理的话!只闪念间,她又说道,或许我愿不该跟着来的,是我害了你。
这话至今想起来仍在无情地敲打着我的良心,但当时的我肯定是毫无理智的,只认作是农村婆娘的唠叨,所以我粗暴地吼起来。当然,阿秀的“是否送一点儿礼”的试探性的建议也被我一概当作幼稚而粗暴地否定了,虽然,其时,我也不知该咋办,虽然阿秀有足够的耐心,再三强调“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愚妇之见!果依愚妇之见,或许……?为时已晚。
我不否认女人的细腻,也不敢恭维女人的理解力,就因为阿秀至死也没弄清丽萍的行为。其实,何止阿秀这样的弱女子,我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又何尝不是呢?
从那以后,阿秀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尽管她仍一如既往地劳作着,但我能感受得到她内心的剧烈争斗;她眼神怪怪的,凭我对她的了解,我敢保证她必动过回家重操旧业的念头,怕是就要做出决定了。
遗憾的是,已无法证实了,因为自命清高的我当时就是不肯认真地跟她谈一次,尽管她必定跟其他的女人一样,甚至犹甚于其他的女人,有着数不清的倾诉。
晚了,一切都晚了!因为,不久,悲剧就发生了。若不是我的粗暴,或许不会……她去了,操劳了这许多年,什么也没带走,一餐美食、一件新衣……不,带走了或许的渴望和尽快还清饥荒的念想。
说到这里,教授的眼睛潮了起来,几欲失控,兄弟们劝他去了一趟洗手间才勉强平静下来,重又开始了讲述。
丽萍虽然只比阿秀小两岁,却象是两个时代的人。阿秀沉着、冷静、务实、能够任劳任怨,丽萍则孤傲、浮躁、喜欢自我表现、骨子里透着一股不计后果的劲头。她说,秀姐善良,我实在不想跟她再争了,可我控制不了自己。那段,为了让自己死心,我分明已决定跟王维好,眼前却依然尽是你。或许我就是人们经常骂的那种发贱的浪荡女人!我恨自己骂自己用力地掐自己,直到生米做成了熟饭,还无法说服自己。哼,若不是那一刻直把他认作了你……丽萍的话,应该是我们最终结合的最好注释。
在这里,不再啰嗦。只说我和丽萍结合后,双职工的收入虽没能让我彻底摆脱困境,生活却总算有了较大改善。
事实上,人的注意力就是不断地由一些事情来冲淡另外一些事情,随着生活压力的逐步减轻,我们都无可置辩地意识到了这样的现实:人们被压制了许久的金钱欲开始或者早已毫无阻拦地释放了出来,心里想的嘴里谈的都是发财的事儿。
受了我无意间举办的辅导班的诱惑或者说启发,丽萍变了——她不再醉心于曾经深爱着的教研,着迷于搜集研究一些专门讲如何发财的书且不说,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她竟对我和阿秀已经习惯了的千百年来都如此的“挣钱、节俭、攒钱”的生活方式极为不屑,总幻想着天上能突然间掉下个大馅饼狠狠地咬上一口。
我劝她,人还是现实一些好,真的掉下个大馅饼,也不一定轮得上咱们。
她反问道,你怎么就知道轮不上咱们?准备,懂吗?没有准备,真的掉下来,那可真晚了,掉,那也肯定要掉到有准备的人嘴里。
我说,真的那样,也不如劳动赚来的钱实在,花着也踏实。
她反驳道,真正的赚钱凭的是智慧,而不是体力,再说了,难道脑力劳动就不是劳动?难道我们命中注定要穷一辈子?真是笑话了!我偏不信,见了钱,会有人不要。
我辩不过她,金钱确如一根神奇的魔杖,毫不费力地指挥着人们:不仅刺激着人的智慧,而且让人疯狂、让人丧失理智、甚至不惜失去自我。
丽萍发财计划的第一步,即是搜集了所有同学、老师、新老同事的背景和现实资料,而后把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逐一分门别类,最后选取其中的四十人举办了一次联谊会。
他们或是政界新星,或是商界骄子,或是学界权威,或是实权部门的负责人,且不说他们居然会喜欢而欢声一片,单是这一次聚会就花去了上万元,相当于我们两个人半年的工资,而且丽萍愣是充大头,坚决不肯让那位大肚便便见了就令人作呕的非要争着去结账的什么局长去结账。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看来,又要暗无天日地节衣缩食了。嘴上虽不说,却难免要心疼,要感叹。不料,丽萍只轻轻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戏谑道,男子汉大豆腐,心疼了吧?别心疼,好戏还在后头呢。
临到年关,她请了二十天的长假,坐着专门租来的满载着廉价购来的茶叶和挂历的载货车出发了,到年三十才回来。见她一脸的疲惫,我不忍问,吃罢了年夜饭,我慵懒地斜躺到沙发上没滋没味地看着中央台越办越糟又不得不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这是个没心没肠子的女人,见我不问,早已憋红了脸,故作神秘地问,你猜,我赚了多少钱?
我不经意地说,有个三五百吧?
她摇了摇头。
我便往大了继续猜道,总不致于三五万吧?
她还是摇了摇头。
我一惊,坐直了身体,唯恐她真的给出肯定地问,亏,亏了多少?
她轻轻地推了推我的头,责备道,大过年的,秽气。实话告诉你吧,三十万,净赚了三十万。说着,她已把成捆的钱如数从兜里倒了出来。
这又是她与阿秀的一个不同:阿秀总是要把钱小数目地逐步存到银行,而她却总要把钱积攒到一定数目才肯恋恋不舍地存到银行,我猜想,她大概就是喜欢手里攥着钱的感觉吧。
整整三十捆哪,我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她,我活到现在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但我显然还没有象她那样似已丧失了理智,慢慢地从惊喜中冷静下来后,我隐隐感到了后怕,劝她道,收手吧,这钱来得太容易,烫手!
她反问道,这钱是偷的?抢的?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而她的脸显然仍在因为过度的兴奋涨得通红,又不敢相信地惊叹道,这次,我算是大开了眼界,千万不要再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仅我们那位做乡教委主任的同学就要了八百套挂历,四万块哪,当然,我甩给他的五千块回扣也起了作用。傻样,最初还不肯要,我就看不透他那小心思?贼一样盯着那五千块!不过,他还真敢要,我都替他担心,可怎么销呢?收了钱之后,他居然轻松地笑了,大咧咧地说,小尅思,那个学校敢不要?我问他,学校有钱吗?他一脸地不屑,反讥笑道,不懂了吧?多收的学费干啥用?请客送……突然意识到因为炫耀话已太多,便戛然而止,竟没有丝毫的尴尬,只笑了笑,说,管他呢。临别,才又追上来千叮咛万嘱咐:都是老同学了,千万别外泄。土鳖样儿!收回扣的时候就不是老同学了?害了你?老娘若是发起狠来,真的害了你,死兔子还想吃老娘的豆腐?老娘岂是那么好欺的?说完,仍是一脸的忿恨。这个女人!
有了这笔钱后,丽萍终于肯听取了我的劝告:人变得安静多了,穿着也不再那么暴露,只是眼神仍无法掩饰经常会有的对金钱的崇拜。
不仅丽萍,其实,所有的人都这样:由于追求美好的愿望,人的目光往往最容易聚焦于事物的正面,留恋的尽是风光旖旎,独不肯去看神镜骇人的反面,贪心膨胀的人尤甚,而贪心膨胀的女人则最容易且一路潇洒地就走向了极端。
县城证券交易所开盘后,立即聚拢了不少人的目光,丽萍对股票的研究更是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挖空了心思要做我们县的杨百万。
不愧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她设计了一套假想试验:虚拟地选购股票,

![[综]神一样的男人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0/4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