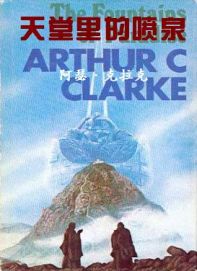男人的天堂-第19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便是“信”。很显然,“信”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要求的标准是不同的。
孩子时代的信以“信和无条件服从为核心的听话”为美德,不需去耐心地回顾我们的孩子时代,因为倡导的东西往往恰已泛滥至无法控制的地步。
也就是说,孩子的听话并非天生,而总是迫于压力或经不起诱惑,即使面对最可信的人,由于自制力和判别力较弱,必也要有一番因为信而听与不听的斗争,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听话与不听话之分呢?这又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这应该是最初的信。
待成了人,具备了自制力和判别力,想要听话了,标准却又发生了逆转,而且因为标准不同而必然地导致的不同的环境的影响,自又不能太过听话,当然,孩子时代牢固的标准的阴影依然存在并发生着作用,这又是一对矛盾,却或许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的“信”。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听话”这个词。单从字面上看,“信”就不等于“听话”,而是听话的前提。
按照我的理解,我们这个话题所要探讨的绝不是单纯的“信”与“听话”的关系,虽然这个关系必然地会是其至关重要的内容,但更多的还应该是“信”所明确指向的对象——人,而且不是孩子时代的那种单纯的“信”,而是步入社会之后面对日渐复杂的环境而逐步变化着的“信”。
我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不要笑,如若不信,不妨自我检测一番,笑得最重的那个说不定还不止两面呢。
这样的检测其实也简单,只需连续地问自己“我说过谎话吗?对自己最亲密的人也没有吗?我能以同样的心态跟无论是地位高于自己还是低于自己或者有求于人与人求于我的人说话吗?我能够一贯实事求是地说话吗?”这样几个问题,回答的结果就足以能够证明你是否“信”以及“信”的程度。
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应该不难,只要一个“是”或者“否”,但确不易说出口,说出口终究有伤颜面。
不过,我们不需要说出口,只要在心里回答。说着,自由从业者故意停了下来,见大家都在默想着,便得意地笑。
刚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结果已经有了,其实不需要说的,人的心理变化无论你如何掩饰总还是会通过形体表露出来,尤其是眼睛,眼睛是不会撒谎的。我猜想,结果必然都是否定的。
他见大家果然都点了头,就加重了语气道,这说明我们的“信”确已出现了问题。既然我们不去信人,又如何非要别人去信己呢?或许这便是乡丁所说的自我防护吧,但绝对是一个恶性循环。
果真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既不需要自责,也没有必要紧张。这怨不得大家,怪就应该怪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似乎一下子全变了,没有给人丝毫喘息的机会。
人是需要思考的,思考的结果就是给自己一个有力的支撑。
物质生活无疑是人追求的第一目标,已记不得哪位兄弟曾经说过,把人赖以活着的胃喂饱终究是人生的第一要事。物质生活无疑更丰富了,但当人获得了这一切之后却又发现,我不单单是为了这个呀。可为了什么呢,一时又说不清,因为世界已经多样化了,多样化得让人措手不及。
这样说不等于说多样化不好,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变化着的世界才最精彩,但我们毕竟不是精英,只是一群俗人,俗人的标志便是总要迟滞于变化。
正是因为这种多样化的变化和由变化而引起的人的内容的变化迅速地交织到了一起,才让人容易发生扭曲,非是单纯的人的品质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要有个正确的认识,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却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或许便是一个极正常的变化过程。很显然地,这个过程也不象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悲观,应该是可以引导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咬文嚼字地去过多地讨人嫌理论探讨,还是多说说自己为好,或许会有更多的感触。
我自小就是个只有一根筋的家伙,由于学习成绩的原因,不少人都认为我傻,因为傻人都一根筋,但并不等于说一根筋的都是傻人。
我所谓的“一根筋”,不过是仗义固执自以为认准了的事情就听不进任何的劝告易冲动,凡一根筋的人都这样:
没有强烈的占有欲,而且豪爽洒脱,只要别人看好了自己的东西譬如最喜爱的玩具等尽可以放心拿去,从不斤斤计较或者贪图回报,有人就当作傻。
这实际上仍是“信”的问题,由于长期衣食无忧而形成的“信”的过度问题,过度的“信”就等于不信,所以才会固执,才会拿别人的爱不当回事。这种状态,居然一直持续到公司出现内讧。
事情且从人具备了独立意识说起,按照我的理解,无论你早熟或者有怎样高的智商,只要不踏出校门就算不得有独立意识。校门,在这个问题上是个不可逾越的坎儿。
人往往便这样,哪怕只有一层窗户纸的间隔就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只要捅破了这层纸,就常常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在跨越这道坎儿的时候,因为陌生,人往往会既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又隐隐透着一股仿佛要脱笼似地对于新鲜的渴望——毕竟要独立自主了,独立自主是人一贯的梦想与追求。待要真正独立自主时,却又会茫然无措,最需要人的指点。
父母是人生当之无愧的第一老师,也是重新启航的导航者。只要父母双全且非个例,无一例外地都会为孩子比为自己更辛苦地谋划。
我们自无法与那些父母手握实权的人相比,单与我的那些熟识的同龄人相比,我父母对我的安排应该是最周全的。
然而,象我这种只有一根筋的人,只要不是经过自己努力才获得的东西就不会去珍惜。
在这里,我们不妨对前面讲述曾详尽提及的足以对我产生影响的“当逃兵”和“牢狱之灾”再稍加分析:应该说,两者都是不懂得珍惜的最有力证明,如果说当逃兵只是不能仰人鼻息率性而为的结果,后来的牢狱之灾就应该是“信”的危机的爆发。
说是爆发,仔细想想又算不上,但至少也是“信”缺失之后迷茫毫无理智的流露。
——“信”应该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支撑,“信”的缺失必然会带来迷茫,而且这个迷茫与人终于能够独立自主时的茫然无措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能好好把握,经常会发生一些出格的事儿。
现在可以说,正是牢狱之灾的结果改变了我,而且这个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即使牢狱也没能使之改变,不过,牢狱还是有成效的,最起码让我学习了冷静处事和一些技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并非是自我保护问题,而是“信”或者“信”的缺失。
“信”的缺失跟“信”一样,也是个过程,而非结果。
过程只是过程,似乎远不如结果更现实更有意义,而我们之所以会存有如此多的模糊认识和由模糊累加而形成的扭曲,恰恰便是因为太过重视结果而忽视了过程。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信”的缺失应是具备这样三个阶段的一个过程:信,但是盲目的,应该属于孩子时代;由于独立自主意识觉醒,信与非信纠缠斗争;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因环境变化交互作用而导致信的逐步变化。
前两个阶段显然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只要简略地提过,关键在于第三个阶段。如果兄弟们不嫌我啰嗦,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再过滤一遍这两段经历。
关于我当兵的事儿,不知我爹娘和我那位亲戚之间到底是否有什么幕后的交易,我想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告诉我。
无论怎样,我那位亲戚或者说他的影响还是照顾了我。
事实上,我并不需要他的照顾,我自觉是非常优秀的。我的离开虽说有赌气的性质,但至少有一半是在为他鸣不平,也算是对他照顾的感谢。
这个时候,还上升不到“信”的高度,或者说“信”还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至多给我留下了人何以会如此的印象,这个印象仍停留在由孩子完成向成人转变的迷茫中,还只是一种迷惑,淡淡地容易忘却却毕竟让我开始了思考。
按照我一贯的“只要没有经过思考的东西就算不得明确”的观点,真正涉及“信”应该追溯到我进工厂的那一段。
客观地说,我便是带着这样的印象做了逃兵,虽自觉无所谓,却终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尤其后来听说有不少人都因此而受了处分,便难免不有一点儿愧疚了。
这远远不是只要的事儿,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人一生不得翻身。
还是应该感谢时代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才让“逃兵”的影响得以淡化,在我爹娘的嘴里甚至公开变成了只是孩子不懂事这样一个只有芝麻绿豆似的小事。
前面的讲述曾经提过,事实上主要是因为部队人事的变化。尽管如此,能够进工厂尤其是谋到给弥勒佛开车的差事儿,已不再是幸运的事儿了,而完全应该归功于我爹娘的运作。
我爹是个似乎永远都让人感觉窝囊因其从未有过强梁的时候而瞧之不起的人,其运作的办法其实也简单,除了奴颜媚骨地赔笑之外,适当的几瓶酒或者几包点心的意思自也离不了,却居然能办得成如此大事。
可惜,我在狱中的时候,他们先后去世了,已无从考究,但排除了时代的因素,必亦有不少的讲究。
至于这些东西,或许出于我年龄的考虑而让我对新领导有个不错的印象,我爹当然是不会告诉我的。在我爹看来,初到一个单位,下属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让领导给下属留个好印象则更重要,是作为下属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的根本。
现在想起来,这无疑极富哲理任谁都不会反对,试想初到一个单位就在思想上与领导耗上了,不快乐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那时,我爹便具有这样的思想就不能不

![[综]神一样的男人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0/4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