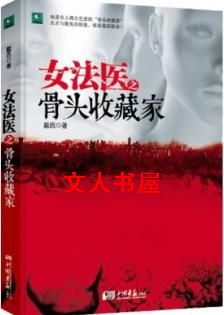法医生涯四十年-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校从没使我感到害怕。我的第一个老师珍科特夫人——普勒斯顿公园预科学校校长,对教育事业有天赋的热情和传授知识的能力,她会使你觉得知识是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她讲她的本国语言——法语,在她用英语讲演时,常常插入法语“‘du tout’(全然)和‘ma foi’(的确)”,当开始解释更加困难的课程时,常常亲切地说“现在,我的孩子们”。这位满腔热情的法兰西妇女谆谆地把求知欲望灌输进我的脑海里。从此以后,这种求知欲给了我极大的乐趣。
我还很幸运,能进入历史悠久的布赖顿中学。校长是身材魁梧的“T.里德”(我仍然能仿造他的签名!),他是位悦人的慈父般的英语和圣经课学者,也教应用数学。很难得到他一次“好的,孩子”的赞扬,但这声称赞却是真正值得去赢得的。我以极大的兴趣学习,有一阶段甚至戴起黄铜镶边眼镜来学习。我的哥哥丹尼斯鄙视我为“书呆子”,而他却顽固地不愿意接受任何教育。他由于有好几年时间都没有什么长进,不可救药地落在他的同伴后面而终于无声无息地在16岁时就离开了学校,到苏塞克斯郡务农,后来没有什么成就,又跑到罗得西亚。一个最可亲的哥哥,就是缺乏雄心壮志!
我在小学、中学、医学院以及在盖氏医院的大学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密切和感情融洽。这是因为师徒都献身于传授和学习共同的专门知识。我有幸学会了一个老师必须做到的两件事:一件是传授知识,另一件事是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多年之后当我在印度、锡兰、香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旅游时,我发现许多过去可爱的门生、学生和研究生给予我最热情好客的招待,原因只是为了“热情地敬重我的老师”。
我从小就再欢语言,我第一次尝到旅游的甜头是由于我在学校里获得了法国旅行奖学金。我在皮西维亚附近的一个法国乡村家庭里经过了短时期的“培训”,从此我对法语就不再感到困难了。几年后参加英国理事会去法国作旅行演讲,我有幸在巴黎的索邦大学作演讲。这一次的讲演,我很认真地用法语准备,由伦敦大学一位法语教师作了罗杰式①(①罗杰(Peter Roget,1779一1869)英国医生及语言学者,著有英语单词及短语词典。——译者)的润饰(付了相当费用)。想不到结果却令人泄气。在与我的东道主英—法协会负责人在艾台里附近吃过晚餐回来的途中,前法国大使柯宾先生(他是个杰出的白发绅士)在车里俯身向着我,一只手握着我的手臂亲切地对我说:“顺便提一下,大夫,我差点忘记提醒你。要是你用你自己的英语向他们讲演的话,这些特定的听众会更加满意。”哎呀,我的法语技巧和在指导下的修饰水平竟是如此!而我的罗杰式润饰全白费功夫!全都付之东流了!
我的父亲对我的学习情况并不了解。他把学校、入学考试和一定的医学教育以及取得资格看成是我的前途所“必需”的。所有好的苏格兰人都必须是勤奋,能够自食其力的,过一种诚实的生活,而我当时想进老牌大学(当时只要有钱就很容生们,为盖氏医院做点好事。先生,继续做好事吧,明天你可能会去医院看病的。”这样就可以得到好几千英镑来支持摇摇欲坠的私人医院系统。
那时盖氏医院有好多著名的教师,为首的是我们的校长T.B.约翰斯顿,他是个严格的苏格兰人的纪律维持者,解剖学教授,那时他正主编著名的《格雷氏解剖学》。当去病房查房时,我们又发现另一类人——内科医生、伦敦西区顾问医生。如果称职的话,他就会坐他的罗尔斯轿车每星期到盖氏医院两次作义务的下午查房。这真是一个大好时机。大学干事、他的住院医生和“一群”学生,我们大约有8到10个,都穿着白大衣在医院前门集合,时间正指2点,那位大人物就会到达。那时我崇拜的是哈伯特·佛伦奇大夫。他高大,漂亮,有成就,经常穿着清净的灰色燕尾服和大礼帽。他会从他的罗尔斯轿车跃上前排阶梯上,让他那穿灰色制服的男仆把门房里他的信件收集起来。戴着大礼帽的门房领班向他敬礼“请进”,他就会大踏步走进有名的柱廊(在这个柱廊里著名的布赖特、阿迪森和何杰金先前都走过),然后他到花园里,他的“一群”学生有秩序地跟着进入。
我所崇拜的另一个英雄是E.R。博兰大夫,当时的内科指导老师,后来象罗温爵士一样,成为大学医学院院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身受重伤,但仍然很机敏,身材细长,清洁,精神饱满,戴一只黑色的单片眼镜以遮盖受伤的眼睛,而且总是穿着整齐。他教过盖氏医院几代学生的医学伦理学。就是这位博兰大夫,他作为医学院院长支持我对病理学的爱好,使我在细菌学方面获得一枚金质奖章,支持我参与病理学方面的古尔氏病①(①古尔(Gull)氏病,一种有粘液水肿的甲状腺萎缩症。——译音)的示教,并在其中担任讲解工作,这一工作使我能开始讲授这一课题,这证明我没有辜负他的支持。
我对教学工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在我取得资格不久时,病理学教研室工作人员的灾然不足,把我正在寻求的大门打开了。头一天,我还是一个奋斗中的年青的临时职员,第二天,我就变成了病理教研室穿着白大衣的老资格的教师了。在我还还是25岁的时候,病理学家这一生涯的大门就奇迹般地向我打开了。在我最后一次考试的那一年我幸运获得的几次奖金和奖品,使我在病理学突然缺人时,得到好运。
好久以后,在中央刑事法庭审判的一件凶杀案,使我在盖氏医院获得的成功得到报偿。我已经是二十年工龄的病理学家时,一个早晨,律师企图贬低我在鉴定中一个意见的重要性。我的意见是:“显然需要通过手术来解除内出血”。他批评道:
“大夫,你是一位病理学家,怎么能懂得临床外科学呢?”
问得好。鉴定人在法庭上总是经常被告诫不要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的严格界限去随便发表议论。这位律师谅必认为他抓住我犯了传统的毛病。我急中生智。
“我获得过”我说,“一枚临床外科的金质奖章。”
他明显地震动了。谁会期望从一位病理学家那里得到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回答?要是他知道虽然我早在20年前就因为我在临床外科方面写过很有见识的论文和短文而得过奖,但我一生中却从来没有拿起过一把手术刀,那就好了!可惜他不知道。他因为失败而一时气得满面通红之后,他就转向问题的另一方面去了。
1932年我意外地得到提升,我和盖氏医院的一位护土玛丽·布坎南结婚,以后我们生了三个孩子。
在盖氏医院作为一个年青教师我最基本的兴趣在于病理学,而这过去是,现在也还是一个法医病理学家唯一扎实的基础。除非他熟悉了疾病的破坏和各种奇怪的变异,他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损伤的研究,更不用说法医损伤学了。法医病理学是病理学的特殊分科,年青的初学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
作为病理学教研室高年示教老师,盖氏医院的尸体解剖大部分是我做的,包括给验尸官(南瓦克的道格拉斯·考宾)的尸检报告。考宾刚好需要一位病理学家来帮助处理他自己的案件,这是我的好机会。通常他会请伯纳德·斯皮尔珀里。当时斯皮尔珀里在法医学实践方面是出人头地的,但考宾不喜欢他,只是出于无奈——遇见重大刑事案件时才请他。有一次检查联体双生子,他只付给斯皮尔珀里一次的尸体解剖费!斯皮尔珀里火了。那是两具尸体,他都检查了,但考宾坚持不给。这种反感以后一直没有完全平息下去,尽管这件小事微不足道,但它却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隔阂。这样考宾就要求盖氏医院的院长哈伯特,伊森爵士(他对我的工作大致是满意的)同意他聘请我去处理他在公共停尸室的案件。伊森和病理学教授都同意了,后者还给我设立了一个“法医尸体检查主任”的新职位,我就去了。那是1934年秋天的事。
当然,开始时每年我只检查少数几宗刑事案件。凶杀案在英国并不象某些国家那样多,相对来说是较少的。伦敦地区的发生率虽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年的凶杀案也只有大约50件;每年发生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也只有150至160件左右——从本世纪初开始就一直相当稳定地保持这个数目。这一数字与当时每年死亡总数60万相比就显得不重要了,死亡总数中约有9万例受到验尸官的关注。几年以后,我给卫生部写了一个我作的2万例验尸官要求的尸解的分析报告。其中55%证实为自然死亡(但以前一直是死因不明的),另外30%估计与各种类型的意外或损伤有关:包括家庭中、医院里、街道上或工作中的意外性损伤。约4至5%是自杀,仅2%至3%才是属于怀疑或确定是犯罪性损伤。
1934年底的一天早晨,在盖氏医院我那间小实验室里电话铃响了。
“辛普逊大夫吗?先生,我是伦敦警察厅探长杨格。我们刚接到一个凶杀案的电话,在滑铁卢车站对面的约克酒店,我们想请你帮忙。”“啊啊,是的,”我说,想尽可能讲得平静些和镇定些,“当然,我马上就来。10分钟内就到”(我想还是10分钟内到好,否则他们会请别人,而我就会失去在警察厅取得立足点的机会)。
当时我仍然是个很年青的病理学家,这是伦敦警察厅第一次叫我处理案件,心里卜通卜通直跳。实际上,每次突然叫我处理犯罪案我都心跳。我会放下一切事情,中途离开宴会,甚至夜深人静时起身,赶去处理新案件。可能又是另一个希思或黑格,或汉拉第,或什么也不是。但不管是什么,我都从没有感到失望或厌烦。法医病理学家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和有趣,以致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烦恼,甚至难得感到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