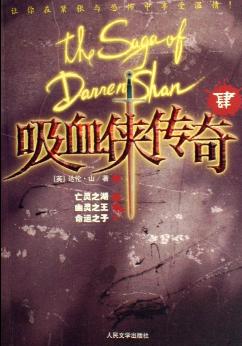山路·山妞和光棍-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易八卦先是揭发了李秉公的一些罪行,接着揭发郑有儒:“生产队成立大食堂的时候,郑有儒说‘一进食堂冷飕飕,三两炒面二两粥,虽然不是监牢狱,受罪的穷人在里头’。郑有儒,你说这事有没有?”
郑有儒知道,又是借机报复的。原来,易八卦和郑有儒也有一些解不开的疙瘩。村里成立小学的时候,他和易八卦竞争当教师,易八卦没争过他,因此有了一些嫉恨。
刚才易八卦揭发的,也确有其事。生产队成立大食堂的时候,郑有儒媳妇领着儿子小惠民从食堂打了一盔子“酸不溜▲”做的稀菜粥,往家里端。小孩子眼望着盔子里的稀粥,肚子里就咕咕地叫起来了。惠民娘边走边给惠民喂粥,一不小心,脚下绊上一快大石头,盔子打了,粥撒了,手也烫了。这一顿,郑有儒全家都没吃上饭。晚上在大食堂吃饭的时候,郑有儒顺口说了上面那几句顺口溜。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到了现在,成了反革命言论,成了易八卦反戈一击的有力武器。马到悬崖收缰晚,船到江心调头迟啊。祸从口出,都怪自己的嘴没有把门的。郑有儒心里埋怨自己。
易八卦得到了优待。魏子利批准,他可以不用撅着了。
一枝花从中受到了启发。她绞尽脑汁,想起了郑有儒的一条罪行。她也要求立功赎罪了。
一枝花揭发了郑有儒这样一条罪状。说的是郑有儒会唱影,有一年夏天,在唱影的时候,郑有儒编词攻击社会主义。
在每场皮影戏开场时,都是大爪子和小矬子这两个角色首先出场,来一小段开场戏,有时是说明唱影的目的,有时是打浑骂科逗乐子。这两个角色相当于京戏里的丑角,也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有一次,郑有儒借大爪子和小矬子的对白,说了下面一段词。
小矬子:“大爪子!”
大爪子:“哎!”
小矬子:“你今天怎么光着腚跑出来了?”
大爪子:“没有衣服穿呗。”
小矬子:“为啥没衣服啊?”
大爪子:“布票发得少呗。每人就发二尺半布票,我这么大的个,能够穿吗?你以为中国人都像你的个子那么小吗?你那小玩意,跳八个高也挠不着我的卵子皮。小矬子!”
小矬子:“哎!”
大爪子:“我的裤叉子不穿了,你拿去改一件长袍穿吧。”
小矬子:“好恼啊,你着打啊!”
这里说“二尺半布票”,说的是那时侯物资供应紧张,布凭票供应,每人每年只发给二尺半布票。衣服不够穿,只好拆了又拆,补了又补。有钱人家才能在过大年时做新衣服。一般家庭,老虎下山一张皮,夏衣拆了改冬衣,棉衣拆了做单衣。那年月,农村的姑娘,在结婚之前没有几个穿过裤叉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就是这么一段笑话,换来了今天这样的后果。
一枝花揭发结束以后,问郑有儒:“你说,这是不是反动言论?”
郑有儒根本没听一枝花问什么。他心里说:“这个臭娘们,真不是个东西,落井下石。钱进和易八卦他俩整治我,是因为我得罪过他们。你为什么?我没得罪你啊。”
和易八卦一样,一枝花也得到了优待。
魏子利和台上的红卫兵代表听完易八卦和一枝花的揭发,非常满意。魏子利当场表扬他们:“你俩有立功表现,散会以后,一定会宽大处理的。”表扬完易八卦和一枝花后,魏子利批评了郑有儒和李秉公,敦促他们认罪。
李秉公和郑有儒一言不发。
易八卦和一枝花受到表扬,越发有了反戈一击的积极性。易八卦揪住郑有儒的耳朵,追问:“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事实?”郑有儒狠狠地瞪了易八卦一眼。易八卦踢了郑有儒一脚。
一枝花追问郑有儒:“我说的事有没有?”郑有儒哼了一声。一枝花扇了郑有儒一个耳刮子。
此时,惠民和茉莉等孩子都站在台下看。郑有儒在台上挨批斗,气坏了他的儿子郑惠民。看见爹挨斗,惠民心里极其愤怒。会议刚开始,他还强忍着。后来看见爹挨打,他忍无可忍,跳上台子。茉莉也跟着跳上了台子。
惠民狠狠地咬了易八卦的手。易八卦照着惠民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
茉莉跳高挠了一枝花的脸,一枝花使劲地打了茉莉一个耳刮子。
值勤的红卫兵把惠民和茉莉推下台。
批斗会以后,易八卦和一枝花由于反戈一击有功,被解放了。易八卦顶替郑有儒当上了代课教师。
李秉公和郑有儒却升格到了公社,进了劳动改造队。不过,对于他俩来说,坏事却变成了好事。自从升格后,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和谁也没有仇火积怨,因此再没挨过批斗,每天学习劳动,还能吃饱肚皮。
这正是:
病入膏肓想忌口,
祸事临头才锁唇。
马临深渊收缰晚,
船遇风浪转舵迟。
要知后事如何,且往下看。
第四回 郑有儒放到风水树 郑惠民订婚黑丫头
书接上回。一个月后,李秉公和郑有儒结束了在公社劳改队的改造,回到了大队。
郑有儒到大队报到后,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
小山沟里没有电,照明全用煤油灯。多数人家为了省几个灯油钱,都早早地止了灯,钻进被窝里。只有郑有儒家的灯还亮着。
郑有儒进屋,惠民娘急忙下地热饭。
“看看,都折腾瘦了。”惠民娘把一碗高粱米饭和一个咸菜疙瘩递给郑有儒。
“在公社劳改这些日子,比在咱大队好过多了,虽说干活累一些,但是不挨打啊。”郑有儒一边扒拉饭,一边说。
吃过饭,撂下碗,郑有儒耷拉着腿坐在炕檐上。
灯窝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可能是煤油里有水的缘故,灯芯不时发出噼啪的灯爆声。
微弱的光,涂在郑有儒消瘦的脸上,一道道皱纹清晰可见。他从灯窝里抄起烟荷包和烟袋,捻了一锅子蛤蟆烟▲,对着灯火点燃,吧嗒吧嗒地嘬了几口。顿时,浓烈的旱烟味充满全屋。躺在炕稍的孩子呛得连声咳嗽。
“真呛啊。你可少抽点吧。天冷,打不开门窗,烟放不出去,都把惠民呛咳嗽啦。那是啥好东西,整天不离嘴,白天嘬了一天了,还没嘬够,晚上还嘬。”惠民娘责怪郑有儒。
“喜酒呐咋▲烟嘛。不管有啥嘬瘪子▲的事情,只要抽上几口烟,心里立刻敞亮多了。”郑有儒为自己辩解。
“遇到不顺心的事往宽处想,不要整天和烟叫劲儿。你呀,自打来了这场运动后,烟瘾见长啊。那玩意不是啥好东西,抽多了伤身子。你看你,抽的脸都不是正经儿色了。按说,像你这岁数,四十四五岁,正是好年纪。可是你,这几年忒见老,都成了大烟鬼了。”惠民娘的唠叨里透着心疼。
“嗨,抽棵烟得心宽啊。你说我这是啥命啊,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回想起来,没过几年舒心日子,先是你不生育,到处请先生搬大夫,花的钱也没数了,你喝的苦药汤子也有一缸了吧?谢天谢地,老天爷有眼,赐给咱们一个儿子。接着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光是吃不饱肚皮也罢,那年头,家家户户都差不多。可咱没管好自己的嘴噢,顺嘴吐露出几句大实话,就触犯了王法,挨了一年多的整,差一点打成右派。刚消停几年,又来了运动,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又翻腾出来了。这么多年了,我都是猫着腰就乎啊。可是,越老实越挨整。不让当老师也就算了,还得隔三差五戴高帽子游街。这日子啥时候熬到头啊。”几滴浊泪从郑有儒满脸皱纹上滚下。
“那还不是因为你嘴上没有把门的,斗大的字不识两口袋,还整天瞎咧咧,祸从口出啊。”
“真后悔当初不该那样年轻气盛啊。”郑有儒又想起了以前那些辛酸的往事。
的确像郑有儒自己说的那样,他年轻的时候可不像现在。他家祖上留下一些家底,供他念过几年私塾,成了这一带为数不多的识文断字的人。也正因为有一些文化,平时喜好编顺口溜,讲笑话。谁知几句大实话,惹上了半辈子的麻烦。反右的年月,挨过整。文革来了以后,又被红卫兵揪出来了。
这些年,每当郑有儒想不开的时候,惠民娘总是劝郑有儒往宽处想。惠民娘见郑有儒又提起这些糟心的事,仍然像以往一样劝说:“孩子他爹,往宽处想吧。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信命吧,人不能和命争啊。熬着吧,老爷儿▲不会总在一个门口转,再长的连阴雨也有晴天的时候。别想那么多了,快躺下睡吧。”
“欢娱嫌夜短,饥寒怨更长啊。我哪能睡得着啊?”郑有儒又发出了无奈的叹息。
“睡不着,我就陪你唠嗑。可咱不说那些不顺心的事了,行不?”
“行。你说的对,挨整归挨整,这日子还得过,咱说正经事。今天从公社回到大队,大队魏主任又找我谈话了。”
“啥事?不会还要开你的批斗会吧”
“不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已经在大会上宣布,结束对我的审查了,以后由大队重点教育。魏主任说要翻盖学校,需要一些木料。他看遍了全大队的树林子,也没找到能做梁柁的材料,就相中咱家院子里这几棵老榆树了,动员我支援学校建设,还说适当地给点钱。”郑有儒面露难色。
“这几棵老榆树可是咱家祖上留下来的风水树啊。以前,咱家就是遇到再大的坎,也没敢动过砍树的念头。”惠民娘也很为难。
“风水树?可别说啥风水树啦。这些年,天天挨整,没见这几棵树给咱带来啥好运气。”
“看样子你是答应他们啦?”
“公家相中了,能拒绝吗就咱家这身份,头皮没有人家卵子▲皮厚,能说不行吗?别说人家给几个钱,就是一个子▲不给,咱也得忍着。”
“主任说没说能给多少钱?”
“说了,说是给个半价。我看也就能给三四百块钱,多不了。既然主任说了,那也就是板上钉钉了,我哪敢讲价啊。这事要是不答应,那不又是政治问题吗!”郑有儒的话音里透着一些无奈。
“不怕贼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