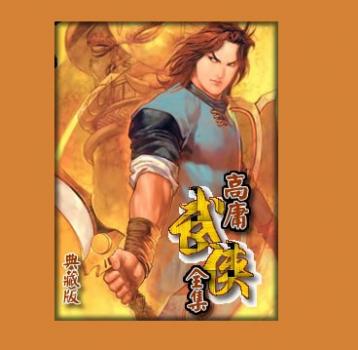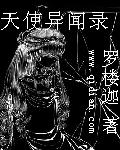高中回忆录-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嗯!是我。”我走近一步,让她能够看的更加仔细一点。“你一个人在干什么呢?”
“我在弄面饼呢!这几天吃饭觉得没味道,所以想换换胃口。”她一边说着一边已经走到那个落地柜子上翻出了一大堆吃的。这似乎已经成一种习惯了,我每次来,她都是这样。“阿海,你今天放假了?这些是奶奶特意为你留的,过来吃!”奶奶说着就把一大把果冻塞了过来。说实在的,那一堆零食里面没有几样是我喜欢吃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年龄的增长,口味也发生了变化。可是奶奶不懂这些,她只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吃咸饼干和果冻。为了不辜负她的一番心意,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吃了点。
近二个月不见,奶奶似乎又苍老了许多。记忆中奶奶的那双手应该是饱满而有力的,而如今见到的却只是皮包骨头,那宽松的皮附在细小的骨头上形成了无数条的鸿沟,一根根青筋高高地凸起像那地图上的火车路。奶奶额上、脸上的皱纹也像东非大裂谷,条条深不可测。一头暗淡无华的白发,宣写着她那数不尽的沧桑。她走路也不像过去那般轻快自如了……这所有的改变使我不得不为岁月的飞逝感到震惊、战栗。岁月不饶人啊,记忆中那位体健的老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生的短暂真让人胆颤心惊,可我们在学校却又总是单板地飞度着,真怕突然回首发现自己已是百年身的时候,会找不到一丝回忆。有了奶奶这样年龄的人多数的时间都是沉浸在往事之中,对于未来他们已经不在指望什么。奶奶这一代人是不幸了,一生中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世事变迁,可是最终也没有过上过几天好日子。在旧社会的时候国家动乱,内忧外患不断,奶奶也可谓是历经磨难,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结果又因为曾经的地主身份被拉去做了半辈子的牛马。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好转了,可是爷爷却过世了。一个观念传统而又年过花甲女人,就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给了儿孙,可是至今为止,家族里也没有出现过一个能让她骄傲的人。每次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茫然地想自己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年轻是我们最大的资本,可是这个资本能换了什么样的人生?对于这一点,我毫无把握。人人都歌唱青春少年是样样红,而我除了有几份友情能让我感到欣慰外,实在再也找不出有第二件称心的事,一味地只有胆怯和痛苦。有时候我害怕青春逝去太快,可时候,又想要是青春岁月里可以跳过这六年中学生涯那该多好,哪怕一下子突然长大了,我也不会为丢失的年华而哭泣。人生最不幸的事情,大概就上违心地活着。
在奶奶家除了倾听她对生活的抱怨外,我无事可做。坐了近两个小时,我找了一个脱身的理由,便从奶奶家出来了。奶奶自然也一再留我吃饭,见实在留不住才把那一堆零食包了,叫我带回去。我知道奶奶的脾气,不敢拒绝,只好收下。
出门不远,见有一群小孩正在游戏,于是招呼他们过来,把吃的全给分了。如此倒也赚了不少“哥哥”,“叔叔”的美称。
二十四
午饭时菜很丰盛,可我没有胃口,只吃了一点点。爸妈见我整日闷闷不乐,以为我病了,非要拉我去医疗站检查检查。我当然拒绝了这份好意。父母依然不肯罢休,一招不成又出一招,硬要我回床睡一觉。我还是同样地反对,但这次反对无效,见父亲阴沉了脸,我只好遵命。
坐在床边,整个人呆滞地像一块木头,两天休息才过了半天,若整个假期都这么无聊,我可真要生病了。进入高中以后,父母已经不允许我画画或者玩些其他的东西,他们说我玩物丧志。我没有争辩,也不想争辩,只能顺从他们,安心地看书、做作业,企图把自己活活闷死。我无聊地坐在床沿上无所事事,脑子里突然迸出了云芝的那句话来——无聊地想玩上吊。是啊,真想找点什么事情做做,哪怕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在郁闷之时,电话铃然响了起来,那急促的铃声使得我格外的兴奋。我飞快地从床上跳下来,那一个迅猛差点把神经拉断。这个电话可真像是干漠中的一场暴雨,我飞快地跑去接电话,猜想着会是云芝还是张敏或莉儿。我家的电话是最近几个月才通的,因为知道我家号码的人很少,所以这个电话也不常响。
“喂!萧海在家吗?”果然是个女的声音,我激动不已。可仔细一听,这声音又不像她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我不由地又有些沮丧。
“我就是,你是——”
“我是曾诗美。”她抢在我问话前先回答了。
曾诗美?我好像和她没有多少来往呀?她怎么会知道我这家电话号码的?我暗暗思索着。
“萧海,你有空吗?我有些问题要请教你。”曾诗美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地说。
“向我请教问题?”我满脑子疑惑,她的成绩可是班里一流的,而我顶多不过一个三流人物。她向我请教问题,那不等于上山捕鱼?我百思不得其解。
“是啊!”
“你什么问题向我请教?”
“关于作文的,我知道你作文写得很好,所以想请你帮我指点指点。”
又是老孙惹得麻烦,我听了作文两字就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时间倒流,能让我回到那节语文课上去揭露他的骗局。不过借此机会出去走走倒也不错,总比一个人寂寞地睡午觉舒服。如此想着我也就收起不耐烦的情绪,回答曾诗美道:“有空,在什么地方见面?”
“去海边吧!”她不假思索道。
“海边?”我总觉得有些怪,但又说不出为什么,只好答应了。挂了电话,我便推了自行车往外冲,妈在后面追着问:“怎么不睡觉了?”可我早飞出了几十米。
一走上海坝,心情便舒畅了许多。十月中旬的阳光已经少了夏日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此刻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倒很有一种温馨感。温柔的海风不紧不慢,不大不小,刚好吹散愁绪。茫茫的海面上波浪一个接着一个朝着海坝涌来,浪涛轻轻地拍打着礁石,发出阵阵轻柔地声响。看着大海,我的心情又郁闷变地平静,又又平静变得波澜起伏,渐渐地,有了一种急欲表达些什么东西的冲动。
岁月飞逝,朝夕轮回
春去秋来,古今循环
光阴荏苒,英雄不在
碧海苍天,谁人舞台
静心弦,辽望波澜起伏
仰天啸,叹人世愁苦
试问苍穹,生来为何?
我也说不清楚这首乱七八糟的几句话算不算一首诗,也说不清楚自己想表达些什么,或者说,我只是想对着苍天和大海大喊几声。至于为什么想喊,为什么要喊,我自己也不知道。喊完以后只觉得心里稍稍畅快了一些。再一次回味自己喊出口的几个句子,倒不由得轻飘飘了起来,那感觉几乎一阵风就可以把我吹上天去。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诗,平常对什么狗屁诗集也是不感一点兴趣,可是今天我却出口成章,作了一首诗。我想那大概是多情而伟大的大海感染了我,是的,大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了。一时间,我激动得只想跪下来拜大海为师。我天真狂妄而又无聊地想,如果在大海门下修炼几年,恐怕尼采见我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了。
“萧海,萧海。”一阵声音把我从自我陶醉中拖回了现实。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曾诗美来了。她穿着一件蓝白色连衣裙,裙脚刚好盖到脚面,在海风中那裙子飘得不亦乐乎,像一只被拴住的雄鹰,挣扎着似要脱离她的束缚远走高飞。她曾诗美脚上穿着一双白色凉鞋和一双白色薄袜,胸前还抱着几本书,那装扮淑女味十足。可惜她没有莉儿的那一头乌发,若换成是莉儿,我倒真有可能被当场迷倒。
“Hi,你来了。”我轻描淡写,有气无力地和她打了声招呼。
“嗯!”她小跑几步到了我跟前,一股香水味逆风而上直冲脑门,使得我喷嚏接连不断。我向来头痛那种怪味,以前每闻到便称之为硫化氢,然后迅速逃出那怪味的势力范围,可今天——有的受了。
“你怎么了,萧海,感冒了吗?”
“感冒?嗯!是有一点点。”我捂着鼻子说,心里觉得好笑,爸妈问我是否病了,她又问是否感冒了,难道我真的是一副病人相?
对作文这东西,我根本就是个门外汉。再说作文的精髓之处,若要心领神会往往需要自己仔细琢磨反复对比研究才能有所感悟,并非不是谁通过一朝一夕的指点就能说清道彻的。写作文靠的是长期的文学积累,和平常对于生活的仔细观察,这一些别人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当曾诗美一本正经地拿起她的作文本向我请教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后悔自己不该自找难堪。我出来的时候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出来散散心。和同学探讨学习,这一个理由在父母面前充足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悬着地心倒慢慢放了下来。曾诗美在开始一段时间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之后,就合上了书,转而谈起了她的境况。从说转入听,自然轻松了几百倍,我也就乐意地洗耳恭听了。
原来曾诗美的家就在邻村,她也是独生女,有个当老板的老爸和在镇政府工作的老妈。她家的生活在整个萧镇可谓首屈一指。
在她说到自己父母的时候,我才发现她不光喷了香水,还涂了口红,抹了胭脂,画了眉毛,更让人头大的是,她说话总喜欢盯着人看,那目光像是要把我捂在鼻子上的手撬开。从始至终我都是“噢、呀、嗯!”的应付,心里一直盘算着怎样脱身,过了好久总算想到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妙计。
“萧海,你希望大海吗?”她深情地望着大海说。
“咳!咳!咳!美!咳咳……”
“你怎么了?萧海,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说。
“咳!咳!咳!咳!我——咳咳!我——风——咳!咳!风一吹,就忍不住——咳咳咳咳!忍不要咳嗽。”我弯下腰,一手捂着嘴一手捶着胸口,边咳边说,时不时还擦一把“眼泪”,恨不能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