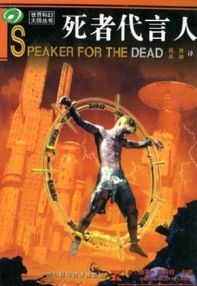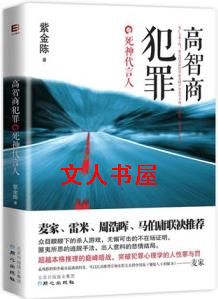大地的谎言-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通迟疑道:“我觉得,他的确有事情瞒着我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侯风说的那个。”
在曾通说话的同时,狱长飞快站起身来踹开门。
门外空无一人,如同刚才的结论。
狱长回头:“反省得不错,通过。”
侯风的嘴角往后掠了掠,得意地摇头晃脑,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复杂了。至少当时他自己是这么认为。
第二章狱长(七)
…………………………
狱长慢慢地在操场上镀着步子。不是犯人们的放风时间,却是他自己活动身体的时间。上回打架事件之后,狱长就做出了冠冕堂皇地加强看管、减少放风时间的理由。因为比起和囚犯们的噪音一同漫步来说,他更有兴致一个人在空旷中呼吸新鲜的空气。他抬起头看看天空,天一片碧蓝如同洗过一样,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直晒在脸上带来的些须温度也马上被呼啸而来的风掠夺干净。这正是鹘山长达几乎一年的旱季。
其实在狱长心底里并不同意侯风的分析。侯风整套看似严密的理论中有一个漏洞,即那个找不出来源的“沙沙”声。如果真象侯风所谓的乌鸦操纵了一切的话,那么是他找来一个看守弄出的声音吗?狱长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能在甬道里弄出动静之后全身而退,甚至不让侯风看见。
另一个问题,侯风认为当初第一次夜探的时候他没有跟上曾通和侯风,而是什么莫名其妙的X和Y。从逻辑上说,这很好的解释了后来在一长串远距离的跟踪和反跟踪里发生的事情,但是,狱长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确信自己是跟在,至少最开始,是跟在侯风和曾通后面。
犯人们的放风时间快到了,他几乎已经听见犯人们嘈杂的声音从山壁内的甬道里隐隐传来。与外界异常隔绝而显得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似乎让鹘山监狱内部争取到了某些比其他监狱多得多的东西,比方说,次序和纪律。在其他监狱,放风之前这样吵吵嚷嚷是绝对不敢想象的。
想到外面,狱长的心思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在监狱甬道外面,通往外界的那条甬道尽头,有一座靠山体的小木头房子。那里寻常有四个看守轮流守卫。如果他们和乌鸦他们串通一气的话,乌鸦他们就该很容易脱逃出去才对。可是,难道这就意味着那四个看守是可靠的吗?狱长抬起头,看着操场四周的悬崖。毫无疑问,乌鸦并没有掌握多少看守或者囚犯,否则,就算用挖山的方式,或者填土斜坡的方式通过悬崖……随便怎么样都有一万种方法脱逃。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看守是可靠的呢?中队长余学钧?不,他连基本的监狱守则都不懂。那么马宣?如果马宣不可靠,那么讨好自己是干什么?可是马宣从头到尾都表现出极力巴结的样子,那似乎不该对自己不利才对。
忽然之间,一道闪电刺破了狱长脑海上方迷朦一团的黑雾,狱长被一个想法钉在了地上:如果余学钧不可靠,那他肯定知道谁是可靠的。可是如果不可靠的看守够多的话,为什么不干脆把不是他们的人包括自己干掉?如果他们的人少的话,余学钧这种既与囚犯同流合污又不称职的人怎么可能当上队长?有没有可能所有看守都不可靠,可他们也和囚犯们不是一伙的呢?证据?自从进了监狱之后,狱长就从来没有见过——虽然他毫不在乎——任何一个哪怕是一个看守对自己敬礼。就如同余学钧是不够格的看守队长一样,他的下属……
曾通和侯风走出甬道。就象自己预料中的一样,侯风的到来被某种地下的途径传播开来,以至于当他们在甬道里排队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囚犯胆敢站在他们前面一排。熟悉侯风历史的人们纷纷用某种畏惧的眼光注视着他,而不知道所以的人则纷纷交头接耳,打听这是何方神圣。曾通心里多少有些奇怪,理论上说,在鹘山监狱里的囚犯都是亡命之徒,应该不会互相买帐服气。可是,他们却在对侯风出现这件事情上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也许,这是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的古训的体现?妈的,侯风算什么状元?
曾通是唯一和侯风并肩走出甬道的人。看守们也默许了这样的情况。从地下消息的传播和看守们对侯风的态度来看,鹘山监狱的看守和囚犯们似乎有某些微妙的关系。考虑到看守和囚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这样的微妙关系并不是乍看上去那么不正常。两人走出甬道,为突然而来的阳光眯了一会儿眼睛,风带来透心凉的新鲜空气,清洗掉肺叶里的污秽连同长时间处在黑暗中带来的怪异气息。这自由是来得如此的欢畅,以至于让两人多少都有点不适应,脚步也放踌躇起来。
当曾通和侯风重新适应了美好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在两人眼睛视野里的是一片黄色沙土地中一个瘦高的身影,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却并没有阻止别人的感官觉察到他的思维和肌肉是同样的敏捷、高效。这,会是一个如同厚重坚实如同大地般值得信赖的伙伴,或者也可能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当阳光洒在他的肩头,一层金边在他的周围若隐若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认知。
后面的囚犯们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他们一涌而出,混乱又嘈杂,带着身体上的恶臭和洞穴里的肮脏,仿佛是一群被洪水赶出洞穴的耗子。曾通看到了百羽,看到了小崔以及其他熟识的人。百羽的脸上仍然惨不忍睹,他看了看曾通身边的侯风,没敢和曾通打招呼,就咬牙切齿地狠狠地瞪了狱长好一会儿,然后带着几个人躲得远远的。
狱长的思考被非常不愉快地打断,他轻蔑地扫视着那些耗子们,然后看了一眼曾通和侯风,转身朝操场的另一边去了。
曾通询问道:“去那边?”他示意狱长的方向。
侯风毫不客气地侮辱他,这是他最近发现在不能用物理攻击的情况下发泄的好方式:“你最好再朝那边靠近些,好让大家都以为狱长非常中意你的屁眼。之后,就永远不要再让我见到你,以免让大家产生桃花三瓣之类既不健康又不正确的联想。”
曾通说不出话来,侯风又道:“现在你带着我周围逛一下。”语气轻松得如同是来交游参观的远方客人。于是曾通带着他走东逛西,来这里半年多以来的种种被回忆并传进侯风的大脑:东南西北山的高度,操场中间已经缩小得不成样子的混沌湖泊,洗衣工地,挑水工作,蔬菜种植,劳动时间人手分配作息制度一二三四。侯风一边听,一边眼睛不停地扫向那些遇见他们就让路,这辈子打从娘胎下就没这么礼貌过的囚犯。
待到曾通说得差不多了,侯风背着手,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突击发问:一棵树上有二十只鸟,你打了个喷嚏吓走了一只,再看时树上还有几只?”
曾通愣了一下:“没,没有了。”他怀疑这又是侯风嘲弄他的圈套。近来他发觉侯风的言辞之锋利话语之犀利,只在狱长之上。他可不想又触了什么霉头。
“如果树上有一百只鸟呢?”
“还是……没有了?”
“真的吗?你确定你的喷嚏有那么响?”
“那……”
侯风出奇地没有嘲讽他:“我已经给足了条件,树上被吓走了一只鸟。如果这样说你不明白的话,那么如果树上有一百二十二只鸟,已经吓走了四十只,那么没有吓走之前呢?”
曾通有点明白他在说什么了,侯风是在怀疑囚犯的人数?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狱长不是说过吗?一百二十二人,那是五年前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的人数了。那么以前,应该是一百六十二人?不,除开自己,侯风,应该是一百六十人。
侯风道:“别他妈白费力气了,老子今天心情好,教你个乖,没事要多想多看。树上有二十只鸟,如果吓走了一只鸟,应该还有十九只。但是如果你不去一只一只的仔细数,你还是会以为是二十只。因为,你既没有见到那只鸟飞走,也没有可能一瞬间看出那些躲躲藏藏的家伙们到底有多少。”
“你是说?”
“数目不对!我们都不是站惯队列的人,对一百多号人应该有多少这样的印象是非常模糊主观而不准确的。这个监狱的人数比我们想象中少得多。我已经数过三遍了,囚犯的数量怎么算也不到一百人。”
“可是,”曾通想起了什么,“有时候狱长会让他们报数。”
“你听到过?你也参与过报数?”
“对啊。”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他们自己口中报数会是一个数字,而事实上我们自己数又会是一个缩水很多的数字。”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侯风道,“那是因为你头壳坏掉了想不出来。谁他妈告诉你只有囚犯才有资格报数的?”侯风转身不再理会他。
曾通的心里有些不安,自己思维的触须似乎已经触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边缘,却又抓不住这样滑溜溜又毛茸茸的东西。
报数的人,不一定是囚犯。不是囚犯,就是看守,那么为什么看守们要帮助囚犯们遮掩?
当如同岩石一般厚重的夜到来的时候,狱长端坐在桌子旁,手边是一杯茶,一把手枪,一只本子,一只手表和一张综合了侯风、曾通以及自己的地图。地图的杂乱纷乱到没有可以让人产生任何的方向感觉,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其中依然存在有价值的东西。
基本上来说,侯风和自己的草图没有太大的出入,而曾通,似乎走完全是另一条线。最让人感觉荒谬的是,曾通在据称自己迷路的时候,曾经两次走过一条十字路口,一次是东西方向,一次是南北方向。虽然曾通不管智力还是方向感都让狱长感到不放心,但他还是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用迷路的说法,曾通这样走也可以成立,但他最后又是如何走出来的呢?是真的因为他所说的,阴森的影子的指点?
也许那不是影子,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地图的旁边,还有一本摊开的笔记簿,那是一个惊人的秘密。除了狱长知道以外,就只有侯风知道一些片段。光是这些片段,就足够说服侯风参加狱长的计划了。他已经在这本笔记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