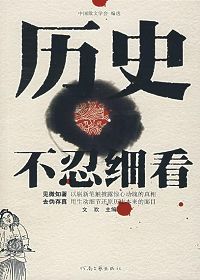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他的钱,还要弄诸股掌之上。只要嘴诓说出来的言辞,面上做出来的态度,毫无破绽,能使他深信不疑,便是要如何便如何,毫无一点阻挡。此次柳娘打定了主意,先来一个虚声恫吓,紧跟着便是调虎离山,安安稳稳拿过四千五百元钱,然后自自由由逃出汉口,还把曹玉琳蒙在鼓里,叫他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固然是妓女的手段厉害,然而施之于这样人身上也不为过。
闲言少叙,却说玉琳回至家中,他那夫人江氏正服药后在床上休息。见他进来,便皱着眉问道:“近来自我有病,你每晚总不在家,至早也要三更以后回来,有时候还住在外边,连夜不归。一问你,你便是有公事,难道你这局子的公事,专在夜间办吗?据我看,恐怕有些靠不住。我从前因为病,也没有神思问你。到底冷眼观看,总觉着你有些神不守舍,大约你许是有了外遇了吧?你如果有时也不必瞒我,只管对我说,我决不难为你。如果相当,我还许接到家来与你做妾。要是不说,倘然被我查出来,那时可别怨我翻脸无情,咱们是到总督衙门去说。”玉琳听了,笑道:“我的太太,你怎么多心到这些地方,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背着你去寻外遇呀。你好好地养病吧,不必操这种无谓的心了。”江氏冷笑道:“你们做男子的,专会欺蒙妇女,别听嘴里说得天花乱坠,心里恨不得飞上天去,把九天仙女,全都搬下来,归一个人享用,那才称心如愿呢。我如今病着,也没有闲心管你的事。不过从今日以后,我要约法三章,每日回家至迟不得过九点。倘然过了九点,我自己到外交局去看。你如在那里,万事皆休,如不在那里,咱们可得从头算这一笔细账,你听见了没有?”玉琳连忙应道:“照办照办,你放心吧。从今以后,我必定早回来。”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想难得这个好机会,柳娘正同我约定七日不去。我有这七天,先把太太哄欢喜了,然后再设法去接柳娘。高低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接出以后,无论如何,也得把她这一关通过。目前只好敷衍着,但求她不追问。俟等接出后,我赶紧发表丁忧,把她们全带回家乡,有什么吵子,回家再说。好在家里有老父替我和解,料想这个母夜叉也无法可施。主意打定,果然从第二天,每晚四五点便回家来。回家之后,不再出门,只在屋里熬药煎汤,伺候床头的胭脂虎。
江氏见他如此驯顺,反认自己是错怪了好人,面子上很假以辞色。这个最短期间内,总算是琴瑟调和。到了第七天,玉琳心想柳娘那里一定很盼望我了。但是这七天内,她为何连一封信也没有,甚至连一次电话全不曾通,这是什么缘故呢?莫非她那男人难缠,始终不曾说好。料想她男人要走了,一定叫人来请我,既无人来,可见一定未走。虽然到了七天,我却不可造次,倘然去早了,生出别的枝节来,岂不更叫柳娘为难?想到这里,便又忍住了不去,直直又忍了三天。已经是十天头上,实在忍不住了,这才坐着马车,一直奔柳娘下处。到了门前,玉琳下车,想要迈步进门,却见门已关闭,门上的灯笼亦摘掉了,大门上却贴着一个红字条儿。玉琳举目细看,见条儿上写得明白,楼房一所,共计七间,如有租者,请至本里第十一号询问,有人带看。玉琳看完了,不觉大吃一惊,仿佛一盆冷水,直从头上淋下来。定了定神,心说莫非我眼花了,如何会有这样奇事?遂又把字条儿看了一遍,对啊,写得不错啊!我倒得问一个水落石出。自己回头,便去寻十一号。隔了六七个门,果然寻着,原来是一座小杂货店。玉琳走进去道了一声辛苦。店主人仿佛认得他,连忙立起身来招呼。玉琳先问道:“那柳娘下处的房子是你的吗?”店主人见问,也不答言,忙缩身到里间去。玉琳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少时店主人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封信,笑嘻嘻地问玉琳道:“你老贵姓是曹吗?”玉琳点点头,说不错。只见店主人恭恭敬敬地请了一个安,笑道:“原来是曹大人,快请里面坐吧,商人有话面回。”玉琳无精打采地走进柜堂。店主人让他上坐,自己在下面相陪,手里举着信,先说道:“曹大人你老可是寻找柳娘?”玉琳道:“是的,你为何会知道?”店主人道:“柳娘住的房子,是商人东家的房。在前一个星期,她就走了。临交房时,柳娘含着两泡眼泪,把商人叫至一间密室内,对我说道:‘五日后有一位曹大人,必来寻我。他如果来时,我这里有一封信,请你交给他。就说我柳娘今生今世,不能再同他相见了,他待我的好处只好来生补报吧。’我问她因何事,必须离开汉口?她对我说,因为丈夫逼迫,父母不肯向着自己,又倒向着女婿,一定要带她回家。如果不从,便有性命之虑,万不得已,所以才随顺他们。所有内中委曲,信内写得明白,请曹大人看信便知道了。”
玉琳不待说完,早已神魂飞越,忙从他手中将信夺过来。见这信封固很严,便用手扯开,将信抽出来,见上面写道:
薄命妾柳娘,百拜上书于曹郎大人阁下:妾自逢君,窃幸风尘中得遇知己,感情日洽,爱情亦日深。故愿定白头之约,终身随君做一侍婢,于愿足矣。不料好事多磨,祸从天降。前夫未死,冒然归来。始念满拟金钱有灵,可以驱其他去。岂知狼子野心,毫无餍足,既要钱,复要人。不从则持刀使剑,百端威吓。伏念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又加以父母不谅,坚持从一之理,无可转圜。遂于某日定妥江轮,强载妾身他去。早知如此,虽一元之钱,亦决不肯向君索讨。在君掷黄金于虚牝,固未必因此介怀。而妾如白璧之微瑕,实自觉问心有愧。每一念及,恨不投身江水,追逐孙尚香之芳踪,用报知己。渺渺今世,永无相见之期。耿耿寸衷,唯矢来生之报。书不尽意,泪与墨俱。
玉琳看罢,不觉放声大哭。店主人反倒百端开劝。玉琳哭了一阵,自觉无味,忙把信揣在怀中,向店主人告辞而去。此时马车已经拉至店门前,玉琳上了车,一直拉回公馆。走进上房,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兀自流泪不止。江氏自从他数日早归,病已好了一大半。今天特备了几样佳肴,预备同丈夫开怀畅饮。却见他进得门来,脸上带着泪痕,躺在床上没精打采的,依然泪流不止,心中不觉大起疑惑,忙过来问道:“你无缘无故,哭的什么?”玉琳被这一问,才想起家中的夜叉婆就在眼前,不应当自己露了破绽,赶忙用袖子将眼泪拭干,一面又笑道:“我并没有哭呀,你许是看错了吧。”江氏冷笑道:“我也不是三岁孩子,连哭笑全看不出来。你一定有什么心事,趁早不必瞒我,快快实说了,好多着呢。倘然被我查出来,你可要自讨无趣!”玉琳笑道:“我没有亏心,也不怕你查。你才好一点,也应该养养神,何必这样操心呢?”江氏见他不肯承认,也不便再往下追,只好处处留心,检查他的破绽。也是活该生事,玉琳满心里只记挂着柳娘,却忘记了衣袋中的书信。夜来脱衣睡下,江氏便暗暗地搜检,竟将这封信搜出来,在灯下观看。他本是世家小姐,幼时很读过几年书,这一封才妓的信她看着毫不挡眼。看完之后,一声也不响,便掖在自己贴身小袄的袋内,上床安息。
次日绝早便起来,梳洗完了,掇一张椅子,在房门口坐定,脸朝着天,不发一语。玉琳起来梳洗过了,便喊着叫套车。换好衣服,便想出门到局子去。才走至门口,见江氏拦门坐着,便笑道:“太太请你闪一步,让我过去,到了上班的时候了。”江氏此时才把头扭过来,沉着脸,在玉琳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忽然冷笑一声,慢慢地说道:“你到什么地方去啊?”玉琳笑道:“自然是到外交局去,难道还有两个地方不成?”江氏冷笑道:“到外交局找谁去呢?”玉琳道:“不过是办公去,还有什么人可找呢?”江氏哼了一声道:“不见得吧。我听说你那外交局里,有什么桃娘柳娘,你不得去请安吗?”玉琳一听此言,仿佛小儿初闻霹雳,立时把脸吓黄。连忙伸手向衣裳袋中,去掏那一封信,哪里还有影儿。这一惊非同小可,立时急得跺脚道:“该死该死,怎么荒唐到这步田地。”江氏似嗔非嗔、似笑非笑地说道:“你总算有良心,还知道这叫荒唐。怨不得自我有病以来,你常宿在外边呢。敢情外交局挪在柳娘下处去了,你早把她接到家来,也省得跑啊!如今人财两空,怨不得你那眼泪比泉眼还盛呢。我如果病死了,大约你决没有这多的眼泪,可见你是一位多情的人了,只可惜你这情用得不当,所以人家不知你这份情,饶骗了你的银子,还叫你害单思病。你自己想想,真有趣味吧。”玉琳被江氏这一片刻薄讥讽的话,说得满脸绯红。自己一想,趁着她尚未翻脸,迎头说几句软话,把她的气平一平,省得打吵子。便老着脸,向江氏深深请了一个安笑道:“夫人说的话全是,实在是鄙人一时该死,错走了路儿。好在事已过去,她这人也走了,求夫人高抬贵手,把这信赏还我。我把它烧了,从此以后,断绝邪念,再不招夫人生气就是了。”江氏冷笑摇头道:“你不必假惺惺,要自己想一想,是朝廷家的命官,又蒙庄大帅特别知遇,委以外交重差。你不洁己奉公,竟敢包揽妓女,真乃是官场中的败类。照这样不如趁早回家,不必在此丢人现眼。我如今既得着你的把柄,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今天便过江去见大帅,倒请示请示,你们做官的人可以自由嫖娼吗?”玉琳受了江氏一顿教训,自己又是羞愧,又是害怕。倘然她真做出来,自己的颜面何在。继而一想,我莫若趁此报丁忧,倒是绝好一个机会。但是阻住了不能出门,这件事却如何发表呢?自己左思右想,十分为难。好在夫妻无隔宿之仇,只可用软磨的法子


![[网王]黑历史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5/539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