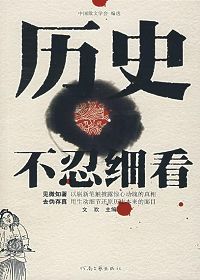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第3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颤着接过命令来看,很厚的磅纸,四围全印着金花边,上面大书:“特派臧汉火为东三省宣慰使。此令。”后面还盖着总统大印。汉火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他本人虽说是誉满全国的大名士,到底那做官的滋味生平还未曾尝着,如今见了这特派的命令,也说不出心中是喜是惧,甚至对于面前的总理应当做一致谢答词,也不知如何开口了。略迟顿了片刻,突然问绍怡道:“大总统这颗印是什么铸的?”绍怡笑道:“自然是金子铸的。你请想,他乃是堂堂一国元首,他的印当然也得格外考究。在前清时代,差不多头品大员就是金印,何况一国元首呢?”这一句话,忽然提醒了汉火,说:“既然这样,我那宣慰使是特任官,当然也可以铸金印了。”绍怡点点头,说:“这是自然的。并且不用你分心,我回头到国务院,便交派印铸局赶紧地给你铸一颗,以便你早日履新。”他这样答着,一面仍周旋汉火,请他入座吃酒,自己也坐在横头上奉陪。汉火此时非常高兴,说:“东三省是我旧游之地,所有地理民情差不多全都熟悉。此番总统既派我前去,我一定要恳切地宣慰一番,决不负总统委托盛意。”绍怡便也乘机奉承他几句,说:“这件差使,要非臧先生去,他人决不能胜任愉快。总统早也就看到了这一步,所以不委他人,独委先生,是知道先生不但有才,而且勇于任事。”绍怡尽着量地一灌迷汤,将这位臧先生灌得晕天晕地,仿佛在云雾里一般。汪、卢两位师爷,便借这机会又放开量灌酒。汉火正在兴高采烈之时,每劝必饮,每饮必空,上好的陈绍,足足喝了有四五斤。因为他本是浙江绍兴人,从幼小时候便酷嗜本地的老花雕,如今得了这意外的喜音,又遇着故乡的佳酿,当然要抖擞精神,痛饮一番。何况同座的三人又有意作弄他,轮流更替地上寿称觞,工夫一大了,又安能不玉山倾倒?始而还能勉强支持,继而舌头短了,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他们仍然不肯罢手,又劝他饮了三杯,这一来,便站立不住,身不由己地便溜到桌子底下。卢师爷忙吩咐长班:“快驾马车,送臧大人回金台旅馆。”绍怡说:“你既知他住在金台旅馆,可以伴送他走一趟。因为他现在是特任官,身份不为不大,倘然路上或是店中出一点岔儿,我们担架不起。况且他身上还带着宣慰使的任命令,要是丢了,更有点麻烦。你同他到金台旅馆,将他交付在王之瑞手中,请之瑞好好地关照他,这是再妥当不过的。你就去吧。”卢师爷答应一声:“是!”左右两个长班,从地上将汉火架起来,把他硬填入马车中。卢师爷还同一个长班在车中扶住了他,然后开到金台旅馆。
王之瑞正在盼得眼穿,满腹疑团,心说这位疯子到哪里去了?北京偌大地方,他地理不熟,倘然走迷失了,如何是好?千不该万不该放他一个人前去,纵然我自己不好追随他,由旅馆中派一个茶房,给他充当长班,也可以放心啊!之瑞正在楼上闷坐,满怀狐疑,忽听楼下一阵吆喝:“臧大人驾到,你们还不提灯笼在前面引路?这是特任的钦差大人,你们开栈房的瞎了眼睛,钦差回来,连睬也不睬。这还了得吗?等回头送你们老板到区里去,打二百板子,自然就明白了。”之瑞一听这话,心里很诧异的,这是哪里来的臧大人呢?莫不成就是我那个伙伴吗?不能够啊?怎会一转眼就变成特任官了呢?他心里一壁想着,早已步出屋外。果见楼下灯烛辉煌,多少人簇拥着一个醉汉,步上楼来。仔细着眼,那醉汉不是汉火却是谁呢?之瑞此时益发如坠五里雾中。少间他们上来,只见内中一位衣服很阔绰的,大声问道:“同住的王大人,在哪一间屋里?”店伙忙跑到头里,指着之瑞道:“这位便是王大人。”之瑞见店伙已经把他指出来,只好向前凑了凑,向问的那人抱拳拱手笑道:“在下便是王之瑞。那位臧汉火先生正是在下的好友,彼此住在一起,不知尊客有什么见教?”那人忙举手致敬,说:“在下是卢金堂,在唐总理宅中充当秘书,现奉总理委派,送臧先生回寓。这里不便多谈,可否假尊寓一叙?”之瑞道:“失敬,失敬!快请屋里坐吧!”又招呼自己的长班,先开开汉火屋门,将他搀进去,放在床上睡好了。然后让卢金堂到自己屋里让茶、让烟,很客气地招待一切,乘势便探询臧汉火得特任官的根由。卢金堂略略地说了几句便起身告辞,又再再托付之瑞照应汉火,防他夜间闹酒致病。之瑞得了这个消息自然是非常高兴,连声答应:“我们是至好的朋友,不劳总理同阁下挂心。”
卢金堂去了之后,之瑞亲自到汉火屋中,但觉得酒气熏人,又听鼾声大作,此时想把他唤醒了询知一切,如何做得到呢?但是之瑞心中打算:连汉火全放了特任官,我那直隶都督,当然是更无问题了。明天他酒醒后,必然详细地告诉我,何争这一宵呢!想到这里,便吩咐长班:“不要离开这屋子,好好地伺候臧大人,防备他夜间要茶要水,倘然呼唤不应,明天我知道了,一定要重重地责罚你。”长班诺诺连声。
之瑞回到自己屋中,越想越高兴,一夜也不曾睡好。直到天快亮了,方才蒙眬睡去。直睡到十一点才起来,匆匆地净过面,便跑到汉火屋中去谈话。此时汉火早已起床,宿酒也醒了,正从怀中掏出那一纸任命令来,反复观看,忽见之瑞走进来,倒有点不好意思的,把任命令向桌上一丢,忙起身让座。之瑞恭恭敬敬地向他作揖道喜,说:“臧先生,大受不可小知,这一来,可以发展你的抱负了。”汉火道:“有什么可喜的?我如何能够做官?老项简直是拿我开胃罢了!唐总理也跟着凑趣,一定撺掇叫我干,我倒闹得进退两难了!”之瑞坐下说道:“为什么不干呢?你从前全是纸上谈兵,如今有了这种机会,倘然要是不干,人家一定要批评你,说你笔下虽有万言,胸中实无一策,这不是授人以柄吗?”汉火道:“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呢?所以勉强答应下来,一切事还得求你指教。”之瑞道:“太谦!太谦!如今做官不比君主时代了,一切手续全都非常简单,并且你这种差使不过是代表总统,抚慰人民,也负不着地方上的行政责任,是很好办的。并且东三省的人民,尚未到开化时代,你这一去,可以发聋振聩,使三省人民耳目为之一新,于民国前途,也是很有利益的,为什么不去呢?”汉火经他这样一鼓舞,不觉兴高采烈指天画地地演说起来,将来到了东三省,怎样开发实业,怎样注重外交,怎样钥启民智,怎样整饬官方,许多题外的文章,全一气说了下来。之瑞在旁听着,禁不住肚里发笑,面子上却又不敢露出来。等他演说完了,方才慢慢地引到自己身上,说:“臧先生此番来京,原为的是在下的直督问题,却没想到一箭双雕,你也随着连带出山,竟做了无心之云,足见人的出处是有一定的。”之瑞说到这里,汉火方才恍然大悟,不觉跺脚道:“坏了!坏了!该死!该死!我昨天去寻老唐,倒是为什么去的!他当时没在家,我朝着他的秘书很发了半天牢骚。后来他回到家中,彼此一见面,他也不容我开口,便掏出命令来,云天雾地地,也不知说些什么,竟把你的直督问题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后来他们三个人轮流着灌我酒,把我灌得失了知觉,方才罢休。及至醒来,身子已经到了店中,我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你的贵家张升在我面前立着,我只得详细问他,这才知道是喝醉了,经他们用马车把我拉回来的。我整整睡了一夜,方才醒来,糊里糊涂。对于你的事,竟未向老唐提及一字,你说糟不糟!”他一壁说着,一壁搓手叹气,表示十分抱歉的意思。之瑞此时,虽然心里很不满意,面子上却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赔着笑脸答道:“这有什么呢?昨天没谈到,今天再谈也不晚,何必忙在一时呢?”汉火刻不容缓地立时便要到唐宅去,之瑞说:“你此番再去,不同昨天了。昨天还是平民,今天便是特任官了。我给你叫一部马车来,派张升跟去伺候,面子上也显好看一点。”汉火大笑道:“民国之中,有什么官民之分?平民也是特任官,特任官也是平民。我就这样去,倒不失我大国民的身份。要马车做什么啊!”他说完了,起身便走。之瑞只得派张升在后面跟着他,还是叫了两部人力车,一直拉到唐宅。
这一回,看门的不敢阻拦他了,立刻将他引到内客厅,还是卢金堂出来作陪。他问总理到哪里去了,卢金堂回说:“今天开国务例会,总理到国务院出席去了。并且臧先生那一颗金印,也得总理亲自向印铸局交派,他们好赶着铸出来,不至误了先生的行期。要不然,就得多耽延工夫了。”汉火听卢金堂说得这样委婉,又兼唐总理出门,是为办他铸印的事,自己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可把之瑞的问题附带着提了几句。卢金堂一力担承:“等总理回宅,我必代先生催问。一两日内,一定有确实的消息。”汉火又谈了几句闲话,还不见唐总理回来,自己觉着久坐很是无味,便告辞去了。
回到店中,据实地报告与之瑞。之瑞口中虽说不慌,究竟心里总有些捉摸不定。有心自己去见唐总理,又怕把事情闹僵了,并且汉火这一面,要叫他知道了我自己出马,不但大大恼恨,伤了朋友的交情,碰巧他一闹脾气,还许要从中破坏,我岂不更吃了大亏?要是背着他,去寻宋樵夫、陈元培那一干民党的人,又必定招他们笑话,说我做官的心太热了,仍未脱前清官僚习气,于自己前途也不见得好。想到这里,倒莫如耐着性儿,仍由汉火这一面慢慢疏通。只是汉火总有些呆头呆脑的,将来难保不误事,这却怎么好呢?之瑞心中真是说不出来的难过。汉火却高兴得了不得,第二天又到唐宅去催,仍然是不得要领。


![[网王]黑历史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5/539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