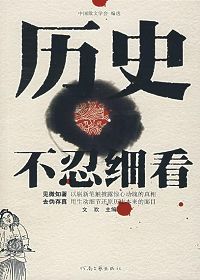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饶了三个响头,方才立起身子来,却又一声不响。只见家中做活的过来,把香案撤去,把帽子银子挪在别的桌上,调上四副杯箸,又搬过三把椅子来。少时从后院走出一位苍髯白发的老头,两个后生随着,一个是长生,那一个却有二十多岁,生得豹头环眼,气象很是轩昂,一齐进了书房。善同忙替引见,说:“这位老翁姓曹,是江苏人,是我的远门姑丈,在山东候补通判,已经多年了。这位少爷,就是他的儿子名叫曹玉琳,在省城什么学堂里读书,说早晚也要做官了。不知我们生儿得何年月日,也能照他父子两个大小弄个官儿做做,也不枉我巴结一场。所以今天恳求老师无论如何,三年以内把你学生教成了,求个一官半职,也不枉我今天磕这许多头。”竹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有心笑出来,又怕他怪不好意思的,只得与大家见礼,高低竹年坐了首座,曹翁相陪,曹玉琳同善同对面坐下,长生在下首打横。少时酒菜上来,虽然是乡间,鸡鸭鱼肉倒是样样俱全。彼此喝着洒,竹年问曹翁因何事到淄川,曹翁说是奉藩宪所委到这里帮审一宗案件,顺便到舍亲宅上走一遭。竹年问玉琳今年贵庚,是读书,还是出来就差。玉琳恭恭敬敬地答道:“小侄现在济南客籍学堂肄业,明年就可毕业了。老伯曾中乡榜,自然是通儒硕学,小侄今天倒要领教一桩事情,不知老伯肯赐教否?”竹年忙谦道:“岂敢岂敢,不知世兄有何事动问?老朽对人向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怕我不知道的,也就不敢强对了。”玉琳笑道:“老伯太谦了。小侄今年廿四岁,家父曾给报捐过一个县丞,依他老人家的意思,等明年毕过业便分省去候补。小侄自念学业毫无,想要出洋留几年学,俟等回来再入宦途做事,不知老伯可赞成吗?”竹年一边听话,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地多喝了几杯,有些酒意了,被玉琳这一问,不觉勾起他的牢骚来,便哈哈大笑道:“世兄,你今天肯将这关系终身学业的事询及老朽,足见你眼力不差,看出老朽不是那迂阔腐败、徒读死书的人。我今天斗胆,当着曹老前辈要大发议论,可不要笑我是狂生,我确实不是狂生。”曹翁道:“岂有此理!老夫子你指教我的孩子,我感激不迭,哪有笑你的道理?”竹年道:“老朽虽是旧学中人,但是如今翻出来的时务新书,我全要买来看看。所以国家的安危,世界的形势,以及中外人情、风俗、政治、法律,种种的不同,我也曾细心研究。到底说一句老生常谈,还得要归之气运。据老朽看,满清的气运已经到了末日了,不出十年,清社一定成墟。清之亡,不亡于真守旧,却亡于假维新。如今派学生出洋,总算是一种最时髦的政策了,哪知留学生愈多,清社的灭亡愈速。多造就留学生,便是清室自杀的利器。老朽一眼早看透将来的结果,到底我心里却是极端赞成。如满清当道之昏暴,各省督抚之跋扈,贪官污吏肆无忌惮;士农工商,四民失业;风俗偷薄,礼教沦亡;政治腐败,纪纲失坠;必须彻底地破坏一下子,然后才有建树可言。据我看,就连这万恶滔天的君主制度,也不能久存人世了。世兄,你拿着这县丞的官儿到各省去候补,究竟有什么出息?莫若趁着年富力强,到外国去学一点实在本事,将来清室亡了,也好做一个开创的人物。虽然说将相无种,也得自己有真学业、真能力,然后才能够乘势崛起。要想再照从前,按部就班,做现成的官儿,只怕以后有点不容易了。”竹年这一席话,说得玉琳同长生全都兴致勃勃,笑逐颜开。只有曹翁面上,却现出一种沉郁不悦的颜色来。善同茫然不知所以,不过听着热闹罢了。玉琳道:“老伯这崇论宏议,实在使小侄闻所未闻,明年毕业后,一定出洋留学,决无二议了。”长生也插嘴说道:“老师,你看门生要随着我曹大叔出洋走一遭,也能够有点出息吗?”竹年慢慢地又干了一杯酒,却不答长生的话,反向善同说道:“东翁,我们宾东相好了三四年,今天倒要支开窗户说亮话。我请问你,是想叫儿子飞黄腾达、升官发财、做个宦途有名的人物,还是叫儿子做一乡的善士、一家的孝子、一代的通儒呢?”这一问,倒把善同问得白瞪着眼,半天答不上来。还是曹翁在旁代为解释了一回,善同才笑道:“先生你要知道,我膝前就这一个儿子,并无三兄两弟,要不为他中举求官,我一年肯拿出一二百银子来请先生吗?什么叫孝子、善士、通儒,我全不懂,只能盼他做个官儿,那不是逆子呢,我心里也是快乐的。”竹年听罢,不觉长叹了一口气,说:“东翁,既然如此,我今年可以不必在府上教书了。现在科举已停,纵然在家里读一辈子书,也休想有个出路,你叫长生随曹世兄到学堂去吧!实对你说,我的本事只能造就他为一个通人,感化他成一个孝子;要求着达到你桌上摆的那宗目的,我实在没有那种把握。最好你叫他入学堂,将来有机会出洋留几年学,回国之后不愁不能做官,这是如今最好的一条终南捷径。你不要错过了,我也犯不上耽误你的子弟。咱们今天的酒,不必做开酒馆,就权当辞行酒吧!”曹翁在旁边却也极力赞成,说老夫子眼光远大,不肯图有限的脩金,误了学生无穷的进步,似这样古道照人的先生,实令人钦佩。善同的脑子里,本来就想叫儿子做官改换门庭,所以每年肯拿出这许多银子来请先生。如今听先生的话是没有希望了,登时面上现出不悦的颜色来,却又不好说什么,只是心里懊悔。竹年又连饮了两杯,蓦地大声说道:“东翁,你这令郎要是入学堂,求功名,将来不患不出人头地,但是老朽有句话你要谨记,长生这孩子聪明有余,诚实不足,而且他的脑力变换太快,将来只怕应了古人的话:是治世的能臣,乱世的奸雄。不但国家沾不着他的光,只怕连你老先生也未必能享着他的福。我如今把他这长生的名字改为敬宗,是叫他顾名思义,将来不至于忘本,却不是叫他学唐期的许敬宗。不知你老先生可乐意吗?”善同道:“我是个不通文墨的人,先生送他名号一定不会错的,就叫他敬宗吧。”此时做活的盛上饭来,大家吃饱了。
竹年果然将自己的书籍收拾了收拾,辞别东家,仍回自己家中教散馆去了。善同此时也并不慰留,倒是忙着同曹翁商量,托他挈带敬宗到济南入学堂,曹翁满口应承。又过了两天,善同备了二百两银子交给曹氏父子,为敬宗入学之用。敬宗果然随着他们到了济南,正赶上中学招考。那时初办学堂,也不考英文。敬宗的汉文从过竹年二年,多少有一点根底,又兼他笔下天生的活泼,居然考入中学。肄业一年,监督很赏识他,应许毕业之后送他到东洋留学。他父亲善同得着此信十分欢喜,同老妻许氏商量,给儿子早早完婚,省得出洋之后,一半时不能归家,耽误了媳妇,不能娶过门来。第二年伏假,便给敬宗成过亲。媳妇的娘家姓蒲,是竹年远门的一个孙女,她父亲也是一个廪生,为人极其古板迂腐。女儿在家,什么《女儿经》、《列女传》,全都教她读过,因此蒲氏倒很能尽妇道。过门之后,什么昏定晨省,侍膳问寝,种种的礼节全能必敬必戒地一一奉行。因此善同夫妇很是满意,常常对人自夸,说我们老夫妻,有佳儿佳妇,膝下承欢,将来的老福,是不可限量的。就是街坊四邻,也全羡慕得很。说章老头子的儿子,将来一定做大官,他这封翁是稳稳当上了。
转眼过了三年,敬宗在中学毕过业了,果然考中了出洋留学。他本堂里四个人,还有师范学堂八个人,一共十二人为一组,定于明年二月放洋到日本去。敬宗年下回家,收拾行装,辞别亲友,此刻却忙了善同。因为儿子出洋留学,仿佛外放了府道一般,得要鸣锣响鼓地庆贺一下子,好叫亲友街坊全都晓得。借着正月请春酒,便预备了十几桌菜,凡是本村外村的亲戚朋友全请来宴贺。大家见他如此高兴,也都跟着凑趣儿,有送喜对的,有送点心的,善同看着,益发快活。等大家吃罢了,他同老妻许氏又重新饮酒,把儿子叫过来,先站起赔着笑脸,让儿子上座。敬宗不觉一怔,心说我爹可真是老糊涂了,那有父子同席让儿子上座的道理,只是立着不动。善同笑道:“吾儿,你自管坐下,为父的有话对你讲。”许氏便一把将敬宗拉至上位,强捺着他坐下。善同便斟过一杯酒来,一饮而尽,说道:“你明天便要起身到省去了,从此一步一步地做起官来,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也不枉我老头子巴结了一场。自从你入学堂以后,连本村的保正同衙门的差役,全都另眼看待。前儿县里派人来要车,做活的告诉他说,送少爷进省赶考去了。街坊李大又暗暗告诉那人说,他们老章家现在出了洋学生,早晚还要做洋老爷呢!你不要大呼小叫的,照从前那样横。如今连皇上家全怕洋人,那洋学生是洋人的徒弟,连你们老爷全惹不起,你何必讨苦吃呢?什么地方没有车,单上这村里来。这几句话居然把差人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地去了。我听了心中好不快活,原来洋学生三个字就有这大的势力,将来到外洋去几年,回来一定是洋老爷了。做了洋老爷还不定怎样威风呢!只怕县太爷全得来给你请安。那时我老头子也沾你的光,做一位洋太老爷,谁敢不恭敬咱们?”许氏道:“可不知洋太老爷戴什么颜色的顶子?”善同略一沉吟笑道:“洋老爷官顶大,一定是红顶子。洋太老爷是洋老爷的爹,似乎比洋老爷又大一层,大概须戴绿顶子吧!”许氏道:“为什么要戴绿顶子呢?”善同道:“你妇人家懂得什么?蓝白金顶全比红顶子职分小,如今要大过红顶子,怎能不戴绿顶子呢?”老夫妻正拌着嘴,媳妇蒲氏进来,对公婆说道:“他的行李我已经全收


![[网王]黑历史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5/539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