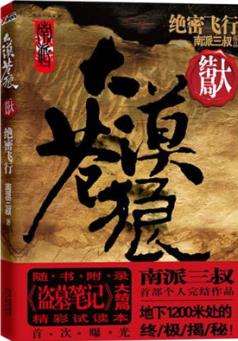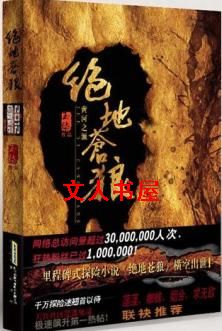苍狼与白鹿-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或许自己真的将以女婿的身份成为他的继承人。
想到岳父家,铁木真不禁以挑剔的眼光检视着自家的帐幕。这是在原来的帐幕被他出生时的那场人为大火焚毁后由也速该亲手重建起来的,然而曲指算来也使用了将近十年啦,各处的边边角角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徒中被磨得开了花。即使内部比起其他家庭显得宽敞些,可是破旧程度却别无二致。里面的陈设也并不超过任何一个普通牧民家庭。虽然也有些贵重物品,但距离丰富二字还差得远。通过对其他部族战争所掠夺来的战利品,往往是平均分配,做为族长的他,也没有为自己多留一根羊毛。全部族中既无超越一切的上位阶级,也没有低人一等的底层阶级,也速该做为族长的行政权力也仅仅是在别人无法裁决的事情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发生战争的时候,则成为一名临时统帅而已。确实,仅此而已。
对此,铁木真没有任何抱怨,他甚至为此感到庆幸。
“至少不会遭到过于严厉的报复吧?”
就现在这个处境而言,能平安的活下去已经是奢侈的念头了。当他看到母亲还在为收复前夫的权力而做着徒劳的努力时,觉得她还没有自己看得更透彻。相对于泰亦赤兀惕人的摇唇鼓舌和乞牙惕本族的离心离德而言,母亲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相颌颉。
“一切已经存在的事实都有其产生的道理,这道理往往最符合与长生天的旨意!”
当在也速该的春祭上倍受欺凌的母亲向铁木真诉说委屈的时候,他初默不作声听着,直到结束,才冷冷得回答道。希望母亲能在自己的当头棒喝下从幻想中醒来。
猝然遭到儿子冷遇的诃额伦不禁有些吃惊得凝视着铁木真的脸,她简直不相信这样成熟老道,洞悉世情的话语居然出自一个不满十岁的少年口中。刹那间,儿子在她的眼中变得异乎寻常得高大起来。以家庭剧变为催化剂,少年跳跃式得成长起来,切实得将亡故的父亲留下的家长担子挑在自己的肩头。
“泰亦赤兀惕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春祭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我们一家的命运今后将落入一个更为悲惨的境地,就像河中之水般,只有冻结为寒冰,才能稍得安稳。全家人要对此有所觉悟。”
铁木真扫视着弟妹们那一张张惶惑的脸,半是训诫他们,半是告戒自己。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气候下,他悄然度过黯淡的十岁整生日。没有祝福,更没有礼物,有的只是母亲的哀叹和敌人的阴谋。
※※※※※※※※※
关于这次为也速该举行的春祭(1),事后被许多人判定为公开分裂的信号。表面上,发难者是也速该的另外两名侍妾——幹儿孛和莎合台(2),但即使是瞎子也能看出,她们只不过是两具在前台表演的牵线木偶而已,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正是日夜渴望着恢复俺巴孩时代权势的泰亦赤兀惕人。这次春祭上,诃额伦虽然以死者正室遗孀的身份争到了主位,但在分祭肉的时候,却明显得被故意忽略掉了。
面对这种公然的挑战,诃额伦勇敢得应战。她毫不犹豫得指出对方的错误:
“在也速该的灵位前,你们怎敢如此?不错,他是故去了,可是他还有儿子,莫非你们认为他的儿子长不大了吗?你们故意忽视我,是不是打算就此抛弃我们?”
“没错!象你们这样没本事的废物,凭什么留在部落中吃白饭?诃额伦,你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强援在后的莎合台用尖利的嗓音率先叫嚣起来,幹儿孛也不甘落后得跟着喊起来:
“是呀,象他们这样的废物,有什么资格在乞牙惕里混下去?睿智的捏坤太子,稳重的阿勒坛,还有勇敢的答里台,我要求你们以长老的身份召开库勒里台(部落大会),做出起营迁移的决定,将他们母子丢下!”
正是这个女人,十年前便试图乘也速该出征之际烧死诃额伦母子。虽然包括他的兄长在内的直接行动者们都被一一逮捕、处刑,然而她本人却用花言巧语骗过了也速该。而诃额伦本人也不愿因此而造成更多的杀戮,最终放过了她。谁能想到,当年的大度却为今日的变故埋下了祸根。
一切都是事先导演好的。几个有身份的长老们立刻答应了两个被嫉妒之炎烧光理智的女人的无理要求,一个装腔作势的库勒里台在两个月后正式召开起来,身为前族长遗孀与长子的诃额伦和铁木真却被完全排除在外。经过一番虚张声势的磋商与讨论,其实答案本身就已经不言自明。那些毫无人道的言论居然形成决议,并即将被执行。唯一对此提出异意的,只有来自晃豁坛族的察剌合老人。只可惜,在注定倾倒的大厦面前,一根细木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无论他的口才如何便给无碍,也终于未能改变众人的心意。
这就是今晚为何会如此骚动的原因所在。
看着族人们忙碌得清点羊只与马匹,进进出出得收拾帐幕内外的物品,进而拔起固定帐幕的木楔,卷起帐幕,连同杂物一起放上大车。没人看铁木真一眼,即使是走过他的身边,也对其熟视无睹,仿佛他是个徘徊于草原上的幽魂,或是如空气般的透明人。
面对这种公开的背叛,铁木真只是静静得旁观,一言不发,仿佛这一切与己无关。十岁的他有着大人的沉着,冷冽如铁的脸上,没有一丝感情流露在外。没有人知道这一夜他在想什么,即使多年以后,他也从未向任何人提及。于是铁木真在这夜的思想活动成为了一个永久的谜团。
后人们经过猜测和臆想,演绎出了铁木真的行动。他穿行在埋首搬迁的族人之间,询问他们为何如此匆忙。得到的答案是:奉泰亦赤兀惕人的命令,搬迁到新的牧场去。
铁木真大声质问道:“追逐夏日丰美的水草是牧人的天性和权力。可是这种权力为何要受泰亦赤兀惕人的指使?”
没人回答他。
他又继续追问:“这个决定为何没有告知我家?”
依旧没人回答他。
“做为也速该的儿子,在新族长没有选出之前,即使是库勒里台的决定也要和我商量,现在你们连句招呼也不打,是想抛弃我们吗?我们一家难道真的是多余的人吗?”
铁木真怒不可遏。这种公开的背叛令他心中的愤怒提升至顶点,发出了足以盖过怯绿连河滔滔水声的咆哮。
终于,有个老人轻叹一声道:“孩子,认命吧。”
黑暗中有人附和着:
“你这小崽子别叫嚷了,吵得人耳朵疼。乖乖回到你妈怀里吃奶去吧,别在这里碍手碍脚得耽误我们上路了。”
嘲笑的声音,漠视的眼光,不屑一顾得冷遇令铁木真全身震颤着,他将双手握成了拳头,莫大的悲愤所带来的力量凝聚其上,但却不知该打向哪里。
这样的描写,虽然很生动,但显然是出自对铁木真的性格一无所知的民间艺人的杜撰。他们在这里将铁木真按照寻常人遭到不公正待遇后的表现经过添油加醋得艺术化处理放大起来,却没有留意到其中所流露出的不知所措和鲁莽轻率。
他们忘记了,铁木真那样的人是不会做出任何徒劳无益的举动的。在此,我们仅仅将其做为一种反衬来加以叙述,从而区分智者与匹夫之间的天渊之别。
同样被惊动的诃额伦的表现却成为流传于草原上的一段佳话,从而使她成为了一位蒙古妇女的典范,以诃额伦母亲(月伦—额客)的威名被载于史册,传于口头。铁木真看到母亲骑着父亲生前出阵时常常乘跨的那匹银灰色骟马,手持象征着乞牙惕氏王权的白旄秃黑(用白色马尾妆饰的旗帜),驰骋于叛离者的人海中,高声呼喊着也速该的名字,向族人们发出呼吁:“还记得这杆为乞牙惕家族带来无上光荣的秃黑吗?失去这些,你们还有什么?从此甘于象泥土一样被人踩在脚下吗?”
没人看她,也没人回应她。秃黑随夜风翻卷飘舞,不时发出猎猎之声,在曦微的晨光中显得无力而渺茫。失去强力支配的同时,它的生命力亦如流云逝水般一去不复返了。在众人的眼中,这一家孤儿寡妇已经毫无意义了。
铁木真以怜悯的目光遥望着徒劳呼唤着部众的母亲。他知道,这样的行动不会起任何作用,却也没有上前阻挡的必要。这是一种态度,失败却未必要屈服,但自己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毋需事事效法母亲。因此,他既不上前相助,也无意去阻止,只是站在帐幕前用沉静的目光观察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越来越多行色匆匆的牧民们从各个方向赶着驼马、车辆和牧群,神情木然得汇聚到自家帐幕前的开阔地上,茫然无序得列成大大小小的集团,或一个家自成一群,或几户结为一伙,舍弃熟悉的土地,冷漠而颟顸地从手擎秃黑的诃额伦马前缓缓得走过。
在走过的人丛中,诃额伦看到了蒙力克,看到了捏坤台石和答里台这两位也速该的亲兄弟,也看到了阿勒坛——前忽图剌汗的儿子,也速该的表兄。她向他们发出了呼吁:
“捏坤台石啊,答里台啊。也速该从未亏待过你们呀!战场上保护你们,营地中维护你们,你们的羊群比他的要多啊!”
“阿勒坛,也速该杀了多少塔塔儿人呀!他从未忘记忽图剌汗的仇,可当他死在塔塔儿人手中的时候,你却在做着什么?”
“蒙力克,你忘记了什么啊?忘记了也速该对你的临终托附吗?他的灵魂在天上,借助我的眼睛在看着你呢!你难道连巴刺合赤的一半也及不上吗?”
被呼唤的人中,前三人只有让身体尽量远离诃额伦,他们的部下则满面沮丧,仓惶奔走起来。显然,诃额伦的责问曾经在适才的片刻之间唤起了他们心中某种微弱的动摇,然而看到自家首领们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后,便不再有任何表示了。
被诃额伦提及的诸人之中,唯有蒙力克将头埋得更深,脚步也愈发慌乱起来,甚至有些踉跄。一瞬间,他似乎要停下,但终于没有停下。忽然,他的衣襟被人抓住,向后猛扯。接着,那人超过了他,拦挡在他的面前,同时也阻住了另一些人的脚步。
“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