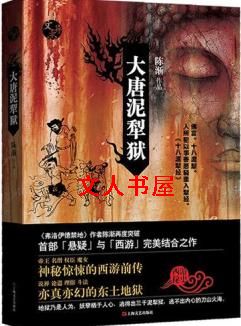飘在大唐-第3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二人连干几杯,但觉胸中意气暗生,激荡不已。一时忘情,竟一起唱起了军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大唐壮士兮气壮山河;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壮志凌云兮气冲牛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万众一心兮气拔山岳;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
乃是李愔和《英雄曲》而作歌,与壮士杀敌时同唱,久而久之成为大唐军歌。
不知何时,雨渐渐停了下来,冯老三的“无肉汤”早已上来。冯老三蹲在檐下柱子旁,从怀中取出干馍,撕成小块,放入汤中。虽然无肉,冯老三嗅一嗅肉汤,面上也不由挂起满意的微笑。
听到二人的歌声,冯老三不由微微侧目,听了片刻,嘴角突然掀起一丝与他的面容极不相称的笑意,摇着头含混地咕哝道:“历来战争不过是仨人打架,有什么意思……”
刚好有一人正往驿站里走来,听了冯老三的咕哝,上下打量了冯老三几眼,突然向冯老三稽首道:“这位先生有礼了。”
冯老三抬头去看来人,见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眼光淡定,神色从容,似虚怀若谷,却又虎虎生威,实在是个少见的精干睿智之人。
来人毳冕七旒,紫褶平巾,金剑饰,一身武官袍服,而且至少是个三品高官。然而此人却未带一个随从,更无仪仗,只身一人穿了朝服骑马而来,实在是令人纳罕。
冯老三眼中闪过一丝怪异,见此人向自己行礼,唬了一跳,忙还礼道:“官爷有礼。”
来人眼光一闪,温言道:“敢问先生,刚才说的‘战争不过是仨人打架’是什么意思。”
冯老三敦厚地一笑道:“先生不敢当,官爷若不嫌弃,称小人冯老三便是。”
来人官职虽高,到也随和干脆,点头笑道,“好。冯兄弟若不嫌弃,与在下一同吃杯酒如何?”
冯老三诧异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摆手说道:“小人不过是乡野粗人,怎敢与官爷同坐。”
来人温和一笑:“冯兄弟说笑了,在下当年也是乡野之人,如今虽穿了一身官袍,却也不敢忘记自己乃是何人,还请冯兄弟莫要嫌弃才是。”
冯老三抬头上下打量来人,突然呵呵一笑,拱手道:“官爷若是想问刚才的话,其实小人也不解其意,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道听途说?”来人不解地望向冯老三。
冯老三抬头看了看天,笑道:“前些日子,也是这样一个雨天。小人路过渭桥,正要往桥边的驿亭里避雨,刚巧有个年轻书生与一个和尚在桥上,二人即不打伞也不躲避,在桥头望着河水幽幽闲淡。小人觉得甚为奇特,便留意听到二人谈话。似是正在谈论当年圣上在渭桥退兵,与突然可汗桥上立盟之事。小人知道此事,因而听得仔细。
后来,那和尚突然慨叹一句:‘历来战争不外乎是俩个人打架。这两个人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放牧的,放牧的见种地的地里面可以长出许多好多西,不像他那样只有肉可吃,心生羡慕,想要地里的东西,种地的不肯,因而来抢,一来一去便打了起来。’
小人听着好笑,便多听了几句。至于什么意思,却也听不明白。”
亏这冯老三看上去拙嘴笨舌,说起话来却条理十分清楚。
“俩人打架?”来人沉吟片刻,笑道,“不错,这天下的战争,自来便是草原上以放牧为生的民族与中原耕种为生的民族的战争最多。岂不就是一伙种地的和一伙放牧地在打么。然而‘仨人打架’却又是何来?”
冯老三继续笑道:是那年轻书生听了和尚的话,点了点头,却又摇头说道:‘不对,其实是仨人打架。’”
“怎么又是仨人打架,多出来的又是什么人?”
冯老三道:“当时和尚也有此问,那年轻书生回道:‘除了种地的和放牧的,还有一个野人。’”
“野人?”来人奇道,“何为‘野人’。”
“书生说:‘以渔猎为生,不事生产,岂不就是野人?’”冯老三笑道。
“渔猎为生,不事生产?比如靺鞨人?”来人听了一愕,想了想又摇头笑道,“的确是‘野人’。然而区区几个‘野人’又能成什么大器。”
冯老三道:“和尚听了也是如此说法。那书生却坚持道:‘野人见放牧的有肉,种地的有菜,眼一红便都来抢,因而这历史中的战争向来是仨人在打架。’”
来人听了不住点头,想了片刻,却又摇头,不无怀疑地自言自语道:“一群野人果真有如此大能力?抢得过放牧的与种地的……”
也难怪来人有此想法,别说大唐眼中,便是在突然、薛延陀等这些游民族眼中,那些光脚打猎的靺鞨人,又怎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当然,若他们知道这些靺鞨人的后世子孙,也就是后世人称的女真族,曾建金与清,大概便另当别论了。
冯老三边看来人,边笑道:“我也不大明白。只是那年轻书生说:现在人们看不起野人。没准哪一天,野人忽然野性发作,突然攻了过来也说不定。”
来人听了此话,却已怔怔愣住。
冯老三温厚一笑,道:“小人的确也不明其中意思,不过是道听途说,觉得有趣而矣。”
见来人怔怔一时不言,当下也不再多话。三下五除二将汤馍吃下肚,打了个饱嗝,才道:“官爷若无他事,小人告辞了。”
说完也不等那人答话,起身走向驿站内,将汤碗还了驿吏,又从怀中摸出一文钱付了“无肉汤”钱。回头看了一眼座中吃得微醉地冯文瓒与薛仁贵,不自主的嘴角挂起令人难以捉摸的笑意。
恰好冯文瓒正回头向驿吏招呼添菜,四目相对,冯文瓒见了冯老三脸上的笑,不由一怔。
冯老三拉了拉头上的草帽,低头向门外走去。
“你,你是……”冯文瓒突然觉得冯老三似是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何人。
站起身正想追出去,那个穿朝服的武官刚好走了进来。
“英公。”见到来人,冯文瓒与薛仁贵不由同时叫道。
原来来人乃是英国公李世勣。
“英公怎会冒雨到此?”三人见过礼,冯文瓒奇道。
李世勣笑着说道:“正要去叠州上任。”
“去叠州……上任?”冯文瓒听了,却是更加惊奇,诧异地道,“英公到叠州任什么职?”。
“都督。”李世勣道。
“叠州都督?”冯文瓒不由惊得目瞪口呆。
李世勣见了,微微一笑道:“莫非冯兄弟认为都督一职太高了?”
冯文瓒慌忙连连摇头,半晌才期期艾艾地道:“都督虽然在叠州最大,可英公乃是何等人物。同中书门下三品,朝廷重臣,怎会突然被贬到叠州?打死在下也不信,英公莫不是说笑。”
也难怪冯文瓒不信。叠州地处陇右道与剑南道交界,与吐谷浑相接,名不见经传,实在是个即偏僻又不起眼、人烟稀少的荒凉之所。
李世民一向对李世勣十分看重,曾经亲口说过:“英公当年不负李密,定也不会负朕,将来太子要托付英公照看。”
说此话时并非秘密会谈,而是在大内两仪殿宴会群臣时所言,无人不知。冯文瓒曾是大内禁卫,岂能不晓。
如此依重之臣,又怎会被故意贬斥出京,远离政治中心?
李世勣到是不以为然,从容地道:“到哪儿还不都是为朝廷效力,没有什么贬不贬。我的一切皆是圣上所赐,怎不为圣上效力?!我刚刚奉诏,正往叠州去赴任。连家都不曾回,因而穿了朝服走到此处,岂会有假。在此稍歇片刻,也是要家人送常服来。”
“莫不是太子……圣上知道否,怎能任他胡来?”冯文瓒眼光一闪,突然脱口说道。
李世勣微笑不答。看了看冯文瓒,见他眼中闪出一道又惊又喜之意,不由暗暗摇头。
冯文瓒乃是蜀王李愔死党,这一句脱口而出,为李世勣打报不平,却也难免半真半假,存了几分他意。只是太着痕迹,便是薛仁贵听了也不由摇头,李世勣岂会不明其意。
薛仁贵暗中拉了拉冯文瓒的衣袖,摇头道:“英公调职,实是圣上地亲自做出的决定。”
“圣上?!”冯文瓒这下却是真得差点吃惊地跳起来。张大一双圆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冯老三正在屋檐下牵牛车,冯文瓒的惊叫声音极大,他到是听了个清清楚楚。突然低声咕哝道:“公主果然料事如神,说圣上安排后事,定会贬英国公出京。看来这次不只卫公病急,连圣上也真的病急。”说完摇了摇头,拉着牛车缓缓而去。
无故贬英公出京,是李世民在安排后事?实在令人费解。
难怪冯文瓒一时不能相信。听薛仁贵说乃是圣上的安排,更加无法理解。
“圣上怎会如此?无缘无故……”冯文瓒此时到是真的有些义愤起来。
李世勣笑着看了看薛仁贵,却依旧是安之若素。见冯文瓒言语有些不敬,忙转开话题道:“刚才在檐下见到一人,说了会儿话,言谈却是极为高明。说‘历来战争不过是仨人打架’……”
当下将刚才冯老三说的话,向二人转述一遍,二人听了,也觉有趣,却又越想越有道理,不由相视而笑。
“仨人打架?!亏他想得出来。”薛仁贵笑道,“是什么样的人物,竟然有如此见识,定当认识一下才是……”
“便是刚才进来结账出去的那人。”李世勣点了点头,不无遗憾地道,“我本想请他吃杯酒,不想他却不肯赏脸……”。
“东天王。他是东天王!”不待李世勣说完,冯文瓒突然惊叫一声,跳起身来,一溜烟儿追出门外。
“东天王?”薛仁贵与英公李世勣听了,也不由大为惊诧,忙跟了冯文瓒一同追出,却哪里还有踪影。薛仁贵原本也认得东天五,只是刚才他背对门口,因而没有看到。
当下不及细说,冯文瓒与薛仁贵二人骑马分头去追。
追了里许,依旧不见踪迹。天知道,那牛车为何会走得如此之快。
约莫半刻钟左右,二人又重又回到驿站,皆无所获。
冯文瓒连连跺脚,急道:“刚才我只觉得他十分面熟,怎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