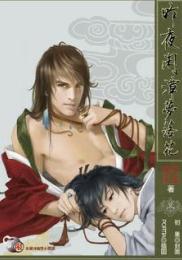汉宫秋 落花逐水流-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皇帝回身嘱咐楚姜:“皇后娘娘身子要紧,莫让闲事扰她清静。你们且看着,朕下了朝再来。”回头只瞧陈阿娇一眼,甩袖便走。
陈阿娇伏在大迎枕上,粗粗喘气儿,目色窒了窒,突然一屈身,竟将喝下的汤药全呕了出来!
身边宫女子已伏倒在地,匆匆一谒后,开始手忙脚乱地服侍着……
才迈出没几步,皇帝蓦然停住了。
杨得意极会看眼色,心知皇帝不忍,眼下便有了取宠着手处,因道:“不紧着点儿!娘娘金枝玉叶,你们这样懒怠伺候,凭你们有几个脑袋掉?”他身阶已算仆从之中极高的,原不应亲自料理这样的“唐突”,但杨得意心里小九九转的极好,皇帝眉色一浅一浓,他皆看在眼里,皇帝此刻仍在意陈后,他自然要为日后位阶前途再铺陈一番。因捋起袖子,直要亲自来,唬得身边围着的宫女子连连磕头:“婢子能伺候,长侍且歇着吧!”
皇帝皱了皱眉:“尽添乱,宫里有的是手脚伶俐的使唤,这些小事若然不能料理,掖庭养着她们作甚?你退开——”
杨得意有些不明白了,皇帝教他退开,自个儿却顶上了——皇帝这会儿不提上朝之事,大抵将朝上诸臣都抛诸脑后了,他走前几步,唬得一众忙活的宫女子连连下谒:“陛下,陛下长乐……”
皇帝虚摆了摆手:“且别紧着‘长乐’,朕没这个心思。皇后这是怎么了?”他已坐到床沿,陈阿娇将脸撇过去,皇帝轻“噫”了一声:“你不是说你不怕朕?那你这是躲苍蝇?……朕上赶着看你脸色,巴巴贴着脸做苍蝇的?”
陈阿娇不理他。
楚姜因回谒道:“娘娘将汤药全呕了……禀陛下,只怕今儿晚又得起高热了,这可怎么好,这数夜来,熬的可怜!”
最后那半句话,声音极轻,像是自语,却是说给皇帝听的。楚姜这样敏慧,自然极力为自家主子挣些恩宠来。
果然,皇帝觑她一眼:“那尽是可怜,你们伺候便是。药吃不下怎么行?灌也得给她灌下去!”
陈阿娇挪了挪,仍是没回头。心里只发恨,心道刘彻你可真狠,你打小不肯吃药,本宫哪回不跟你站一处的?这回倒好,长成了皇帝,生硬了翅膀,心子也愈发狠,本宫不吃药,还撂你这儿强灌呢!
忽然便觉得颈窝下一凉,再接着,便有一双手直触了她脸来,是生冷的凉气,阖盖了她满脸,怪舒服。
“还烫呢,待他们煎了药来,朕喂你。”
要换作平时,陈阿娇早厚皮厚脸地忘了皇帝待她的诸番不好,只这一时,她内有心事,因长乐宫唁信这一出,被刘彻给瞒了下来,害她连皇慈最后一面儿都没见到,她恨刘彻恨的紧,因此连他刻意讨好也不理。
刘彻到底是皇帝,自小养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十六岁践祚始,登临大宝,宫里的女人个个赶着讨好他,他何曾受过妇人之气?这会陈阿娇在他面前使性子,他也不受用了,扳过她的头:“瞧着朕,”他负了气,只说,“瞧朕。”
作者有话要说:这些写的有些长了,我怕大家忘了。。。提醒一下,皇帝现在是在宣室殿批改奏折,去探陈阿娇的病是昨晚离开卫子夫宫中的事情,他在回忆。也就是说,以上写的,都是皇帝下朝之后回到宣室殿,没事想起来的~
☆、第34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4)
陈阿娇脾气拧的很;和刘彻两人;针尖顶针尖儿的刺人;她哪肯任他摆弄?因撇过头去,看也不看皇帝。
皇帝生了气;亦是拧道:“陈阿娇;你好大的胆性儿!我知你不怕死,倒是个硬骨头,只不知……”皇帝冷笑:“你陈氏满门;个个皆是不怕死的?!”
她一窒,转过头,又死撑着要坐起,皇帝倒是虚扶了她一下,被她挡开。她眼色极冰冷;就这么瞅着皇帝,把个刘彻盯的毛骨悚然,皇帝哂笑:“你别这样看朕。”
她吸了一口气,拼着不怕死的劲头,因忤皇帝:“陛下乃明君,古来明君,哪个不是刽子手?秦始皇如是,我看陛下,亦是不遑多让!”
皇帝虽则生气,亦是没摆面儿上,算抬举了她几分薄面。因冷笑道:“你把朕与秦始皇作比,那是好词儿,朕犯不来跟你生气。陈午作逆,朕本就是要收拾的,将来,免不了对陈氏用重典,亦算朕负欠你,——所以,此番你再说大不敬之话,朕都忍。”
她算被一泼冷水浇透,可算实打实地惊醒了来,乌漆的瞳仁只死盯皇帝,指甲揿着软锦,真要抠了进去,生生的疼。
“陛下是打实了心子要收拾陈氏的?本宫不信是父亲做事不明,才惹恼了皇帝,大约……陛下打八百年前,便实心要拿我堂邑陈氏开刀以慑朝廷,是么?”她的眼睛很漂亮,恍如一片平静的湖面,有高鸟的影儿掠过,直把皇帝吃了透。
刘彻道:“好好养你的病。这关你什么事?”
“不关我事?天家不计骨肉情分,这本宫知道,但……”她含了手指在嘴里,像小孩子一样,那眼神,出了窍似的飘远了去:“但臣妾不是天家人!臣妾有父有母,承堂邑侯府养育,恩情深重!如今父亲有难,怎样不关我的事?”
“这话说的,倒好像朕是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乜她:“怎样说话的,陈阿娇?”
“皇帝已说过,免我大不敬之罪,阿娇生来这样说话。”
皇帝笑笑:“好,好……你尽说。”
得亏是陈阿娇,他自幼一块儿长大的青梅,脾性摸的顶透,陈阿娇说一是一,有甚么不敢做的?要换作宫里任何一个女人,敢这样忤他,十个脑袋也摘下来了!
“皇帝陛下不念天家骨血之情……阿娇早觉奇怪,从来孝谨的彻儿,居然连皇外祖母唁信都瞒着,陛下安的是甚么心?皇外祖母是得病猝死,亦或……只怕还有待斟酌!”陈阿娇伏低了头,只顾把玩手下攒丝流穗,也不看皇帝,或者说……是她不敢看。恁是再大的胆子,亦知怎样的话是可说,怎样的话忍死不能说,她这些胡嚼道的,可真要气坏了圣躬!
她话中暗指皇帝夺权弑祖,刘彻能咽下这口气?不掐死她已算皇帝仁德!她不傻,又是宫闱之中走绊这么多年的,能数算不清何为轻、何为重么?
可她偏要赌上一把,激一激刘彻。
皇帝大怒,当下立身,一扬手,甩开低一伏高一伏挂着的吊幔,“撕拉”一声,半幅攒金丝吊幔竟被他扯了下来,杨得意吓怔,连伏地,身旁宫女子旋即呼啦啦跪了满地,殿内寝,只剩极细小的呼吸声,端无旁的人再敢说话。
皇帝恨毒了她。气不能出,连话也说不来。半晌,才端看她,严威伏于内心,似笑非笑:“陈阿娇,你的意思是,长乐宫皇慈病故,实乃朕之大罪,是朕……端无半分忠良之心,害了皇祖母?”
“焉知不是?”
好个陈阿娇!
“你这话何意?”皇帝气得满头面雾煞煞,直龇她。她仍是好汉一条:“陛下知道我是怎么个意思。”
“你意思是,朕弑祖杀亲?长乐宫老太后薨,朕还得负全责,背上这样个不忠不孝的罪名?”
她不饶人:“不忠且不算,皇帝陛下乃我大汉一等一的明君,忠陛下、忠朝廷,且才能算一个‘忠’。”她语带讽刺,又道:“满朝文武,只有忠陛下,才算‘忠’,堂邑侯吾父,触忤陛下,那便只有‘死’字一个。因此忠君之说,全无旁述。但这‘孝’一字,皇帝陛下自己掂量,您配?”
杨得意未等武帝发怒,便抢了前,磕头如捣杵:“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娘娘烧糊涂啦!全不知自个儿在说些什么,待会儿醒转过来,娘娘定然是第一个后悔!陛下、陛下万万息怒!”
绡纱外是轻转的风,蹭抚满庭院树叶沙沙作响,薄透的夜,早已被天边一道曙色撕拉开,天将晓,清凉的气息散了满院。春色渐渐爬上树梢。
皇帝踱步,忽地杵道:“娇娇,我们能不能好好说会儿话?”
是轻缓的口气。
他仍温柔。
凭陈阿娇这几句忤逆之言,皇帝杀她万次也不够,都道君心难测,这帝王的心,果然是万万的深不可测,他竟不太着恼了。
“陛下,你好久没有叫过我‘娇娇’啦。”
像是梦话。柔的好似从天光之外延伸来,她在做梦。
窗外是满树落红。
“娇娇,你总不肯说软话。宫闱门庭深,吃亏的是你。”他微微叹息:“朕讳彻,你也好几番不曾这样喊过朕了,总不是朕亏你,朕也被你亏待。”
“陛下,”她忽然扯他袖子,“几时发丧?娇娇是糟践命,搁长门永世不得翻身啦!但好歹皇外祖母疼我一世,娇娇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总要……总要送她最后一程……”
皇帝微一怔,淡淡道:“时候不早,朕要上朝了。”
他到底还是心狠。
“陛下起驾——”
杨得意熟稔的“唱起”,撕开长门冷宫破晓的天幕。清晨,气息凉嗖,满地落瓣似蝴蝶一般,旋转在涡风里……
斜倚熏笼,坐到明。
皇帝一早上心不在焉,伏在宣室殿御案前,想事儿出了神。自陈阿娇那边出来,便伏宣室殿批阅奏折,连上朝都懒怠。杨得意催请再三,才懒懒应付朝上去了。
这一回来,又想心事。杨得意立一边伺候着,只琢磨皇帝心事,因寻思着,九成九出塞战事不力,再加一根搅屎棍陈午,有的君上烦扰呢!
故不敢言。
谁料皇帝反是先开口了:“她怎样了?”
杨得意只挠头,想了半天,才回上来:“好的很呢,陛下宽心,娘娘刚吃下汤药,又炖了燕窝,手脚伶俐的宫女子正伺候着,半丝儿怠慢也是没有的,过不几时,就该来宣室殿请早安了。”
皇帝愈听愈不对劲:“杨得意,你别给朕打马虎眼——”
杨得意略一伏身,只叫屈:“奴臣不敢、奴臣不敢!奴臣所禀,皆属实。娘娘凤体大安,腹中小皇子亦是……”
皇帝皱皱眉:“你说谁呢?”面上已有不悦。
杨得意恍悟,只恨自己脑袋长的不够刚硬,万一圣上龙颜大怒,自己项上这颗脑袋,顶得上几轮刀斧砍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