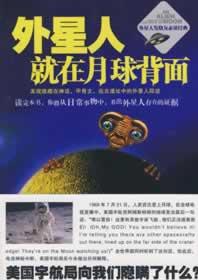关山月-第8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管奸来路,歹来路,绝对跟关山月没关系。
他俩是先来的,原就在座,不是跟着关山月进来的,而真,从关山月进来到如今,也没看过关山月一眼。
就凭这两样,绝对跟关山月没关系。
既然没关系,关山月就既不必关心,也不必在意。
伙计躬身哈腰,满脸陪笑把茶送来了,又躬身哈腰,满脸陪笑的走了。
关山月喝茶了,也听曲了。
茶既然送来了,不能不喝;曲既然唱上了,也不能不听、边喝茶,一边听曲,一边等,等有人盯他,等动静。
他认为,“黑白双煞”应该已经知道他来了“九江”了!
盯他的人该出现了!
虽未必会有什么动静,但盯他的人该出现了。
是么?
每个地方都少不了有要饭的,要饭的也会挑人多的地方跑。
“九江”也不例外。
本来嘛,人少的地方要什么饭?跟谁要?
叫要饭的,手伸出去要的可不都是饭,也要钱,要到了钱,一样能买饭填饱肚子。
既是要钱,当然往人多的地方跑。
同样的,酒楼、茶馆人多。
要饭的会往酒楼、茶馆这种人多的地方跑;酒楼、茶馆这种地方的掌柜、伙计也都会装没看见,不会管,不会赶。
要饭的可怜,谁不同情?行好、行善也为自己积德不是?
要饭的必会有分寸,约束自己,绝下会成群结队往一家跑,一家顶多一两个,也绝不扰客,伸手出去,给就要,不给就走,绝下纠缠不休。
其实,最要紧的还是要饭的不能惹,一旦惹了要饭的,做生意的生意就不要想做了,天天来一群,不用吵,不用闹,只往你门口一站就够了。
不吵、不闹、不犯王法,地方官府、衙门也无可奈何!
当然,酒楼、茶馆里的客人例外,客人敢惹要饭的,不过,酒楼、茶馆里的这种客人并不多。还是那句话,要饭的可怜,谁不同情?行好、行善也是为自己积德。
还有,饮酒、吃饭、喝茶是什么事?谁会在这时招惹不痛快?
只是,说酒楼、茶馆里的这种客人不多,并不是说绝对没有……
“陆羽居”进来个要饭的,是个年轻要饭的,十七、八,眉清目秀的,只是一脸脏,一身脏,一手端着个破碗,一手是打拘棒,进来就挨桌递出碗去,也不说话。
不用说话,谁都知道他要干什么?
这时候挨桌央求施舍,不也扰人听曲?
一桌又一桌,想给的给,不想给的不给,看也不看一眼,都没事儿。
到了那两个扎眼的那一桌了,碗刚递出去,一个眼一瞪,手一挥,叱喝:“去,滚一边儿去!”
碗飞起来,落了地,不但更破了,根本就碎了,前面几桌有客人给的几枚制钱也落了地,到处滚,有的还看得见,有的不见了。
年轻要饭的怔住了。
满座的茶客也怔住了。
唱曲的也停住了!
那一个,脸上现了凶相,两眼也露了凶光,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娘的,瞎了眼的脏东西,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跑来扰大爷听曲!”
抡起大巴掌来就掴!
这一巴掌要是掴中,年轻要饭的准惨。
距离近,出手快,没有掴不中的道理。
还好,理虽如此,事却不然……
年轻要饭的被人及时拉开了,这一巴掌落了空。
拉开年轻要饭的人是关山月,他先一句:“小兄弟这儿来。”拉开了年轻要饭的之后,他向年轻要饭的道:“我给。”他抬手递出了一块碎银,又道:“这够你吃几天了,也再买个碗吧!”
年轻要饭的两眼都瞪圆了,没伸手接。
大半是从没人给过这么多,不敢接。
关山月拉过他的手,把碎银塞进了他手中,道:“拿着,去吧!”
年轻要饭的一躬身,转身去急急忙忙的捡起了地上几枚看得见的制钱,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没事了,关山月要回座去,刚要迈步。
“站住!”一个冷怒暍声响起。
不用想都知道这是谁。
关山月收势停住,回身望那一个:“叫我?”
那一个脸上的凶相,两眼的凶光增多了三分:“废话!”
关山月没在意:“有事儿?”
那一个道:“当然有事儿!”
关山月道:“什么事儿?”
那一个道:“我要问问你,多管什么闲事!”
关山月道:“就是这事么?”
那一个道:“就是这事。”
关山月道:“我只是把那位小兄弟拉过来,给了他一块碎银,算是管闲事么?”
郡一个道:“当然算,他扰我听曲,我打他,你为什么把他拉开?”
关山月道:“你打人倒有个理了,我没有怪你,你倒怪起我来了,一个要饭的,怪可怜的,你不施舍也就算了,凭什么打人?”
关山月说的是理,但没人说话。
那一个道:“他扰我听曲,该打,我就要打他,就算他没有扰我听曲,我想打就打,关你什么事?你管得着么?”
那一个显然不讲理,可也没人说话。
是不愿管闲事,还是怕事?
关山月道:“我不能让你随便打人,不只是你,任何人都…样;只要随便打人,就关我的事,我就管得着!”
那一个冷怒而笑:“你不是本地人吧?”
关山月道:“不是。”
那一个道:“别管别人了,管你自己吧!”
依样画葫芦,也是抡起巴掌就掴。
关山月一把抓住了他的腕脉:“别打别人了,打你自己吧!”
抓着腕脉就往那一个的脸上送。
那一个还真听话,“叭!”地一声,自己的巴掌住自己脸上掴了一下。
“哄!”地一声,有人笑了,笑的人还不少。
另一个脸上变色,霍地站起:“你找死!”
他要动。
关山月手一扬,松开。
那一个给了另一个一个反巴掌,打得另一个砰然又坐了下去,差点没把鼻子打出血来。
又是“哄!”地一声,笑的人更多了。
刚才不是没人说话么,如今怎么有人笑了?
恐怕是忍不住。
或许是从没受过这个,那两个气得“哇!”“哇!”怪叫,另…个又猛然站起,跟那一个一起要动。
关山月抬手拦住:“别在这儿扰人喝茶、听曲,坏了人家的东西也得赔,外头去!”
他转身要往外走。
那两个可不管这个,各自抄起凳子来,向着关山月就砸。
许是关山月一句“坏了人家的东西得赔”,提醒了他俩。
他俩一砸关山月后脑,一砸关山月后背;后脑也好,后背也好,算起来都是要害。凳子那么硬,力又那么大,只一砸中,脑袋开花,脊梁骨断折,不死恐怕也差不多了。
距离这么近,眼看……
没人笑了,有人叫了,惊了。
哪能不惊叫?谁看见谁都会惊叫。
而关山月脑袋后头像长了眼,就在惊叫声刚起的时候,他已经转回了身,双手并出,各抓一个,两把凳子入了他的手,那两个的砸势停住了,硬是砸下下去了!
惊叫声没了,变成了惊叹!
那两个,急沉腕,掹力扯。
这是必然的反应。
那两把凳子在关山月手里像生了根似的,也像嵌进了整块的钢铁里,一动也不动。
又有人惊叹了。
也难怪,满座的茶客恐怕从来没见过这个,开了眼了!
那两个真机灵,一起松开了凳子,一起抬手撑腰。
关山月说了话:“在这里,你俩谁敢再动谁倒霉,不信试试。”
那两个或许都信了,手是已经到了腰际,但是谁都没再动。
不只是机灵,知机,识时务。
关山月又转了身,过去住自己桌上丢下了茶资,走了出去。
他不打算再回来喝茶、听曲了。
本来嘛,经过这么一闹,虽然没真打起来,恐怕暂时没人能再坐在这儿喝茶,听曲了。
只是,他前脚刚出“陆羽居”,后脚跟出刚才那名伙计:“客倌不用出去等了,那两位客倌已经从后头走了。”
也称那两个为“客倌”,而且用的是个“定”字。
谁都不得罪。
做的是生意,客人都是主顾,都是衣食父母,犯不着!
倘若那两个是本地耍横狠狈的,更犯不着了,也不敢!
这,关山月是头一回碰上,江湖上也不多见。
那两个,真是知进退,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只是,如果是地面上的一号人物,住后还能混么?
许是知道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的身子骨跟命才是真的。
关山月什么都没说,微一笑,转身要走。
只听伙计道:“客倌不进去喝茶听曲了?”
关山月回身一句:“不了,改天再来!”
走了。
伙计站在“陆羽居”门口发怔。
这样的客人,“陆羽居”一定盼望多坐,常来。
关山月是认为没必要在“陆羽居”坐下去了,他本来就认为很快就会有人盯上他,很快就会有动静;如今经过“陆羽居”这一闹,他认为会更快有人盯上他,会更快有动静。
他出了“陆羽居”就拐进了旁边一条小巷子里,他认为在这小巷里比较容易有动静。
他还真料对了,进巷子没多远,他就听见有人盯上他了。
盯他的人从他背后来。
关山月拐进了另一条小巷子。
盯他的人急急跟进来。
关山月拦住了他,但是关山月为之一怔。
站在他眼前的,是个年轻花子,就是刚才“陆羽居”里那个年轻要饭的。
年轻要饭的说了话:“尊驾请不要误会,我是来谢尊驾的,谢尊驾援手,谢尊驾周济!”
抱拳躬身。
听说话,不像一般要饭的;看举止,也不像一般要饭的。
关山月道:“小兄弟恐怕是‘丐帮’弟兄。”
师父跟他说过丐帮。
年轻要饭的肃然道:“不错,打狗棍棒行万里,鹑衣破碗吃八方。”
关山月道:“小兄弟既是‘丐帮’弟兄,适才在‘陆羽居’,恐怕是我多事了。”
年轻要饭的道:“我承认接近那两个是有目的,不过,坏事的是那两个凶残成性,跟尊驾无关。”
关山月道:“果真如此,我就放心了,举手之劳,也不敢当小兄弟一个谢字。”
年轻要饭的道:“尊驾从外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