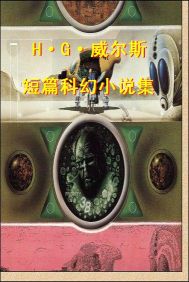乔治·法莱蒂-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点吗?你难道没有想过正好可以通过帮助别人来帮助你自己吗?帮助你自己找回自我?”
弗兰克以无家可归,失魂落魄的眼神看了看朋友。
“不。”他机械地吐出了个单音节词,这像堵墙横亘在他俩当中。有那么一会儿,两人都没有说话。他们俩都知道那个故事,对结局却都茫茫然。
敲门响起,摩莱利不等应答便走了进来。
“总监大人……”
“摩莱利,什么事?”
“有个蒙特卡洛广播电台来的人要找您。”
“告诉他我现在不接见记者。过会儿等头头定个时间,会开个记者招待会。”
“他不是记者,总监……他是个晚间节目主持人。他们的电台经理也来了。他们看了报纸,据说有点关于港口那两个受害者的消息要报告。”
于勒迟疑着。任何有用的线索都是天赐宝藏。只是他担心总有不少疯子自以为知道所有关于谋杀的情况,甚至愿意承认他们本人就是凶手。不过,现在任何机会都不容错过。
“带他们进来。”
摩莱利走出门,弗兰克像收到事先安排好的信号一样,顿时站起来走向门口。他正要开门,门就打开了,摩莱利又走了进来,带来两个人,一个是名30岁左右,留着黑色长发的年轻人,另一个男人年纪大些,大约45岁。弗兰克看了看他们,侧身让他们走过,顺势从半开的门中溜出去。
“弗兰克,”尼古拉斯·于勒叫住他,“你确定不想听听吗?”
弗兰克·奥塔伯一言不发地走出房间,随手带上门。
9
弗兰克离开保安局,向左拐上苏弗瑞·雷蒙得路,又走上阿尔贝特一世大道,这是一条沿海滩而建的公路。蓝天中有个起重机懒洋洋地工作着。人们还在忙碌着拆除比赛台,将它们装上卡车。
周围一切都有条不紊。他穿过大道,走到港口前的散步区看船只抛锚。码头上发生的事故已经毫无痕迹。贝内特船已被拖走,想必停到了什么安全的地方,以便警察随时调查。“巴里亚图号”和其他被撞到的船仍停泊在原处,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似的漂浮在水面,它们被波浪簇拥着,互相轻轻撞着护舷索。障碍物已被拆除。看起来一切正常。
港口酒吧恢复了寻常的热闹。这场事故可能引来了更多顾客,百无聊赖的人都喜欢赶到事故现场凑热闹。也许发现尸体的那名年轻水手也在,在众人簇拥下,一遍遍重复故事。也没准他正一声不吭坐在一杯酒前,试图忘掉噩梦。
弗兰克坐在一只石凳上。一个男孩正飞速溜冰,身后还追着名小女孩,她的溜冰鞋可能坏了,正呜咽着央求男孩停下。一个牵着黑色拉布拉多犬的男人耐心十足地等狗方便完毕。他掏出一只塑料口袋和一把小铲子,把狗粪收拾起来,好丢到垃圾箱里。
普通人。像许多别人,像所有人一样生活的人,比别人多一点点钱或者多一些幸福,或者自以为能比别人更容易得到它们。或许一切只是演戏而已。就算是金子做的,囚笼终归是囚笼,每个人都是自身命运的炮制者。所有人都依据自己制定或者拒绝制定的规则,构筑自己的生活或者毁灭它。谁都无法逃脱。
一艘船驶出港口,一名穿蓝色游泳衣的金发女人站在甲板上朝岸上什么人挥手。朦胧中,同样的海水,同样的倒影,回忆交叠现实。
※ ※ ※ ※ ※ ※
他出院后,和哈瑞娅特在佐治亚海岸租了幢小屋。一幢建在沙丘当中的木头房子,倾斜的红瓦屋顶,距海边大约100码。它还有个走廊,装了巨大的玻璃滑门,夏天把门打开,就成了个阳台。
夜里,他们听着刮过稀疏树林的风声和海浪拍击海滩的声音。他们躺在床上,他感觉到妻子睡着前紧紧搂住他,仿佛她需要反复确定他的存在,仿佛她几乎不能相信他真的活着,就在她身边。
白天,他们躺在沙滩上,游游泳,晒晒日光浴。海滩空无一人。喜欢热闹的游客不会选择这里,而是纷纷赶到那些时髦海滩,欣赏仿佛要参加《救生员》美国流行电视剧,演员多为身材性感的俊男靓女。试镜似的肌肉俊男和丰满美女们。弗兰克躺在毛巾上,可以尽情露出消瘦的身体,不必羞愧有人看见他满身的红色伤痕和他们在他的心脏附近做手术,取出那块差点要了他命的弹片后留下的可怕伤痕。
有时候哈瑞娅特躺在他身边,用手指沿着伤疤上敏感的皮肤划着,泪水涌上双眼。有时候他们不说话,两人默默想着同样的事情,回忆过去几个月的痛苦以及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这种时候,他们没有勇气看对方的眼睛。他们各自将脸转向大海,直到其中一个人找到力量,默默拥抱另一个人。
时不时地,他们到奥涅斯特买些东西。这是离他们最近的渔村,这里看起来不像是在美国,倒更像苏格兰什么地方。这个宁静的小镇没有任何成为旅游点的奢望。木制的房子看起来全都一个样,都沿着一条与大海平行的街道修建,岩石上建着一道水泥堤坝,冬天它阻挡着暴风雨掀起的海浪。
他们在码头对面一家有大玻璃窗的饭店吃饭。饭店修建在混凝土桩子上,铺木头地板,侍者走过时脚步发出咚咚回音。他们啜冰凉的白葡萄酒,玻璃杯冰得起雾,还吃新捕的龙虾,敲开钳子时,他们把手指都弄脏了,汁水溅上衣服。他们经常像孩子一样发笑。哈瑞娅特看起来无忧无虑,弗兰克也一样。他们什么都不谈,直到接到那个电话。
他们当时都在小屋里,弗兰克正在切做色拉用的蔬菜。烤箱里飘出烤鱼和土豆的香味。屋外大风卷起沙丘上的沙子,大海覆盖着白色泡沫。几个冲浪者孤零零的船帆轻盈地穿过风浪,朝向海滩上停驻的一辆巨大吉普车驶去。哈瑞娅特呆在阳台上,呼啸的风声使她没有听到电话铃响。他把头探出厨房门,手里还抓着个红色大辣椒。
“电话,哈瑞娅特。你接一下好吗?我的手脏。”
妻子赶过来拿起正响着古老铃声的老式挂壁电话。她凑近听筒,他站在旁边看着她。
“你好?”
听到对方的声音,她脸色一变,好像听到的是噩耗。她的笑容消失,沉默地呆立了一会儿。她放下听筒,哀切地看着弗兰克。这个表情日后在他的回忆中反复出现,折磨着他。
“找你的,是霍姆。”她告诉他,然后转身默默地回到阳台。他拾起听筒,上面还有妻子手握过的温暖。
“是我。”
“弗兰克,我是霍姆·伍兹。你怎样啦?”
“很好。”
“真的?”
“没错儿。”
“我们抓住他们了,”霍姆好像10分钟前才刚刚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般突兀地说道。他假装没有注意到弗兰克寡言少语的回答方式。
“谁?”
“拉金一伙。我们这次逮他们个正着。没再碰上什么炸药。进行了场枪战,杰夫·拉金被击毙。发现了一堆毒品,一大堆钱。还有不少重要文件。我们取得了巨大突破。再有点运气的话,准能找到足够的材料,把更大的组织连窝端掉。”
“好啊。”他像先前那样机械地回答,不过老板还是不加理会。他想象霍姆·伍兹坐在木头包壁的办公室里,手抓电话,金边眼镜后的蓝眼睛像他的灰色西装蓝衬衫一样一成不变。
“弗兰克,我们能够端掉拉金的老巢,全亏了你的努力。你和库柏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所以我特地来告诉你一声。你什么时候回来?”
“说实话,我不知道。快了吧。”
“好,我不想给你压力。不过记住我说的话。”
“好的,霍姆。谢了!”他挂断电话,走去找哈瑞娅特。她坐在阳台上看那两个孩子拆开冲浪板,把它们装上吉普车。
他默默坐到她身边的木凳上。有那么一会儿,他们默默看着海滩,直到孩子们离开,仿佛这些毫不相干的场景可以帮助他们避免交谈。
“他问你什么时候回去,是吗?”哈瑞娅特打破沉默。
“是的。”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谎言,弗兰克决意对她坦言。
“你想回去吗?”
“哈瑞娅特,”弗兰克回答,“我是一名警察。”他转向她,但她刻意回避了目光。于是他也转过头看着大海,以及海风中互相追逐,白沫四溅的波浪。“我选择这个职业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因为我喜欢它。我总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适应别的生活方式。我甚至根本不知道怎样改变。我祖父一直说,你不能把方楔子打进圆洞。”他站起身,搂住妻子有点僵硬的肩膀,“哈瑞娅特,我不知道我是方形还是圆形。但我知道自己不想改变。”
他回到房中,等他再次出去找她,她已经不见了。她在房子前的沙滩上留下一排脚印,通向沙丘方向。他看到她往前方海边走去,只剩一个小小的影子,头发在风中飞扬。他用目光跟随着她,看到她又走过两个沙丘,消失在视线里。他想,她可能希望一个人独处一阵子,也许这样更好。他回到房里,在桌边坐下,面对一桌佳肴食欲全无。
突然之间,他对自己说过的话有点恍惚。或许他们俩可以选择别的生活方式亦未可知。也许生来是方形的人确实不能变成圆的,但至少可以把四角磨圆一点,免得伤害别人,尤其是他爱的人。他决定思考一晚上,明天早上再和她谈谈。他们一定会一起找出一个解决方法。
他们俩再也没有过什么明天早上。
下午很迟时候,哈瑞娅特还是没有回来。夕阳中沙丘的影子像深色手指,在海滩上越拖越长。他看到两个人影慢慢沿海岸走来。他眯缝起眼睛,试图在刺眼的落日光线中看清他们,但是他们还太远。不过他能看到他们的脚印,像一道轨迹一般,从地平线那头的沙丘蜿蜒而出。他们的衣服在海风中劈啪作响,身影发着微光,仿佛是从远方柏油马路的尘雾中钻出来的。他们渐渐走近,弗兰克认出他们中一个是奥涅斯特的治安官。
他觉得体内升起一股不祥预感。那个看起来更像会计而不是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