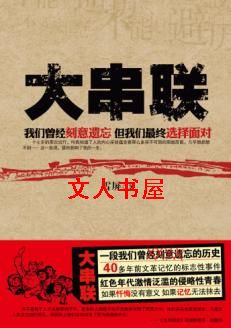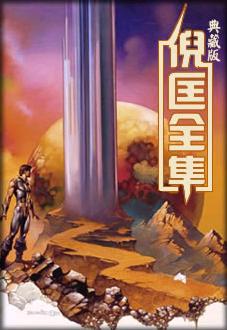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还有什么比孕育一个新生命更神圣更伟大呢!
孙卫红肚子里的小崽子动静大了起来,它像个便秘的妇人,把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小腹部,轻声呻吟,咬牙切齿,约摸两炷香或三炷香工夫,一个湿漉漉的小猴崽呱呱坠地了。孙卫红把臀部移到早就准备好的鸡血藤上,磨蹭一会儿,又坐了一会儿,撕裂的伤口不痛了,血流如注的荫部也止了血。孙卫红这才有了气力,把小老鼠一样的小崽子抱起来,咬断了脐带,吞食了胎盘,一下一下舔着小崽子身上的羊水,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小崽子的小眼睛还没睁开呢,就急慌慌地钻进母亲怀里讨食了。孙卫红把早就胀鼓鼓的Ru房递了过去。霎时,奶汁如注,小猴崽咕嘟咕嘟的吮吸声,像敲鼓一样在小岩洞里滚动。这是孙卫红有生以来听到的最为动听的音乐。
身个只有人类一半高的金丝猴,幼儿发育的速度却比人类快得多。孙卫红的小猴崽三天就能下地走路,十天就敢出洞戏耍,一个多月,孙卫红就把它扶上枝头,强迫它在低空晃晃悠悠荡秋千。就是这一天,从孙卫红身边走过的老猴王,猛一回头,看见孙卫红身边有个小猴崽,浑身金灿灿的细毛,两个圆溜溜的眼睛,小尾巴在屁股蛋上卷起个小圆圈,真是可爱极了。老猴王一喜,走了过去,吸溜着鼻子在小猴崽身上嗅了嗅。
孙卫红唧唧叫着,用猴语告诉老猴王,这就是你的小崽子呀!
老猴王也唧唧叫着,用同样的猴语自我陶醉地回答,哦,看这小家伙多像我!
老猴王把小猴崽抱在怀里,在草地上翻跟斗,上树杈荡秋千。又采了许多果子给它吃,还搂在怀里美美地睡了一觉。老猴王也不知是第几十次或者第几百次做父亲了,然而,叫它最快活最激动的,是这一次。因为这只小猴崽是老猴王和孙卫红的优化结晶,是花果山上最漂亮的一只金丝猴崽。
蓝雪梅接到她哥一封信,说她妈出了工伤事故。事故不算大,而伤残却是致命的。她妈跟她爸一起在上海港当搬运工,有天扛一袋日本进口尿素,两百多斤重,也不等其他工友帮忙,她独自逞能,颤颤巍巍地从架在大货车上的搭板往下走,有那么三五步就要着地了,她却支撑不住,腿一软,腰一闪,摔了下来。既不见出血,也不见青肿,可她的腰怎么也直不起来了。比雪梅大十来岁还没成家的哥哥,用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在从雪梅当年的作文本上撕下的格子纸上写道:
“……妈已今(经)睡(卧)床半个月,吃、黑(喝)、拉、杀(撒)都不能自里(理)。开初,我和阿爸还指望妈能很快好起来,没想到她这一睡(躺)再也下不了床。我和爸用板车把妈推到医院一检查,拍了个(X光)片子,大夫就说妈的子追(脊椎)神金(经)断了,没治了,成了个费(废)人了。……”
雪梅阿哥的字迹歪歪扭扭,缩成一团,一笔一画都传达着揪心的痛苦。雪梅读着读着,眼泪扑簌簌滚落,视线便一片模糊。但是,她哥哥带哭的声音继续从远方传来:
“……雪梅,现在阿拉家真是太困难了!妈整天睡(躺)在床上,白天我和阿爸都得去海港上班,妈就没人管了。晚上阿拉回家,得忙着做饭,给妈擦实(屎)换库(裤)子,喂汤喂饭,被六(褥)天天被妈尿湿,来不及换洗,爸只好天天在床上铺三重旧报纸……妹妹,侬快快申请回上海吧,阿拉家眼看要家破人完(亡)了!……”
雪梅一阵眩晕,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人家都把父亲比做天,把母亲比做地。可是雪梅知道她家母亲绝对比父亲更重要。父亲干完活,回到家,除了吃饭睡觉,再跟左邻右舍杀两盘棋,他就没有多少家务好干了。母亲除了做工,还包揽了全部家务,烧菜做饭,洗洗刷刷,缝缝补补,用那双粗大勤劳的手,撑起一个穷困的家。现在怎么办?母亲什么活也不能做了,还要父亲哥哥端屎倒尿。雪梅是家里惟一的女孩子,却发落在远隔千里的枫树坪!
张亮和希声知道雪梅家里出了事,也都急坏了,陪着雪梅叹气掉泪。张亮、希声和雪梅住在一条弄堂里,从小认识雪梅母亲。那是一位多么善良、勤快的大妈呀!
“文革”前有一阵子“学雷锋”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张亮和希声的表现也都很自觉。雪梅妈每回拉着一板车煤球从弄堂里走过的时候,张亮和希声都会立马赶上去,助一臂之力,帮着大妈把那辆沉重的板车推回家。张亮和希声家里受到冲击,父母都进了“牛棚”,雪梅把张亮和希声领回家,总能吃上一顿热饭,睡上一宿好觉,领受那个年代人间少有的温暖。
第九章 告别伤心地(2)
张亮说:“雪梅,你还发愣干啥?把你哥的信递上去,快快申请招工返城呀!”
“这、这……”雪梅觉得这事很难开口。她是上海知青队队长,刚下来的时候,当“扎根派”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后来看到不少知青招工招干走了,她虽然也想回城,还从未向组织说过要走的话。
希声也说:“雪梅,你把信给我,我去找春山爷!”
吴希声是大队会计,跟春山爷的关系非同一般。张亮也觉得这个主意不坏,催着雪梅快把家信交给希声。
雪梅抹着眼泪说:“我这一走,我们上海知青队就散伙了。”
张亮横眉立眼道:“嘿,都到这个地步了,还顾得了上海知青队?你还相信‘扎根农村,战天斗地’那一套?”
雪梅不说话了。事已至此,眼前只有这条路。
吴希声把蓝雪梅的家信交给春山爷,说了说情况,春山爷非常同情,满口答应了。但他说招工的事由公社掌握,大队没有指标,但有权推荐,他会立马向公社报告。
第二天,蓝雪梅这封沾满泪痕的家信,已经摊在刘福田的办公桌上。刘福田心里一动,引起高度重视,嗯,蓝雪梅家这么困难,又是我们的阶级姐妹,当然要关心的。我手头正好有个上海国棉厂的招工指标。但招工招干这类事十分敏感,必要的过场总是要走一走的,公社研究研究就马上办。春山爷很是感动,说刘主任,太谢谢你了,请你千万抓紧吧!唉,雪梅她妈躺在床上半死不活哩!刘福田说,放心,这事我比你更着急!
第三天,刘福田立即从公社赶回枫树坪,召集全大队知青开会。那个年代,农村七会八会多的是,知青们能躲则躲,能溜则溜,惟有涉及招工招干的会,都是每会必到,到必坐得整整齐齐,支棱起耳朵听得非常认真的。
刘福田讲了一通全国形势大好之后,才说到那一个招工名额。接着,交待了选拔程序:个人申请,大队推荐,公社审批,等等。最后,又要求大家发扬风格,去者高兴,留者安心,做工务农都是一样干革命么!
散会后,知青们懒懒散散、三三两两地走了,谁都不愿说话,情绪十分沮丧。等啊等啊,等来一个招工名额,摊在二十多人头上,能轮到谁呢?但是,毕竟有了二十几分之一的机会啊,谁心里不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人人都把这种内心的渴望掩饰着,知青楼的气氛还是显得异常沉重而紧张了。
从1969年春天下来插队,一晃,快过去八个年头。当年他们在知青楼前栽下的一排枫树苗,如今已长成撑天大树,难怪那些学生哥和学生妹要长成壮小伙大姑娘,而且也该谈婚论嫁、成家立业了,真让远方的父母愁白了头呀!因此,即使是百分之一的机会,知青们都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免费电子书下载
一回宿舍,上海知青队三个人就关起门来筹划这件事。
张亮问道:“希声,春山爷那边你都疏通好了?”
希声说:“春山爷二话没说,一定会推荐雪梅的。”
一向总是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蓝雪梅,这回好像是占了大家的便宜似的,心里还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雪梅说:“唉,这怎么好呀?要说困难,你们家也有困难。”
张亮不满地盯着雪梅:“看你看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我们忍心跟你抢这个名额吗?”
希声也掏心掏肺说:“雪梅,你别再谦让了!你妈卧床不起,没有你在身边,日子怎么过?不过张亮,有句话我可得说在前头:你们俩是一对儿,让雪梅先走,是你们俩都同意的,日后可不要说我拆散你们呀!”
张亮说:“你怎么这样啰嗦?走一个算一个,总不能大家都憋死在枫树坪呀!”
“张亮,我在上海等你,一辈子等你!”雪梅心里很难过,说话的声音都发颤了。停了会儿,又把脸转向吴希声,“咳,希声,就是委屈了你!以后你回到上海,我说什么都要给你找个好对象,我有好几个女同学至今还没有主。”
“嘿,回上海,找对象?”希声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这辈子我什么都不敢想了!惟一的愿望,是祈求你们活得比我好!”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都动了感情,六只清澈明净的眼睛里,早就泪水盈盈。
最后,他们又想到一些细节,比如走后门送礼,那是必不可少的。雪梅开头还有些犹豫,说刘福田凶是凶点,人还是正派的,万一碰一鼻子灰,反而把事情弄砸了。张亮就不屑地皱皱鼻子,哼,哼,正派?正派个屌!他就那么三十多块工资,你们没看见他天天抽好烟,那都是“伸手牌”,自己从来不掏腰包。希声也说,如今办个屁大的事,领导都说“研究研究”(烟酒烟酒),没烟没酒,不送点礼,谁会给你研究。雪梅也就同意了,倾其所有,把一点积蓄掏出来,张亮和吴希声也帮衬点钱,买了两条“前门”烟、一瓶“四特”酒,由蓝雪梅拎着去大队部找刘福田。
刘福田正在开会,特意溜出会场见了蓝雪梅。他满脸堆笑,一副特平易近人的表情,问道,找我有事?雪梅头一回为自己的事来麻烦领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