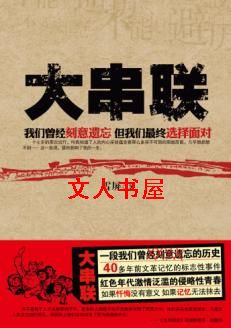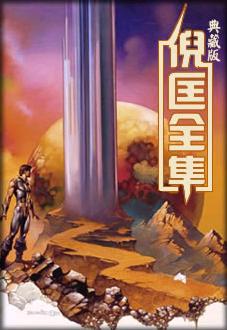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小子等着吧,我一定请你喝喜酒!”
“我就盼着这一天!”希声双眼放光,一腔真诚,把一只胳膊搭在张亮的肩膀上,无比深情而向往地说道,“到时候,我就给你们当个证婚人吧!”
两人歇够了,也谈够了,这才提起柴刀、扛上钎担上山去砍樵。
第三章 偷尝禁果(7)
又过了些天,吴希声却突然向雪梅和张亮提出“分家”。起因不光是发现他们在一起睡觉,更主要的,是他在无意中看到伙房后头的垃圾篓子里的鸡蛋壳,却好久吃不到一粒鸡蛋。上海知青队多年来实行乌托邦式的“共产”原则,即使只剩下雪梅、张亮和希声三人,也是在一口锅灶里开伙吃饭。张亮个大饭量大,可他挣的工分也多;希声体弱吃得少,他的工分收入也少。雪梅的劳力和消耗都属中等。也就是说,他们的劳与酬,大体扯平。在某件小事上,谁吃点亏,谁占点便宜,那也无关紧要,因为多年同窗,特别是“文革”中结成的友谊,足够把他们之间的不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吴希声甚至觉得,在枫树坪的日子虽然苦一点,但他与张亮、雪梅三人姐弟哥们式的情谊,一辈子都值得回味。就说养鸡吃蛋吧,好当家雪梅姐饲养着一窝老母鸡,竞相下蛋,好长日子,他们每人每天都能吃到一粒鸡蛋。前些日子,四只老母鸡被黄鼠狼叼走三只,雪梅伤心不已,叫张亮在鸡橱边装机关设暗器,不杀黄鼠狼誓不罢休。可是狡猾的黄鼠狼并不上钩,雪梅也不敢多买几只母鸡来养。一只老母鸡下蛋就供不应求。雪梅把一粒鸡蛋打成蛋花花,煮成一锅汤,大家一视同仁都能沾点蛋腥味。可是现在,希声已经许久只见蛋壳却吃不到鸡蛋,原本就不大牢靠的“共产”原则,不能不在希声心里砉然坍塌。他想,中国许多大家族中的同胞手足,原来都相亲相爱,一旦娶了老婆,随即有枕边风、私房钱,没有不祸起萧墙,吵着闹着要分家的。雪梅和张亮虽然还没打结婚证,已经不避人耳目、卿卿我我地睡在一起了。按照人之常情,他们该有小两口的小日子,张亮一天独享一粒荷包蛋,也在情理之中,我吴希声掺和进去算个什么事?
这天希声下工回家又迟了点,他洗好脚,挂好锄,走进伙房见张亮和雪梅已经吃过饭,桌上留着一锅红薯饭,一碗苋菜汤,一碟萝卜干,就是不见荤腥,当然更没有煎蛋炖蛋或鸡蛋汤。
雪梅撩起围裙搓着手,尚未开口已是满脸歉意:“真对不起!那只老母鸡又抱窝了,老不下蛋。希声,你将就着对付一餐吧!”
“没事,没事,能填饱肚子就好哩!”希声不动声色,端起碗筷吃饭。其实,他进屋前,特意查看过搁在伙房后头的垃圾篓子,里头分明有个新鲜的鸡蛋壳,希声就心里不快,闷声不响地扒下两碗红薯饭。
雪梅忙着洗碗抹桌,张亮坐在灶头吸喇叭烟,烟屁股上的火光一闪一闪。吴希声发现,雪梅和张亮偶尔交换个目光,他们的眼神里有一种小夫妻的暧昧。希声觉得心里堵得慌,有点窒息感,作了两次深呼吸,才鼓足勇气开了口:“雪梅,张亮,你们都在这,我想说个事。”
希声的语气异常平静。也许正是平静得异常,雪梅和张亮都感到事态严重,四只耳朵嗖地支楞起来。怪了,他们的小弟弟、才二十出头的吴希声,还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平静的语气和严肃的表情说话的。
“你说,你说,希声!”雪梅在饭桌边坐了下来,朝张亮招了招手,“哎,你也过来吧!”
张亮也在桌边坐下:“嘿,到底有啥事体?快说快说!”
到了关键时刻,希声又心里犯难。他咽了口口水说:“唉,也没啥大事,没啥大事,不说了!不说了!”
雪梅却是一脸的关切:“是不是你爸他又病了?”
希声支支吾吾:“不,还好,还好。”
张亮急了,嗓门提高八度:“哦,我知道了:刘福田那小子又欺负你?”
“没,没。”吴希声连连摇头,“这阵子他倒没有找我的麻烦。”
雪梅抿嘴一笑:“我猜八成是跟秀秀闹别扭了!”
“没,没,没!”希声还是一个劲摇头。
“哎,到底是啥事体?”张亮霍地站起,一拍桌子吼起来,“你快快说呀!我就见不得你窝窝囊囊的!”
希声一下子被逼到悬崖上,退路是没有的,他咬咬牙,终于说出憋了多少天的一句话:“雪梅,张亮,我,我,我想跟你们分、分伙吃饭!”
“什么?什么?”雪梅和张亮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疑疑惑惑地盯着吴希声。
吴希声重复一遍,雪梅和张亮都听清了,马上都有些尴尬,交换一个会心的眼神,又佯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匆匆撇开脸。毫无疑问,事情的起因决不会仅仅是他们在一起困觉,他们同时都想到了鸡蛋的分配不公。可是,吴希声没有挑明,他们也只好装聋作哑。沉默一会儿,雪梅绕了个圈子问希声,你是不是嫌我没当好这个家?你吃不饱,吃不好?吃得不自由?希声一一予以否认。雪梅就瞪圆了眼睛,追问变成质问:“这就怪了!你为什么要闹分家?希声,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什么?”
希声有点茫然:“不就是自己做饭自己吃么,这能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我们上海知青队要彻底散伙了!”雪梅眼里泪花闪闪了,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年前,我们从上海来这里插队,一共是十个人,先先后后走了七个,留下我们三个,你还要分伙吃饭,上海知青队还存在不存在?”
“事情没这样严重吧。”希声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有些认同雪梅的看法了,就神情沮丧地埋下头,好像自己真成了破坏上海知青队的罪魁祸首。
第三章 偷尝禁果(8)
在雪梅看来,这事几乎关系知青队的生死存亡,便动了感情,又沉着脸启发道:“希声,你不会忘记吧,我们下来的时候,可是宣过誓的呀!”
吴希声想起来了,1969年春天,上海知青队成立的时候,他们十个特别要好的同学,挤在雪梅家那间阴暗的小客厅里,举起拳头,在毛主席像下庄严宣誓。雪梅用清脆的女高音念一句,九个童音未褪的中学生齐声跟一句:
“扎根农村,战天斗地!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好看的txt电子书
十个稚嫩的声音憋在白粉斑驳的土墙挤压中,像春雷一样滚来滚去,让他们耳膜震颤心头剧跳。后来;希声曾经琢磨过,这些口号和原则,有的来自当时舆论的灌输,有的似乎是受“桃园结义”和“梁山聚义”的影响。有一阵子,他奉为圭臬,身体力行,把自己家里寄来的一点钱和粮票都交给队里打平伙。但是不久,他就觉得这种活法像小孩子过家家,偶尔玩玩可以,时间长了就太不实际。五六个年头过去了,十个同学走了七个,蓝雪梅说,再不能一个一个走了,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有糖同甜,有盐同咸,谁如果自顾自,就是王八蛋!现在,雪梅和张亮俩睡到一个暖被窝里去了,他吴希声只能看到蛋壳却闻不到蛋腥味。他们信奉的“共产”原则还有多少实质内容呢?
然而,吴希声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如果那样,也叫姐们哥们太难堪太伤心了。憋了半天,他急中生智,终于想出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他这次回上海看望父亲,见父亲胃病严重,食堂的大锅饭吃不下,哥哥希文常常给父亲买些饼干、蛋糕,可他哥每月定量的粮票也只有二十八斤,做弟弟的他想尽量省下点粮票往家里寄。往后,他打算晴天吃干的,雨天喝稀的,干活吃三餐,挂锄吃两顿,如此这般,他就不能不自己开伙吃饭。
希声的表情和语气都十分沉重,雪梅和张亮相信这是他的一片孝心,便都劝说希声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苦了自己,粮票不够么,我们会给你凑的。三张嘴巴都少扒两口饭,总比你一个人勒紧裤带强吧!吴希声支支吾吾,敬谢不敏,雪梅和张亮交换个眼色,也就点头同意了。他们心里都有点虚,如今他们是同床共枕的一对儿,哪能死拉硬拽着吴希声一块过日子?
次日收工回家后,张亮把吴希声拉到饭桌前。桌上添了好几样荤菜:腌菜炖红烧肉、小鱼干炒笋干、泥鳅干煮芋头、鸡蛋炒蒜苗,还温了一壶客家米酒。虽然都是些土里叭唧的小菜,但在“文革”末期的枫树坪,也算得上相当丰盛的一桌便宴。
吴希声大为惊异:“咳,你们从哪里发了一笔洋财,敢这样铺张浪费!”
张亮笑笑:“我们马上要分家了,总得在一起吃一顿‘最后的晚餐’吧!”
“咄!看你这嘴有多臭啊!”雪梅骂过张亮,又朝希声解释道,“我们搭伙吃饭这么多年,我盘点盘点,还有点伙食尾子,就随便添几个小菜,大家乐他一乐吧!”
三人围桌而坐,雪梅不断给希声夹菜,张亮不断给希声斟酒。桌上的气氛可是空前未有的,希声惴惴然地问道:“咦,这是怎么了?还把我当客人吗?”
雪梅神色凝重地说:“你是什么客人呀?我们三个还是一个上海知青队,分伙不分家。希声,往后这桌上有啥好吃的,给你添一副碗筷就是了!”
“对对对!”张亮学着《 红灯记 》里李奶奶和李铁梅的台词说,“我们仨,拆了墙是一家,不拆墙还是一家!希声,往后你小子有什么难处就找我,我张亮要是敢皱一皱眉头,呸,我就是个王八蛋!”
张亮这话无意中骂到雪梅头上,雪梅就抡起筷子敲张亮的脑壳:“说你嘴臭,你还臭上加臭,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张亮也立时悟出那话不雅,臊得满脸通红。好在希声是个谦谦君子,从来不愿揭人之短,只一味赞叹雪梅做菜的手艺,把他们的尴尬掩饰过去。张亮又借机跟希声干了好几杯酒,两人都有些微醺了,额上汗津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