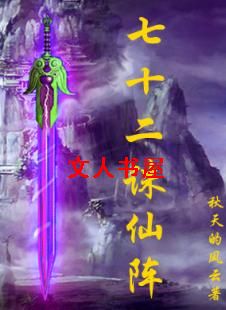七十七街安魂曲-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自己醉得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记这个倒记得清楚。”
我抬眼望着他:“莱尔,莱尔,坐下来,我善良的朋友。”
莱尔在我对面坐下,伸出手来握住我的一只手。昨天整晚他都在讥笑、嘲讽、玩世不恭地对我,而此时,我从他脸上读出了真诚的关注与担忧。“那么你是陷入困境了,孩子?打算怎么办?”
“你指哪个困境?是房子吗?是蚀本出售,还是硬撑着负担它?是我姐姐吗?是干脆让她死,还是把她强留在地狱的边缘?还有麦克吗?”我不得不移开目光,“噢,他妈的,我该拿他怎么办?”
“好了,这回我同意你用厨房里的菜刀,行了吧?”
“谢了。”我说。
“麦克昨晚打电话来了。”他站起来递给我从留言机上取下的记录。从周五晚8:53开始,记录依次如下:麦克说他爱我;女儿又要钱了;凯伦伯格说卡洛斯·奥利里要去人民公园;麦克说想念我;杰克·纽克斯特感到很绝望;兰娜·霍华德想要我在11点的新闻上讲一段话;爸妈打电话来再次强调他们支持我的决定,并且希望我周六回去吃晚饭。午夜时分,麦克又打电话来问我到底去哪儿了。
这会儿时间尚早,我觉得麦克还应该在家里,于是打电话给他,电话铃响到第三声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你好。”
我问:“麦克在吗?”心里希望她告诉我打错了。
“麦克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她说,“我会给他传个信。”
我说不必,谢谢了,心里乱作一团,居然没问她是谁就挂了电话。
她也许是迈克尔的朋友,也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我没把这事向莱尔提起。我用最后一口咖啡吞下两片阿司匹林,离开了屋子。
每个周六莱尔都自愿到卡斯特罗的疗养院去帮忙。我上楼洗澡,听见他在放军营乐队的歌曲。他还带了胡桃巧克力——莱尔说多吃是保持好身体的最好途径。
我及时下楼帮助他收拾了厨房。莱尔把东西收进被他擦洗得洁白无瑕的碗橱和抽屉里,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久久地留恋于那些杯盘餐具上,不舍得放下,好像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要永别了。
“先不要收拾你的行李,我还没要把房子卖掉呢。”我说。
他若有所思地笑了笑:“当我65岁的时候,你还会需要我吗?你还能养活我吗?”
“当然。”我是真心的,可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动摇了。我像爱我的亲人一样爱莱尔,自从那次地震以后,我们就像一家人似地住在一起。可是,当我们必须分道扬镳时,这种感情还能得以维系吗?麦克退休以后要搬到远离尘世的地方去,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在疗养院门口我让莱尔下了车,然后在网络的分支机构停了一下,给兰娜发了封信。我再次沿着海湾向东开去,脑袋还在隐隐作痛。
19
卡洛斯·奥利里熟练地把手里的银丝做成一个耳环圈,然后迅速地剪掉多余的部分。“我为什么要和你谈话?”问我的时候,他连看也没看我一眼。
“见鬼,卡洛斯,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话呢?”我坐在他旁边的草地上。这儿是伯克利商业中心的人民公园。它曾是平民百姓谈论、参与政治活动的地方,现在却成了那些无家可归者、生活漫无目的者的避难所;同时,它还是一个非法的毒品超级仓库。这里气味怪异,我一会儿也不想在这里多待。15分钟过去,他做好了一副耳环,我们之间却只进行了一些无聊的闲谈。太阳就在头顶上明晃晃地照着,我全身燥热,再也没有耐心等待卡洛斯告诉我一些有用的东西。
卡洛斯建议我再坐一会儿。我拒绝了,站起来说:“今天全国有一半的人想和我谈话,卡洛斯。如果你不想说什么,那么,我还是走吧。”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不要这么生气嘛!”他剪了一下耳环的接合处,把正在冒烟的烟蒂放在他的有水晶珠子项链的盘子里。他大约50岁,由于长期生活在户外,脸上饱经风霜,皱纹很深。他穿着紫色的衣服,戴着一串珠子项链,脚踏一双凉鞋。一脸大胡子使他看起来有些可怕,在伯克利之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被人看作是一个逃跑的疯子。
他眯起眼睛抵挡着太阳光,说:“也许我们有一个沟通的问题。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会想和一个像我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无业游民说话?”
“一个叫查克·凯伦伯格的人说你有可能知道一些共和军的信息。”
“凯伦伯格?”
“凯伦伯格。”我重复了一遍。
“噢,我认识他,联邦调查局的。”
“他说,也许你听过共和军说起枪战之前洛杉矶发生了什么。”
“谁?我吗?他一定是找错了人,我不是那个卡洛斯·奥利里。”
“也许是他错了吧。你看,与你谈话真是特别的有趣。但是现在我还有些别的事要干。”我站起来,把包挎在臂弯里,“再见。”
“不要气急败坏地走开,美丽的女士。”他拿起他刚做好的耳环——上面有着长长的水晶悬垂物,递给我,“把这送给你。让我把它们装好,这样它在你的手里也不会遭受散落的命运。”他用一张黄色的纸包好耳环,向上举着递给我:“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我把耳环放入包里,放了10美分在他的手里。
卡洛斯又捡起那还在缓慢燃烧的烟蒂,再次点燃,像以前那样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我走到人行道时,他正随着一种神秘的内心的交响乐而扭摆着身体,好像我根本就没出现过。
我说过,我在伯克利长大,我对这里很熟悉,卡洛斯·奥利里不是我获得信息的惟一渠道。在艾米莉住的医院外举行的游行,让我想起自己还认识那么多人。
我看见了我妈妈的朋友珀尔米特夫人,她正站在她家房子旁边阳光照耀的花园里栽种郁金香。只见她戴着一顶宽檐草帽,着一身斜纹粗棉布工装裤,跪在地上——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她卷卷的头发从帽子下面钻出来,太阳在她有皱纹的脸上留下一片温柔的、银色的阴影。
珀尔米特夫人的听力几年以前就开始减弱了。我拿出照相机,在离她大约10英尺远的地方跪下时,她显然没有听见我发出的声音。我已经给她拍了两张照片,她才感觉到我的存在,眼睛转向我。
“噢,玛吉,亲爱的,是你呀?”她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只是把几绺露出来的头发放回帽子中,“你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一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拍尔米特夫人。”当她正面对着镜头时,我把焦距又调了调,给她拍下了第三张照片。然后我把照相机收好,朝她走了过去,“你看起来很美丽。我会把照片寄给你的。”
她把一只手伸向我,紧紧地抓住我,逼迫我蹲在她旁边。然后她递给我一把铲子和一小桶骨粉:“我正想着你要路过就好了,你果真就来了,就像以前那些日子一样,还带着照相机呢。有一次,我还问你妈妈,是不是可以给我一张你上学时的照片,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我看见你所有的形象都是你在摄像机后面工作着。”
我笑了:“扛一台摄像机是我惟一的露面方法,现在仍然是。”
她微笑着抬头看我的脸:“亲爱的玛吉,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总是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吗?”我把一茶匙骨粉倒入她刚在有护根的泥地上挖的3英寸深的洞里。“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生命是一幅巨大的、没有成形的图画。没有人给我指路,我就在里面徘徊,永远在迷茫中前行。”
“那些年,我觉得你是少数几个精于计算的人。”她温柔地笑着,递给我一根郁金香茎,“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宝贝?”
“共和军。”
“太可怕了。”她装作惊慌失措地举起了双手,“有很多年没有想起过那群暴徒了。他们是你的新项目吗?”
“算其中的一部分吧。”
“为了讨好你,我想我得帮你点忙。但是怎么帮呢?”
“你知道一些事情。”我又栽好一棵郁金香,“在洛杉矶枪战之后,共和军在伯克利又有过短暂的复兴。”
“短暂而且激烈。”她肯定地说,“他们在整个城市画画、写字,‘那些剥夺人民生命的法西斯分子去死吧!’不是原汁原味的,是吗?”
“你知道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住在哪儿吗?能找个人和我谈谈吗?”
“我想那些还在监狱里待着的人是很容易找到的。至于他们想不想与你谈话,则另当别论。贾奇·盖茨也许能帮你。”她正了正帽子,“你还记得那个盖茨吗?在中风前,他是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
“贾奇·盖茨怎么样了?”我问道。
她苦思冥想着,思维都早已越过了贾奇·盖茨,然后说:“还有萨拉·简。”
“萨拉·简·穆尔?”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个名字,“她向福特总统开枪了?”
“你有一个好的记性,就像你的妈妈一样。”她说,“你应该和萨拉·简谈谈。我相信她仍然在狱中的某个地方。在赎身谈判中,她是海斯特家族和共和军的联络人。我想她是一个簿记员,曾经留在海斯特身边做过一段时间文书工作。她不仅是留在伯克利的共和军的密友,还是联邦调查局的成员和给警察局提供情报的人。”
“我曾听你说起过阿普里尔·富尔吗?”
“没有。真的。和萨拉·简谈谈吧。”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
“这里的人都知道她。她会和我们一起参加‘又一个争取和平的母亲’的游行示威活动的。”她说,“她有一大笔继承得来的钱。我想这就是共和军为什么想和她交往的惟一原因。这个女人为芭蒂·海斯特牵肠挂肚,总是打电话到她家里,企图通过谈判释放她。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说。也许她有一种英雄情结,我不知道。她是那么想救出芭蒂,就在联邦调查局逮捕芭蒂几天后,她就疯了,她企图枪杀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