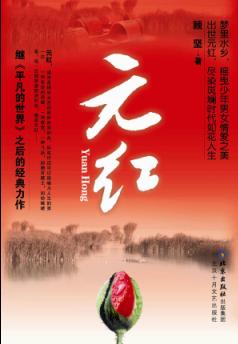元红-第10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存扣略带歉意地说:“忙啊,穷忙。做生意就像坐牢,沾上了就没得自由了。就是回来,也是来去匆匆。”
“是呀,生意是条牛绳,拴上了就不好走。”保国指着窝棚后的水面说,“你看,这十亩蟹塘就把我陷在这块了。”
“收入还可以?”存扣问。
“一年几万块钱吧。”保国轻描淡写地说。
“你老哥神哩,做什么都灵光。难怪人家城里人现在羡慕农村。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下岗工人啊,一个月拿百十多块钱生活费,管嘴都难,可怜哩!”
保国说,他要趁不老,趁能动,多攒点钱留给儿子学兵。
……
存扣离开牯牛湾时,朝东北方向看了一阵,看那里树木葱绿的一块地方,有大鸟在上头盘旋。那是秀平歇息的地方。存扣眼前又迷蒙了,他喃喃地说:“姐姐,明天我去看你,今天来不及了哩……”
存扣说来不及去看秀平;是因为他要回去划纸。中饭时他对哥嫂说了;要到秀平坟上烧纸的。月红说:“路远啊,你弄捆纸到河边上烧烧吧,朝东北方向喊秀平的名字就行了。”存扣说不行,要亲自去的。他说:“我要去哭一哭。”存根说明天起早陪他去。存扣说:“不要,你去了我哭不出来。”
存扣从田里回来后,便去杂货店拎来一捆上好的毛苍纸,先用红色百元大钞在最上面按了又按,便以此确定了每张纸钱的最大价格,然后就慢慢划,足足划了两个多小时。一捆纸蓬开来,竟是原来体积的十数倍之多,不得不用月红嫂装棉花特制的大蛇皮袋把它们装进去。存扣试着把这庞大得夸张的口袋背在肩上试试,有一种很踏实很富足的感觉。想到明天秀平就会收到这“几十万块钱”,他心里高兴得很。
《盐城》第一章6(1)
晚饭,存根把福生和玩得好的几个人请到家里来陪存扣。是在“国权酒楼”订的菜,老板娘亲自把盒担挑过来,小扁担挑得“嘎吱嘎吱”的。蹲下来,从一层层的红漆盒子里往外拿菜,很有点变魔术的意思,把八仙桌上变得满满的。毕竟是酒楼里大师傅做出来的,无论冷盘热菜,都弄得很讲究,那喷喷的香,腾腾的热,让你忍不住咽唾沫,急急就想吃。
“钱真是个好东西,来人到客不要动手烦神,坐在家里电话拨拨,就有人替你把桌子布置得好好的。”福生笑着说。
几个人喝得不少,说得也不少。
存扣说今天打东桥上走,看到半条河都纠缠着水花生老藤,水边上浮着玻璃瓶儿,塑料瓶儿,方便袋子,还有棒棒棍棍的,还有死鱼,真是脏死了;说春上河水应该是碧清的呀,怎么把个河搞成这样?
福生说有什么办法NFDAB,污染大呀。现在种田老早就不用绿肥了,不划水草不罱河泥,河泥越积越厚;从前在大集体时,家家草不够烧,脱粒后的草粉子(草屑)都当个至宝,现在人变“修”了,烧(煤)炭,烧电,烧煤气灶,收割后那些黄灿灿干焦焦的好稻草好麦草就在大田里放火烧,或干脆就推进河里。河床本来就越来越浅了,弄得行船都困难,有的河沤得黑咕隆咚的,篙子插下去臭水直冒,拔都拔不上来。现在人又不如从前自觉了,垃圾往河里瞎倒,杂七杂八的东西往河里乱撂,你说河哪有不脏的。
开日杂店的庆平接着说,以前穷的时候又没得什么垃圾,所有的垃圾都是肥料,都能送到大田里去的。哪像现在,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倒在哪里一百年都烂不掉。“自从用了化肥,这世界上就脏了不少——以前在路上有一颗鸡屎狗屎人都像个宝拾起来哩!”他想了发笑,背诵道,“粪肥是个宝,庄稼少不了。鲜灰熟粪烂河泥,沤到田里值大钱。”
存扣听了也发笑,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这些乡间民谚他小时候上学都背过的,那时学生课后背个粪筐满世界拾粪,为谁先看到一堆大狗屎争得打起架来的都有。
开缝纫店的阿虎说,现在到了夏天,下河洗澡的孩子都不大看见了。河泥太深,水太脏,玻璃瓦瓷的又多——“以前罱泥的人罱到一丁点戳人的东西都要拣出来的。现在摸鱼的一碰(方言:常常,冷不丁)就把手划开来戳开来了,摸歪儿的人不敢下水用脚踩用手摸,都是用耙子扒。”
杀猪的宝宏说,我们顾庄水大还好些,他东台县的姐姐家那庄上根本就找不到一条能下水洗澡的河了,弄得水乡的伢子都不会游泳了。大人带着他们上东台县城花钱到游泳池里去学,真是日了鬼了。
月红嫂插上一句,说最让人憋气的是出门就见水,水却不能吃,不能用。八百年也想不到水乡人却要用自来水,“以前的水多好吃呀。下河一拎就有,要多少有多少,不花一分钱!”
自从向阳河上游建了个农药厂,顾庄这边的水就没法吃了,有药水味。有年发大水,排污塘的废水漫出来,一条河里的鱼死得白花花的。人站在河岸上,被药水味都呛得头昏。村民造起反来,乡里只好给装了自来水。
存根说,其实我也代卖农药,本不该说农药不好,但实事求是地讲呢,自从有了农药,还有化肥,农业产量是成倍地翻,但给人带来不好的东西也多,最典型的是种出来的东西不好吃了。以前新米儿煮起粥来那米油多厚,粥膜子拿筷子一挑多高,鼻涕似的。现在哪有什么米油粥膜子,煮出来清汤寡水的,像煮的烫饭;新小麦一出来家家都炒焦屑吃,那个麦香哟……现在有些才打出来的粮食还不敢吃,要把它陈陈。药水打得太重,农药残留大,人吃了得癌症。田里的农药化肥渗进淌进河里去,鱼呀虾的也都没得以前好吃了,不鲜。
福生说,现在田里的蛇和青蛙也少了,以前泥鳅一抠一水桶,现在你去抠抠看,全被化肥腌死了,被农药药死了;连天上飞的麻雀都少了。
又谈起了社会风气。说现在人赚钱没心没肺,只要能发财,杀头的钱都敢挣。开浴室就等于开妓院,假装医生卖假药的,用假钱套真钱的,装和尚尼姑化缘的,给人下蒙汗药的,还有偷跟抢的,现在哪样没有?当官的贪的多哩,不贪又受排挤做不长,受害的就是老百姓……现在人胆子大,脸皮还厚,以前庄上有哪个人犯了法多稀罕,坐牢出来后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犯法坐牢的不新鲜了,出来还耀武扬威的——“老子是从山上下来的!”坐牢倒像有了本钱、成了英雄——有的人释放回来,家人在几里路外就放起了炮仗,还敬菩萨,摆酒请客,像迎接新科状元似的……
阿虎转了一句文:“说这就叫世风日下,美丑不分!”
存根说这种世相也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不知不觉中人也就慢慢适应了,见怪不怪了。有时候自己也就加入了这中间,回过头想想,都不晓得是啥时候被这风气同化了。
福生却叹了口气,虽说现在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收入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可人却觉得累,还不如以前穷的时候。那时候虽然苦,缺吃少穿的,却容易得到真快乐,吃一顿肉就开心得不得了,来个电影船像过节一样……“说实在的,不是我人贱,有时候我还真怀念那时候。”
《盐城》第一章6(2)
月红笑道:“你还真是贱,果真回到那个时候,你一天也挨不下来。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偷了家里一个鸡蛋到商店里卖了六分钱,五分钱买块烧饼,一分钱买糖,被你爸爸打得屙了一裤子的事?”
福生连连告饶:“好嫂子,别提这事,现在大家正在吃酒哩!”
大伙儿全笑起来。
……
散席后,存扣睡在楼上东房里,仍想着酒桌上谈的话题。他想改革开放这些年,农民生活富旺了,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但农村却不如以前干净了。其实城市何尝不也是这样。为什么经济的发展要以牺牲环境做代价呢?难道就没有两全的办法吗?同样,我们的物质文明在不断进步,而精神文明却有些脱节,人们的精神也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很多人变得急功近利,疏离和背弃道德,甚至于法律,这多么可怕呀……
他突然心里就蹦出了“原始”这个词。
记忆中的很多东西是原始的,这些原始的东西将顽固地占据他的心灵,直至永远。
譬如故乡。故乡是他生命开始的原乡,她应该是美丽的。可眼下的故乡却在发生着不少差强人意的变化。
初恋是生命开始的另一种原乡,她应该是美丽的。秀平是她的初恋,可是秀平却过早地夭折了。阿香是他的另一种初恋吧,但又以悲剧而告终。
还有……理想。他原始的理想显然是做一个作家。这是他孩提时捧读着机工保国借给他的大书时就萌生的梦幻愿望,这是他和秀平一起论证和巩固多次的美丽计划。可是现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人。
为什么美丽的东西是那么容易破碎,是什么让人们无法坚守“原始”?
前几天,在谭咏麟的《杨花》歌声中,他已经为他原始的理想掬过一捧感伤的热泪!
现在,存扣固执地认为,他的这次回乡是基于一种冥冥中的呼唤,故乡的呼唤,秀平的呼唤。现在他已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故乡——还有秀平——又要告诉他什么呢?
“姐姐!是你唤我回来的吗?你要告诉我什么呢?”存扣在黑暗中问着秀平,泪水潸然。
他的头脑中突然就闪起了电光!——“姐姐,难道你是要告诉我不要忘记我俩共同设计过的理想,要我恪守和重拾文学梦?”
肯定是的!你曾说过,我这辈子一定要写出一本好大书来的!“你现在还在等吗?姐姐!”存扣哽咽不能自禁。
……
《盐城》第二章1
次日清晨,存扣扛着装满纸钱的蛇皮袋悄悄地出发了。袋子太大,他不得不弯着腰,看不见他的头脸,像个负重的满载而归的拾荒者。他不好意思走大街,从庄后绕了过去,但还是被不少人看到了。从村西到老八队后面的墓地,起码四五里路,袋子虽不重,但“远路没轻担”,又得弯腰低头,累得实在够呛。
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