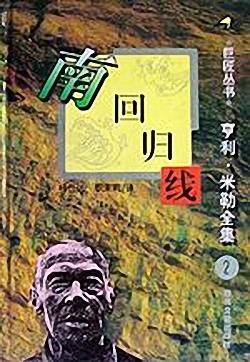南回归线-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尊敬他们。我们自己单独在一起时,我们的想像就无拘无束。事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性;我们要求于一个题目的东西,就是它得给我们驰骋的机会。我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惊奇不已的是,我们相互间的理解有多好,我们多么尖锐地看透了每一个人的基本性格,无论大人小孩。例如,我们在七岁的年纪就十分确切地知道,这个家伙最后会蹲监狱,那个家伙会成为一个苦力,还有一个家伙会成为饭桶,等等。我们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例如,比我们父母的判断正确得多,比所谓心理学家的判断更正确。阿尔菲·贝查结果成为一个彻底的叫花子;乔尼·盖哈特去了监狱;鲍勃·昆斯特成了一个干重活的人。正确无误的预言。我们接受的知识只会阻挡我们的视野。从我们上学那天起,我们就什么也没学会;相反,我们被搞得迟钝不堪,裹在语言与抽象的云里雾中。
有酸黑面包的时候,世界是它本质上的样子,一个由魔法统治的原始世界,一个恐惧在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世界。能激起最大恐惧的男孩就是头儿,只要他能维持他的权力,他就受到尊敬。还有一些其他的孩子是造反派,他们受到赞美,但从来没有成为头儿。大多数人都是那些无畏者手中的粘土;有一些可以依靠,多数靠不住。气氛十分紧张——无法预言明天会有什么事。这种松散的、原始的社会核心,产生出强烈的胃口,强烈的情绪,强烈的好奇心。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每一天都要求有一种新的力量检验,一种新的力量感,或失败感。因此,直到九十岁的年纪,我们都有着真正的生活趣味——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够幸运的,未被父母宠坏,夜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逛,亲眼去发现事物。
我现在带着某些遗憾和渴望想念着的事情是,早先童年时代这种极有限的生活却好像无限的宇宙,而随后的生活,成年人的生活,则是一个不断缩小的王国。从一个人被放到学校里去那一刻开始,这个人便迷失了,人们会有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感觉。面包的味道没有了,生活的趣味也没有了。得到面包变得比吃面包更重要。一切都要盘算,一切都有一个价码。
我的表弟勒内成了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斯坦利成了一个一流的失败者。除了这两个我十分喜爱的孩子以外,还有一个乔依,他后来成了一个邮递员。当我想起生活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时,我就会哭泣。作为男孩,他们是完美的。斯坦利最不完美,因为他更冲动。斯坦利时常暴跳如雷,不知道你如何能同他一天天相处,而乔依和勒内则是善的本身;他们是朋友,是按这个词的古老意义来理解的朋友。在我外出到乡下去的时候,我经常想起乔依,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乡下小孩。这首先意味着他比我们认识的男孩子更忠实,更真诚,更体贴。我现在可以看到乔依来见我;他总是张开双臂跑过来,准备拥抱我,总是被他为我的参与而设计的冒险搞得上气不接下气,总是装满了他为我的到来而攒起来的各种礼物。乔依招待我就像古代的君主招待他们的宾客一般。我看一眼任何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便是我的了。我们有无数事情要相互告知,没有一件事情是沉闷乏味的。我们各自世界的差异是巨大的。虽然我也属于这个城市,但当我拜访我的表弟勒内时,我才了解到一个更大的城市,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纽约城,在其中,我的世故是微不足道的。斯坦利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居住区去远足过,但是斯坦利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个陌生国度波兰,我们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他说另一种语言,这个事实也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崇拜。每个人都被一个与众不同的光环所环绕,被一种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的明确身分所环绕。由于进入生活,这些不同的特征消失了,我们大家都变得多少有点儿相似,当然,最不像我们自己。正是这种独特自我的丧失,这种也许并不重要的个性的丧失,使我黯然神伤,使黑面包鲜明突出。奇妙的酸黑面包形成了我们的个别自我;就像圣餐面包人人有份,但是每个人只是按照他独特的皈依上帝的状态来接受圣餐的。现在我们吃着同样的面包,却没有圣餐的恩惠,没有皈依上帝。我们吃面包来填饱肚子,而我们的心却是冰冷的,空虚的。我们是分开的,但不是个别的。
30
《南回归线》第九章(3)
关于酸黑面包还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们经常一边吃面包,一边吃生葱。我记得在傍晚前,手里拿着三明治,同斯坦利一起站在我家正对面的兽医诊所门前。似乎麦基尼医生总是选择傍晚前来阉割一匹公马,这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的手术,总是聚集了一小群人。我记得烙铁的气味和马腿的颤抖、麦基尼医生的山羊胡子、生葱的味道以及阴沟里的气味,因为就在我们身后,他们正在铺设煤气管道。这完全是一场嗅觉表演,而正如阿伯拉尔阿伯拉尔(1079—约1144):法兰西逻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神学家。
——译者惟妙惟肖地描绘的那样,手术实际上不痛。我们不知道手术的理由,常常在手术后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往往以争吵告终。我们俩都不喜欢麦基尼医生;他身上有一股碘仿味和臭马尿味。有时候他诊室前面的街沟里淌满了血,冬天时血结成冰,使他那边的人行道有一种古怪的样子。时常有一辆两轮大车驶过来,一辆没有遮掩的车,散发着可怕的臭味,他们把死马扔到车上。确切地说,尸体是用一根长链子吊到车上去的,链子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就像抛锚一般。患气胀病的死马的气味很难闻,我们那条街上满是臭味。然后还有酸味从我家房子后面的锡工厂传来——像现代进步的味道一样。几乎令人不能忍受的死马味,比起燃烧的化学品的味道来,还要好上一千倍。看到太阳|穴上有个枪眼的死马,看到它的脑袋躺在血泊中,它的屁股眼里满是痉挛地排泄出来的最后排泄物,也比看到一群穿着蓝围裙的人从锡工厂的拱形大门里走出来,看到他们推着一辆装着一捆捆新制成的锡的手推车强。对我们来说,幸好锡工厂对面有一个面包房。面包房的后门,其实这只是一个铁栅栏,我们可以从那里看面包师傅工作,闻一闻那甜蜜的、不可抗拒的面包、蛋糕的香味。我说,要是那煤气管道铺在那里,那就会是另一种味道的大杂烩——翻起来的泥土味、烂铁管味、阴沟气味,以及意大利劳工靠在翻起的土堆上吃的洋葱三明治的味道。当然,也还有其他味道,只不过不太明显;例如,西尔弗斯坦裁缝铺的味道,那里总有大量熨烫工作在进行。这是一种热烘烘的恶臭,你要理解这种味道,最好想像一下,西尔弗斯坦,他本人就是臭烘烘的干巴犹太人,正在把他的顾客们留在裤子里的臭屁抖落出去。隔壁是两个信教的笨蛋老Chu女开的糖果与文具店;那里有太妃糖、西班牙花生、枣味胶糖、“甜烟丝”香烟等等几乎令人作呕的甜味。文具店就像一个美丽的洞|穴,总是冷冷的,总是摆满各种有趣的物品;冷饮柜就在那里,它发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味道。一块厚实的大理石板横放着,在夏季时节,石板变得酸溜溜的,而它又令人愉快地把酸味同碳酸水嘶嘶地倒进冰淇淋杯里时发出的那种叫人心里痒痒的、干巴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31
《南回归线》第十章(1)
长大以后,各方面都有了精细的改进,原来那些味道没有了,只是有另一种显然难忘的、显然令人愉快的味道——窟窿眼儿的味道——取代了它们。尤其是同女人玩过之后留在手指上的那种味道,因为也许以前没有注意到,可这种味道甚至比窟窿眼儿本身的味道更可爱,因为它带着已成为过去时的香水味,但是,这种表明你已长大的味道,同童年时代的那些味道相比,只是一种微弱的味道。这种味道在你大脑的想像中几乎同在现实中消失得一样快。对于所爱过的女人,人们会记得她们的许多事情,但是却很难记得她们那眼儿的味道——全然不会。另一方面,湿头发的味道,一个女人的湿头发味道,却更加强烈持久得多——为什么呢?我不知道。甚至现在,在差不多四十年之后,我还能记得我蒂丽姑妈洗头以后的头发味道。她总是在热得要命的厨房里洗头。通常是在星期六傍晚前,为参加舞会做准备,而舞会又意味着另一件怪事——会出现一个佩带十分漂亮的黄|色条纹装饰的骑兵中士,一个非常英俊的中士,甚至在我眼里,也是太彬彬有礼,太有男子气概,太聪明伶俐了,像我蒂丽姑妈这样的低能儿根本配不上他。但不管怎么说,她坐在厨房餐桌旁的小凳上用一条毛巾擦干头发。她旁边放着一盏罩着熏黑的玻璃罩的油灯,灯旁边是两把烫发钳。我一看到这些就充满莫名其妙的厌恶。她总是使用一面支在桌上的小镜子;我现在可以看到她一边挤鼻子上的黑头粉刺,一边对自己做怪脸。她是一个难看的女人,没什么本事,粘粘乎乎,呲着两颗大獠牙,只要她一笑,嘴唇往后一掀,就露出一副马脸。她就是洗完澡以后,也散发着一股汗味,但是她头发的味道——那种味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不知怎么的,这味道同我对她的恨和轻蔑联系在一起。这种味道,在头发干起来的时候,就像从沼泽地底下发出来的味道一样。有两种味道——一种是湿头发的味道,另一种是她扔到炉子里,燃烧成火焰的同一种头发的味道。她总是梳下来一些打了结的头发卷,它们还带着她油腻肮脏的头皮上的汗与头皮屑。我常站在旁边看她,很想知道舞会会是什么样子,很想知道她在舞会上做些什么。在她全部打扮完毕的时候,她会问我她看上去是否漂亮,我是否爱她,当然,我会告诉她:是的。但是然后在厕所里,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