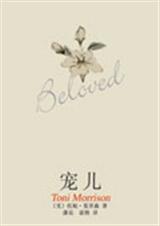宠儿-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官去右边。一个疯疯癫癫的老黑鬼拿着把斧子站在木头堆里。你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疯子,因为他在咕哝着………发出低沉的、猫一样的呼噜声。离他大约十二码远处是另一个黑鬼………一个帽子上戴花的女人。可能也是个疯子,因为她也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手扇着,仿佛在把蜘蛛网从眼前拨开。然而,两个人都盯住了同一个地方………一间棚屋。侄子向那个老黑鬼走去,从他手里拿下斧子。然后四个人一起向棚屋走去。
里面,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淋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在作第二次尝试。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就在这群人紧盯着面前的一切的当儿………那个仍在低吼的老黑鬼从他们身后的屋门冲进来,将婴儿从她妈妈抡起的弧线中夺走。
事情马上一清二楚了,对〃学校老师〃来说尤其如此,那里没什么可索回的了。那三个(现在是四个………她逃跑途中又生了一个)小黑鬼,他们本来指望他们是活着的,而且完好得可以带回肯塔基,带回去正规培养,去干〃甜蜜之家〃亟待他们去干的农活,现在看来不行了。有两个大张着眼睛躺在锯末里;第三个的血正顺着那主要人物的裙子汩汩而下………〃学校老师〃四处夸耀的那个女人,他说她做得一手好墨水,熬得一手好汤,按他喜欢的方式给他熨衣领,而且至少还剩十年能繁殖。可是现在她疯了,都是因为侄子的虐待,他打得太狠,逼得她逃跑了。〃学校老师〃训斥了那个侄子,让他想想………好好想想………如果打得超出了教育目的,你自己的马又会干出什么来。契伯和参孙也是一样。设想你那么过分地打了这两条猎狗。你就再也不能在林子里或者别的地方信任它们了。也许你下回喂它们,用手递过去一块兔肉,哪个畜生就会原形毕露………把你的手一口咬掉。所以他没让那个侄子来猎奴,以示惩罚。让他留在家里,喂牲口,喂自己,喂丽莲,照管庄稼。给他点颜色看看;看看你把上帝交给你负责的造物打得太狠了的下场………造成的麻烦,以及损失。现在所有这些人都丢了。五个哪。他可以索要那个在喵喵直叫的老头怀里挣扎的婴儿,可是谁来照料她呢?都怪那个女人………她出了毛病。此刻,她正盯着他;要是他的侄子能看见那种眼神,他肯定得到了教训:你就是不能一边虐待造物,一边还指望成功。
现在这个侄子,他兄弟按住她时吃她的奶的那个,不由自主地战栗着。他叔叔警告过他,要提防那种慌乱,可是看来这个警告没被采纳。她干吗逃走,还这样做?为了一回打?妈的,他挨过一百万次打,他还是个白人呢。有一回打得特别疼,气得他摔坏了水桶。另一回他把气撒到了参孙身上………也不过扔了几颗石子。可是挨打从来没让他……我是说他不可能会……她干吗逃走,还这样做?他就这样问了警官这个问题,警官正站在那里像其他人一样惊诧不已,但没有战栗。他使劲咽着唾沫,一口接一口地。〃她干吗想逃走,还这样做?〃
警官转过身,然后对其他三个人说道:〃你们趁早都走吧。看来没你们什么事了。该我了。〃
〃学校老师〃用帽子使劲抽打自己的大腿,离开木棚屋之前又啐了一口。侄子和猎奴者跟他一起退了出来。他们没去看胡椒地里那个帽子上戴花的女人。他们也没去看猎奴者的枪没能拦住的七张凑过来的脸。够了,黑鬼的眼睛。黑鬼小男孩的眼睛在锯末里张着;黑鬼小姑娘的眼睛在血淋淋的手指缝里瞪着,那只手扶住她的脑袋,好让它掉不下来;黑鬼小婴儿皱起眼睛在老黑鬼的怀里哭闹,老黑鬼的眼睛只不过是两道裂缝,正盯着自己的脚面。然而最可怕的是那个女黑鬼的,看上去就像她没有眼睛似的。眼白消失了,于是她的眼睛有如她皮肤一般黑,她像个瞎子。
他们从〃学校老师〃的马身上解下那匹借来的、本来要运女逃犯回去的骡子,拴在栅栏上。然后,他们顶着烈日骑马走了,把警官留在身后这伙罪该万死的黑熊中间。他们全部目睹了以一点所谓自由来欺骗这帮人的恶果,这些家伙需要世上一切的监督和指导,才能避免他们自己更喜欢的同类相残的生活。
警官也想退出来。走出这间本该贮藏木料、煤炭、石油………寒冷的俄亥俄冬天的燃料………的棚屋,站到屋外的阳光里。他一边这样想,一边抗拒着跑进八月阳光里的冲动。不是因为害怕。根本不是。他只是觉得冷。他也不想碰任何东西。老人怀里的婴儿在哭,那女人没有眼白的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方。他们都可以就那样一直待下去,冻结到星期四,可是地上一个男孩叹了口气。仿佛沉溺在甜美酣睡的乐趣中,他这一声轻叹叹得警官猛一激灵,立即开始行动。
〃我必须把你抓进去。别再找麻烦了。你已经干得不少了。现在跟我走吧。〃
她没有动。
〃你乖乖地走,听见没有,我就不用把你捆起来了。〃
她还是不动,于是他决定走近她,想个办法捆上她那双血淋淋的手,这时他身后门口的一个人影让他转过头来。帽子上戴花的黑鬼走了进来。
贝比·萨格斯注意到谁还有气、谁没气了,便径直走向躺在尘土里的男孩们。老头走向那个女人,盯着她,说道:〃塞丝,抱着我怀里这个,把你的那个给我。〃
她转过头,瞟了一眼他怀里的婴儿,喉咙里低叫了一声,就像她出了个错,面包里忘了放盐什么的。
〃我出去叫辆大车。〃警官说着,终于走进了阳光。
可是无论斯坦普·沛德,还是贝比·萨格斯,都不能让塞丝把她那〃都会爬了?〃的女孩放下。走出棚屋,走进房子,一直抱着她不放。贝比·萨格斯已经把男孩们带了进来,(奇*书*网。整*理*提*供)正在给他们洗头、搓手、扒开眼皮,自始至终嘀咕着:〃请原谅,请你们原谅。〃她包扎好他们的伤口,让他们吸过樟脑,然后才开始对付塞丝。她从斯坦普·沛德手里接过哭闹的婴儿,在肩膀上扛了足足两分钟,然后站到孩子的母亲面前。
〃该喂你的小宝贝了。〃她说。
塞丝接过婴儿,还是没撒开那个死的。
贝比·萨格斯摇了摇头。〃一次一个。〃她说着用活的换了死的,把死的抱进起居室。她回来时,塞丝正要将一个血淋淋的奶头塞进婴儿的嘴里。贝比·萨格斯一拳砸在桌上,大叫道:〃洗干净!你先洗干净!〃
于是她们厮打起来。仿佛在争夺一颗爱心,她们厮打起来。都在抢那个等着吃奶的婴儿。贝比·萨格斯一脚滑倒在血泊之中,输掉了。于是丹芙就着姐姐的血喝了妈妈的奶。她们就那样待着,直到警官征用了一辆邻居的运货马车回来,命令斯坦普来赶车。
这时,外面的一大群黑脸孔停止了嘀嘀咕咕。塞丝抱着那个活着的孩子,在他们和她自己的静默中走过他们面前。她爬进车厢,刀锋般光洁的侧影映入欢快的蓝天。那侧影的明晰使他们震惊。她的头是否昂得有点太高了?她的背是否挺得有点太直了?也许。否则,在她从房子门口出现的那一刻,蓝石路上的歌声就会马上响起来了。某种声音的披肩就会迅速地裹上她,像手臂一样一路搀扶她、稳住她。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一直等到货车朝西掉头、向城里开去,才唱起来。然后也没有歌词。哼唱着。一句歌词也没有。
贝比·萨格斯本来想跑,跳下门廊的台阶去追运货马车,尖叫着:不。不。别让她把那个最小的也带走。她本来要这样做,也已经开始了,可是当她从地上站起来,走进院子,运货马车已经没影了,而一辆大车隆隆而至。一个红发男孩和一个金发女孩跳下车,穿过人群向她跑来。男孩一手拿着吃了一半的甜椒,一手提着一双鞋。
〃妈妈说星期三。〃他提着鞋舌头,〃她说你得在星期三之前修好。〃
贝比·萨格斯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大路上拽着缰绳的女人。
〃她说星期三,你听见了吗?贝比?贝比?〃
她从他手里接过鞋………高靿的,沾着泥………说道:〃请原谅。主啊,我求你原谅。我真的求你了。〃
视线之外,运货马车吱吱呀呀地驶下蓝石路。里面没有人开口。大车已经把婴儿摇晃得睡着了。炎热的太阳晒干了塞丝的裙子,硬挺挺的,仿佛尸僵。
那不是她的嘴。
素不相识的人,或者也许只从餐馆的门洞里瞥见过她一眼的人,可能会认为那是她的嘴,但是这事保罗·D更明白。噢,的确,前额上还笼罩着那么一点东西………一种安详………能使你想起她来。可是你单凭这个就说那是她的嘴,那可不行,于是他就这样讲了。告诉了正在审视他的斯坦普·沛德。
〃我不知道,大叔。反正我看着不像。我认识塞丝的嘴,可不是这样。〃他用手指抚平那张剪报,凝视着,丝毫不为所动。从斯坦普打开报纸的庄严气氛中,从老人用手指按平折痕,先是在他的膝盖上、然后在树桩劈裂的顶端将它摊平的慎重中,保罗·D知道,它该搅得他不得安宁了。无论那上面写的是什么,都会震动他。
猪在滑运道里嚎叫着。保罗·D、斯坦普·沛德和另外二十多人一整天都在把它们催来赶去,从运河到岸上到滑运道再到屠宰场。尽管由于粮农迁往西部,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现在吞并了许多企业,但辛辛那提在俄亥俄人的印象里仍旧是猪的港口。它的主要职责是接收、屠宰和向上游运去北方人离不开的肉猪。冬天里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有流浪汉都有活儿干,只要他们能忍受死牲口的恶臭,一连站上十二个小时。这些事,保罗·D都令人惊叹地训练有素。
他冲洗干净身上所有够得着的地方,还剩一点猪屎粘在他的靴子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