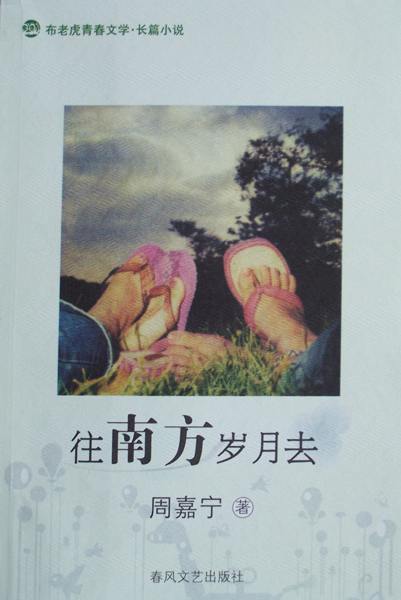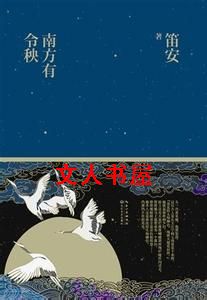南方·爱-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饰厕中,主要有供双脚放置的两块足悬石、前迫石、后迫石,还有一个铺着雪白细砂粒的尘|穴。
饰厕里的石头,是川石,象征清洁无垢。
这种饰厕,用途只是供欣赏用。在茶事开始前,由主人在石头上洒满装有花叶的清水,傍晚时还点上灯笼,是供客人当做艺术品观玩的。
田红生当然不知道饰厕的作用,当时加之他腹内雷鸣,裤子一扒,一泡稀屎,全部拉在雪白的细砂石上。
黑黄|色的稀屎,与饰厕角落里一朵怒放的鲜艳山茶花,交相辉映,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我实在忍不住笑,只得紧紧咬住嘴唇以免自己笑出声来……
该到向日本“塞哟那拉”的时候了。
田红生正撅着屁股收拾东西。他把酒店里的和式睡衣、烟灰缸、火柴盒、衣架、香皂、洗发液,甚至手纸,都一件不拉地塞进包里拿回去作纪念。他就差连地毯也掀起来带走了。
这个平素一脸正气全身挺刮西服的家伙,此时忙得身上热汗直冒,假发随便扔在桌子上,身上只着一件半透明的一次性内裤——他已穿了一星期,原本的白色已成灰黑色了。
这就是我平素点头哈腰要巴结的中层领导,在国外连一点儿尊严也没有,十足的一个鸟毛。
25。独自去偷欢(1)
我坐在酒吧的高脚凳上,黯然地喝着酒。
其实,我对酒一丁点儿也不感兴趣,那种苦辣入喉,令人极其不舒服。我主要是想,在这种活人拥拥的地方感受活意,或许能从红男绿女们沸腾的生活中,汲取我所缺乏的活力。
耀闪灯光之下,我看见一个姿色甚美的年轻女人,正同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外国人紧拥着跳舞。
“妈的!”我心中咒骂一句。总会有漂亮年轻的女孩喜欢勾搭老外。好×都让洋狗操了。
那个年轻女人与金发老外相拥着来到柜台前,就坐在我旁边。她过于投入,眼波荡漾在洋汉子的脸上,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近在咫尺的我的存在。
我漠然地喝着酒。那女人纯正的法语清晰入耳。这是真正悦耳动听的法语,一丁点儿口音都没有,如同我在大学外语系上二外课时法国原版的教学带那样动听,微带喉音,有一种金属的质地。
我突然笑了,我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它太过于简单——钱就是一切,似乎每个人的生活目的都是为了钱。
钱流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城市,经过百万富翁的真皮腰包,在女人们的丝绸胸罩或细羊皮的手袋内逗留,再跳过熙攘不堪的大饭店柜台,变成提款卡内的无形钱流,再化为可触可摸的奢华物品。
金钱,在银行、商店、饭馆、不知名的药铺、性病走方郎中的钱箱内,流动,流动,一直流呀流呀,再流出城市,奔向不知名的地方。
“钱能买到一切……真的,钱可能买不到爱情,但这个城市没有爱情。”记得以前在商业银行时,我有一位身价千万的客户曾满口哲理地对我说。那个小学毕业、木匠出身、其貌不扬的矮子,曾经是我鸡鸣狗盗客户中很让人感兴趣的一员。每当他张口说话之前,他都会把戴满五个戒指的右手伸出向空中猛力一晃,在一道金弧划过后方才开腔。“我曾经一床睡三个妞儿,她们的学历分别是研究生、本科生和大专生,我让她们把毕业证放在枕头边上,研究生五千元,本科生三千元,专科生二千五。瞧,在我这里,真正体现了知识的层次感以及知识的价值……不过依我个人经验,学历越高,干那事的投入感就越差……我倒喜欢山里的村妞,原始激|情,哎呀哟,震荡啊,扑腾哟,那嗷嗷的叫声令你……那句成语怎么说……意猿……不……心猿意马……”
我寂寂地独自饮酒,心中空空荡荡。
追求点什么、热爱点什么的感觉,对我来讲,似乎丧失已久。金钱,对我好像诱惑不是很大;所谓的仕途,也是一种幼稚可笑的东西。
我总是牛×哄哄地自我沉醉,觉得类似贵族的血液在我体内流淌。我一直对自己说,绝不会劳心劳力、失去人格地去追求过多的金钱。
爱情,爱情,才是种把握不住的虚幻,它很遥远,很高尚,像梦中的星星;它同时又很真实,很低下,很不堪一击,如女人花儿般美丽的身躯——几百元就能买一次。
我脑子里有许许多多不想回忆的回忆,有的深有的浅。深的,诸如……林紫倩——她那几根美丽手指的温柔,回想起来,温柔似唇吻,脆冷如琉璃……这些刻入骨髓的陈年旧梦,对我日后的生活道路影响之巨,甚至超出了我自己的想象力。
对她的不尽思念,让我终于明白了物质世界物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洞悉了生活中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确实有一些不完全是文人的胡编乱造。
我步入社会以后,接触过许多女人,包括像文琴美那样的一夜之恋或者多夜之恋——但她们在我脑海中都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我赶紧扭头仔细观察身边那个陪同老外说法语的女人,想寻找存在的世界。
我只看到,她侧面,美丽,高雅,却永远朦胧于烟雾酒气之中,看不甚明。这个女人,仍旧沉醉于她自己流畅的法语和情愫之中,她对面外国人微胖的脸,混合着巴黎的高雅和巴黎的淫秽……
这个城市,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美女,其中不少在各大宾馆、酒吧做流莺,幸运些的成为港商台商的包养情妇,倒霉的沦落到街边发廊倚门卖笑。
25。独自去偷欢(2)
我忽然涌起一股冲动——去找个素不相识的女人!
所谓“白领”的高雅女人,我已经厌倦了。
“花钱买欢!”这个念头如同导火索的火焰,一经点燃便无法熄灭。
我感觉到了一种新鲜的热望已在体内升腾,它类似酒精和大麻的混合体,令人精神勃发,充满崭新的欢愉。
即使现在,没有江学文在身边,我也有足够的胆量去寻欢。
我把酒杯重重地顿在大理石的台面上,酒滴溅入了眼睛,火辣辣地痛。
高级的桑拿洗浴熟人太多,不是安全的好去处。而黄岗区的上步林,一处鱼龙混杂之地,那里有数不清的食肆和发廊,也有数不清的张贴在电线杆子和墙壁上的治疗性病和梅毒的广告。从这些走方郎中手工印刷的广告中可窥见讯息:此地游妓众多。
发廊妹们坐在屋内向外面行人频频吆喝:洗头、洗头,阿生进来洗头。
这些姑娘大多是外省乡下妹,偶尔有几个小城镇的流莺,大概才刚刚学会用眼神撩人——“秋波”滞缓,也不那么诱人,毕竟刚从电影、电视剧中学来的。
我徜徉其间,稍许的兴奋新奇之余又似有芒刺在背,生怕遇见什么熟人。我忐忑不安,急切渴望有哪个洗头妹把我拉进发廊。
倒是那些粗壮庸俗的民工模样的汉子大合妹子们的胃口。他们一身臭汗,用乡音打着哈哈纷纷拥进发廊。每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内,都会有七八个洗头妹或坐或立,任意挑选,大屋旁边的小门,挑帘进入,便是寻欢作乐之所。
我很是纳罕,自忖为什么没有人来勾引自己。想了半天,我觉得,可能自己那身惹人眼目的“高级”西服上装,让游妓们望而止步。
洗头妹们的智力水准,可能判断不出我的来头和目的,说不定以为我是便衣。
这一点,我自己事先并不清楚,倒是可能有几个外地民工盯上了我,尤其盯上我腕上的手表和项间的白金链。大概,他们随时准备找个黑暗处,一拥而上,把我抢个精光。
我很感失望和失落。刚才在酒吧内那种强烈的欲望开始消退,如今,欲望被一种尖锐的烦躁所替代。
我周身开始出汗,步子加快,眼看就到了巷子的尽头。
我该不该折回去呢?难道就这样白来一趟?
多年来令我痛苦不安的怯懦又开始袭击了我。
退缩,我自小就为此深深自卑,这令我失却了许许多多的机会,包括一两次可能发生的爱情。
我站定脚步,“这是个自信心的问题。”我暗中对自己说,“懦弱是虚假的,是自我退却的无力辩护,要打破虚空,做自己想干的事……”
我猛然走进距自己最近的一间发廊。
发廊内恰恰没有顾客,只有七八个洗头妹,都大睁双眼望着我,竟然没人上来招呼。
教养是一件僵硬的外套,我一时间竟喉咙发干说不出话来。
我经历过诸多大场面,能够熟练地当着三百人同声口译外宾的讲话,也在陪同公司高层宴饮的席间谈笑自若,还可以周旋于数位所谓的高雅淑女之间。
然而,如今,当我面对一堆乡下妹时,不可告人的欲念却令我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
“我……我要洗头。”嗫嚅半晌,我方才说出一句话。
我小心翼翼地坐着,双手搭在自己腿上——椅子把手上油渍斑斑,令人作呕。
我坐在那里周身很不舒服。
冷冷的水浇在我的头上,洗发水刺鼻的假香。
干惯重活的乡下妹子劲很大,简直要把我的头皮搓抓下来。我用力挺直脖子以免脑袋摇晃。
身后的洗头妹生得黑胖粗蠢,肥嘟嘟大脸上一双牛眼倒是炯炯有神。
我欲望全消。
门外又进来一个肉贩模样的粗壮汉子,顿时有几个洗头妹拥上前去。“要不要洗头,老板?”“阿生用哪种发水?”“我们店便宜,洗头只收十五元。”
25。独自去偷欢(3)
那汉子瞧了瞧我,大概觉得我的样子文弱可欺,没有威胁感,更不像是公安便衣,于是他的态度便陡然放肆起来。“嗯,大爷我不要洗头,要按摩。”汉子两只手同时在两个洗头妹胸脯摁了两把。
那几个洗头妹不吱声,靠门的一个朝门外左右窥视了一会儿,向屋内点点头。顿时,几个洗头妹唧唧喳喳地争抢“客户”。
“好啦,好啦,老板,我陪你。”那个年纪较大一些的黑瘦女人用手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