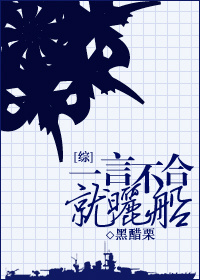言不由衷-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戴欣和笑柔做了一个交易,只要她把言士尹干过的好事和一张伪造言氏财务盗窃的栽赃检举上去,等到戴氏过继了言氏的所有股份,和她三七分成,让言家欠她的,统统补偿回来。
笑柔收了那张光碟,不费心思把曹舒芮弄晕,偷得了护照从美国跑回来。看见言方时她还以为有那么一点希望,但是他却转过身,头也不回的走掉,那日还下着雨,她蹲在行人寥寥的街口,嚎啕大哭,原来那一夜之间,她已经一无所有。
她给自己伪装了一个冰冷的面具,冰封了自己的软弱,用手上的利器去换一场她想要的婚姻。明知道那样没有幸福,或许别人会说不是非得那个男人不可,可是她赵笑柔,这辈子固执认定了一个人,那就是非言方不可。
言方必不可能答应他,她只能去威逼利诱,诱饵其实很吸引,可是言方依然把持得住。
'调整顺序。'
“这样我们都不会有幸福的。”
“幸福?”她冷笑起来,“我还有幸福吗?爸爸死的时候我以为我的幸福会是妈妈,可是当我知道所有事情后,我的幸福呢?你能给得了我?”
言方无语以对。
“肯或者不肯?”她咄咄逼人。
“笑柔。”言方伸长手臂,想拥她入怀,但她冷冷的避开。
“没用的,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我现在只要你的答案。”
“我们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笑柔撇过头,空调丝丝吹得透心彻骨的凉:“没有。”
车厢因为两人的剑拔弩张而变得沉寂压抑,暗涌像海啸一样无声地翻滚过来,把原本逼仄的空间压得让人难以喘息。
“我不能……”
“够了。”笑柔蓦然大声打断他,“已经三个字了,已经够了。”她凄凉地笑起来,眼泪再也无法束缚,从瞳中流出,簌簌划过脸庞低落消失在衣衫中。
她用手支着额头,只觉得那里疼得厉害,一阵阵昏眩击过来直要把她掀倒。她就知道,就算拿上一切来逼他,最后的结果不还是这样吗?答案再明确不过了。
她找到把手打开车门,从容地站出来。言方见她脸色有些苍白,亦担心地追过去,她不肯让他靠近:“别过来,让我静一静。”
“笑柔。”他还是担心,她的脚步有些踉跄。
“你回去吧,我自己静一静。”她看着他站在原地,确认他不会跟过来,转身泰然自若的离开。
泪水要流就让它流吧,流干了是否心就不会再痛了。她嘲笑自己傻,傻得天真傻得透顶,她以为用那些东西逼他,他就会答应娶她。
罢了,这么一闹一颗心早就累得干涸麻木了,他们没有以后了,那条路人从中隔开,他们各自站上了一条不归路,然后背道而驰,越走越远,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她不知道走了多久,每一步都是虚的,像踩在浮云上摇摇晃晃。
刺眼的阳光从两座高耸的大厦之间像一束强光照耀下来,笑柔正好抬头看红绿灯,阳光射进眼里,她一恍就觉得世界好像颠倒过来。
对面那是红灯还是已经变换了绿灯?
身边的行人纷纷扰扰,她头重脚轻,意识渐渐有些模糊,只想过了马路,过了马路再说。她凭直觉慢腾腾的走过去。
身边的行人越来越少,她心里急头就更晕。
忽然不知道哪里传来一声尖啸,她吓了一跳就懵了,眯着眼寻找声音的来源。四下变得很嘈杂,人群的尖叫生,汽车的汽笛声……昏眩像海浪一样袭来,狠狠地砸在她身上,最后除了黑暗一片,再无知觉。
老李见笑柔走了,言方站在车边,脸色阴沉得难看,于是小心翼翼地说:“曹秘书说,所有的股东都来齐了,净差您了。”
“嗯,我们现在就回去。”
“那赵小姐呢。”
言方最后看了一眼她远去的背影:“她会没事的。”
他总相信她会没事的,他以为她能从美国回来,迢迢山水,浩瀚的太平洋,她可以回来,就一定会没事。
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心安竟然让她独自离去,明明看见她苍白的脸色,明明看见她磅礴的泪水。
曹舒芮在会议室外焦急的徘徊却不知道是否进去,而言方此时也在里面心神不宁,幻灯片下说得激情四溢的人变成一出无声的默剧,那副幕板时快时慢地变换着什么他一点也没看进去。熄了灯的会议室黑暗得像洪水一样将他包围,那边唯一亮着的好像是出口,那么远又那么近。
曹舒芮最终没能忍住,她悄无声息地进入会议室走到言方身边,低□用仅以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言总,笑柔出了车祸。”
仿佛一根尖锐的钢针狠狠地从头颅穿透过去,他蓦然站起来:“你说什么?”他这一声极大,会议室里的人纷纷看过来。他顾不了这么多,霍地站起来风驰电掣般从会议室里跑出去。
他慌了神,电梯没在他所在的楼层,他拼命的按,脑袋里一片空白,车祸是个怎样的概念?他开始害怕,悔不该让她自己走,她那伤心欲绝的样子,泪眼婆娑,字字铮铮地说她没有幸福了,一遍遍在他眼前回放。
一个由心底已经绝望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他不敢想,他逼自己不去想,只恨不得这电梯能快一些,再快一些。
Chapter 42
外面一直在下雨,雨水不停打在窗户上,刷刷的响。隔着厚实的玻璃窗,像病房这种被层层围裹住的密室空间,里面的寂静反倒衬托了雨声的清晰,它像洪流一样,传进来的声音变得模糊,好像有啸声,拼命要冲垮了防堤,崩溃瓦解。
笑柔醒过来了,睁开眼首先入帘的是灰暗的天花板。
病房里只开着昏暗的床头灯,窗帘密实地遮住窗户,不留一丝缝隙,不知此时是白天黑夜。
掉瓶悬在床头的挂钩上,盐水一滴一滴,缓慢地从导管输入血液中。
她脑袋刺刺的疼,还在拼命回忆自己怎么在这里。
这个病房再熟悉不过了,第一次来是因为学校剪彩,单薄的身子抵不过萧瑟的寒风,歪了脚后祸不单行染了风寒,是言方送她过来的;第二次是去县城的前一天晚上,她冒着瓢盆大雨从妈妈那边回来,发了烧,昏迷得不醒人事,也是言方送她过来的。
而这一次……她好像是看见有辆汽车飞速地向自己驶过来,但她明明是看见绿灯才过马路。眼看车子即要撞上来的一刹那,忽然脑袋像压了百斤重的石头,天与地在翻转,世界在混淆。
她还没弄清楚了是怎样一回事,病房被咔的一声推开。她下意识地抬头,心中猛然一紧。
病房太小,她软弱无力,无处可逃。
言方看起来很疲惫,颔下的胡须渣子像雨后春笋一样钻出来,他脸色低沉,像凝了厚厚的一层霜,如深渊得湖水一样冰冷。
他慢慢地走过去,在与病床对着的沙发上坐下,双手支着额。笑柔艰难地转过头去,他半侧身子陷在暗里,脸埋在手中,什么都看不真切。
她一下记起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是车祸?又好像不是,最后的记忆停留在自己在马路上。
半晌,病房里的沉默叫人害怕。她动辄了一下,言方闻见声响,见她挣扎着要坐起,便走过去,默默地扶她起来,把枕头竖放在床头,再把滴管置到一边不让她压着。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仔细,那么体贴细腻。
笑柔垂下眸,看着自己瘦骨嶙峋的手背上扎着一枚针,绷带画了个十字紧紧粘住,血管在苍白的几乎透明的肤色下变得显而易见,还有条条青筋,难看地突出来。
“你非要用这样来逼我。”良久,言方终于开口,他筋疲力尽,他已经拿她毫无办法。
笑柔有些恍惚,抬头莫名地看着他。因为消瘦,一双眼睛微微的向内塌陷,变得大而无神,带着凄然的迷茫。言方只和这双眸子对望了一眼便移开眼去:“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你都答应你,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他兀自笑起来:“我真是低估你了,赵笑柔,没想到你这么狠。”
笑柔心里一沉,她完完全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怎……怎么了?”
她喉咙干涸,声音沙哑,一紧张扯动针头,疼得她额上密密泛着冷汗。
“你何必费尽心思去折磨自己,你不用拿自杀来逼迫我。”
“自杀?”她茫然。
言方冷冷的说:“红灯的时候你站在马路中间,难道脑子里还会想着别的事情?”
原来他以为她闹自杀,那两货车飞驰过来的时候她除了天旋地转什么都不记得,后来曹舒芮告诉她,目击者称,那辆货车好像撞到她了,又好像没撞到,她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那么恨,说话的时候咬牙切齿,他一直憎恨别人不择手段的逼迫,笑柔一次又一次挑战他的底线,这一次竟然那么恨,那么决绝。
她笑起来:“你以为我是自杀?”
—文—言方撇过头不看她,他怕那双凄凉的眸子,掺着无底的绝望一点点往她心里渗。
—人—笑柔缓缓闭上眼:“你要是这么认为就这么认为吧,我没有想过再逼你,你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她真的是这么想,如若他再要她走,那就永生也不要再回来了。
—书—“我待你太好,想不到你这么不珍惜自己,你这样还不到任何人。”
—屋—“珍惜自己?呵。”她想笑却笑不出声,眼泪噙在眼角又落不下来,整个人像被捆着吊起来,难受之极,“是啊,我恨那一下为什么不把我撞死去,死了一了百了,火一烧灰一把埋了撒了悉随尊便。”
言方这下真被她激怒了,伸手狠狠将桌上的东西拂倒,一阵刺耳的嘈杂落得一地狼藉。他从来没有那么生气,发怒成这样,用摔东西去发泄。笑柔一直闭着眼睛,笑得比哭难看,她没敢看他愤怒的脸色,也没有看他离去的身影,只听见门狠狠地砸在门框上,撞击之大仿佛这病房也震了三震。
刚才好像听见他说,答应她,什么都答应她了。
曹舒芮一直在医院照顾笑柔,两人没有太多的对话,笑柔甚少进食,终日望着窗外的银杏树出神,到了五月,阳光从茂盛的银杏枝叶丛中照射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