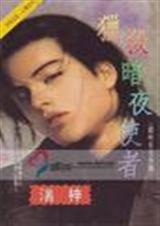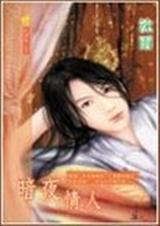暗夜吻别-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大大吓了一跳,吓醒了,脱口叫出来说:“织田操?”
“哼!”织田操非常不满地粗声说:“我这么大一个人站在这里,你居然没看到,还把我当成电线杆,简直太混蛋了。”
“这里这么暗,我又没戴眼镜,胃又难受得要命,一直想吐,哪注意到那么多!”杜小夜委屈地解释。
“尽管如此,你也不能把我当电线杆!”织田操蛮不讲理,霸道说:“看看你,浑身酒臭,你没事喝那么多酒做什么?”
“没办法啊,大家都喝——唔——”
话来不及说完,杜小夜连忙掩着嘴冲到一旁,又吐得一塌糊涂,粘了一身酸臭的残液和味道。
“不要在这里呕吐,脏死了!”织田操极不客气地批评她。
这是他的劣根性,只要有谁惹他生气,他就毫不在乎地用话刺激对方;更何况,这个怒气,他从傍晚憋到现在。
他将她拎到盥洗台,监视她冲洗干净,见她用衣服擦脸,又存心找碴地用轻蔑的语气说:“不要用衣服擦脸,那看起来很蠢!你不带手帕的吗?连这种东西都不带,还算什么女人!”
带不带手帕,跟是不是女人有什么关系?杜小夜识趣地不跟他顶嘴,提着衣服的下摆,呐呐说:“不能用衣服擦,那该怎么办?我又没有带那个……手帕……”
她知道织田操是藉题迁怒,他还在为下午的事生气,这种时候最好不要再惹他,乖乖听他的话。
“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织田操不耐烦地大声吼叫,心浮气躁。
他有理由这么生气的。这混蛋家伙,拿他赌钱下注,居然赌他输球!而且他要她解释的时候,她居然躲他,还回了他浑身的沙;而后他等了她一夜,她没看到他也就算了,教人忍无可忍的是,她竟然当他是一柱电线杆!简直——简直——
“混蛋!”他愈想愈气愈懊恼,冲着她的脸破口大骂。
正偷偷用袖子擦脸的杜小夜,被他突然没头没脑骂了一脸,不由得偏过脸庞,闭紧双眼。
“跟我来!”他气消了一些,拉着她往海滩走去。
“喂!这么晚了!你拉我到海滩去做什么……”呼喝的叫声,一下子就被迎面的风吞噬掉。
“少废话,跟我走就是!”
“可是……”
“你再啰嗦,我就缝住你的嘴!”
织田操粗声粗气地咆哮威胁。夜色太黑,杜小夜看不清他的脸,但她可以想见,此刻他脸上那种难看的表情,两道剑眉一定又在打结。
他走得又急又快,她跟不上他的脚步,一路被拖着小跑,时时被自己的脚绊到。下到海滩,脚下的沙粒松暖又柔软,她一时没有留意,被织田操拖着的脚步深深一踩,陷进沙堆里,趴倒在沙滩上。
“你怎么这么蠢,连路都不会走!”织田操不但不扶她还在一旁风言凉语拐弯地骂她。
但看她狼狈的样子,他的心情似乎又变好了一些。他憋了一晚上一肚子的闷气,可不许她这个混蛋家伙心情太快活。总之,他心情不好,他也不许她太快乐。
“快点起来!拖拖拉拉的做什么?我可没那闲功夫在这里等你这个笨蛋!”他还是口不择言地胡乱骂她,不过,口气不再那么粗蛮了,也少了很多火药味。
杜小夜讪讪地爬起来。她不敢回嘴,一回嘴就完蛋了,又要惹织田操生气,最后倒楣的还是她。
他们的关系实在非常莫名其妙。从他莫名其妙地踢她屁股一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话片面宣布她是他的“女人”,一切就变得愈来愈莫名其妙。他理所当然地“主宰”她,以她的“男朋友”自居;她理所当然地被他牵绊着,愈来愈难以否认,然后,他们的关系就愈来愈“理所当然”和莫名其妙。
而他对她的任何态度——不管是蛮横、无礼、傲慢,或者粗声恶气和自以为是,似乎都显得那么天经地义、理直气壮。偏偏她又无法抵制他,被他的蛮横霸道克得死死的。
“你带我到这里做什么?我明天还要工作……”织田操拉着她,一直往海滩外走去。潮声愈来愈近,她口气愈显得犹豫和迟疑不进。
夜早深沉,整个海滩暗得如此际的海潮,广漠而没有灯光。星斗稀疏,天地共一色的沉静,白日的喧嚣人语随着热气的蒸发早已灭寂,除了海水的潮骚,整个海滩只剩下偶尔的风吹细响。
夜,沉淀到色彩的最底层;黑暗让此刻的世界神秘颤动地宛如浑沌初开。
“喂!你到底要做什么?”织田操一直不说话,只是拉着她一径往海水处接近,她不禁提高声音,压抑不住几分急躁与不安。
“你不会看吗?当然是游泳!”
织田操回头皱她一眼,眉毛果然还在打结。他脱掉背心,抓住她的手腕拉她下水,她惊叫一声,拼命抵抗,死不肯就范,固执得像头牛立在原地,惹得织田操蛮性大发,硬是要将她抱下水。
四周没有借力可供她攀凭,织田操力气又大,她像条牛一样,被他用力地一直拖到水边。
“不要!我不要下去!我不会游泳啊!”她害怕得失声大叫起来。
“什么?”织田操愣了一下,回头不相信地望着她。
“我怕水,不会游泳,这样行不行?”她涨红脸,心有余悸,甩开他的手,往海滩上方退了好几步,离海水远一些,才安心下来。
织田操回头又看看她,又转头看看海面,再回头看她——他简直不敢相信,她这么大的人了,居然不会游泳,而且还害怕接近水!想想他十岁就挑战遍各种海上活动,举凡滑水、冲浪、潜水,亦或帆船、风浪板,无一不精,就连独木舟也难不倒他,而这混蛋家伙,居然——居然——是个对水有恐惧症的运动大白痴!
他不禁大大地摇头,朝她逼近两步。
“你想干什么?”她立刻竖起身上的刺,戒慎防备,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他不理她的嚷嚷,一直逼到她跟前才停下来。
“难怪这整个礼拜,你总是将自己包得像个肉粽,从没见你沾过一滴海水。”他总算恍然大悟,过去一个星期她为何总是离海水远远的,绝不受任何蔚蓝的诱惑。
“你一直在监视我?”她大吃一惊,退开一步,随即甩甩头。
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打从在海边再相遇,每天收了工,他就理直气壮地逼她看他冲浪,看得她头昏脑胀,他当然也看透她的习惯。她怀疑,他是不是打算什么都不做、整个夏天就耗在海边,和那群联合国小子比赛谁能冲破最大的浪。
有钱人家的大少爷就是这样,整天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她看他每天除了游泳、冲浪、潜水和玩帆船,就没做过什么有建树的事情。
风声呼呼的,热带海洋吹来热情的回响。织田操突然靠近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眼光古怪,而且有点坏。
“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杜小夜防贼一样,对他带着怀疑。虽然她是大近视,但还不至于离谱到将织田操眼中的古怪看成含情脉脉。她敢打赌,他一定又在想什么用花样了。
她暗忖着偷偷溜开,才刚起念,织田操蓦地猛然抱住她,将她压倒在沙滩上。她没料到会是这样,吓了一跳,本能地抵抗挣扎,两人扭成一团,在沙滩上翻滚。
“放开我!你想干什么……神经病!”她边挣扎边诅咒。
对她的叫骂,织田操充耳不闻,很快就将她制服,将她压在他身子底下。
“我一直想试试看,这样将女人压倒在身体下会是怎样的感觉——”他一本正经地望着她因羞赧愤怒而涨红的脸。
“神经病!”她又啐了他一声。羞恼说:“你怎么可以随便将别人压在身体下!你懂不懂什么叫礼貌和尊重?!”
“我只管我想做的事。”织田操蛮不讲理地回答。
不管什么事,只要他想做的,他一定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他才不管她答不答应,总是强迫她屈服。
“你——”杜小夜又羞又气,又恼又怒,偏偏就是拿他没办法。他天生是她的克星。她气恼说:“你知不知道你很重,会将人压扁的,还不快起来!”
事情一开始,本来就很莫名其妙,所以现在不管发生什么莫名其妙的事,她也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反应过度了。
不过,害羞是正常的,气恼也是必要的,她不可能将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当成是正常的事,陪着织田操一起发神经。
“这感觉满舒服的,我再耽一会。”织田操索性将脸凑到她脸旁。“你如果再多长一点肉就好了,感觉更舒服,但我看你大概只有身高在发育。”
“要你管——莫名其妙!”杜小夜困难地挣出手想推开他。“就算我只有身高在发育,总比你乳臭未干来得好。怎么说,你都不会比我大,充其量不过是个毛头小子!”
“男人的成熟度是不必和年龄成正比的——”织田操想证明什么似的提高声调。但他还是沉不住气地问说:“就算你比我大也大不了多少。你几月生的?”
“你又是什么时候生的?”杜小夜反问。
织田操瞪着她看一会,才很不甘心地说出来。居然和她同月同日生,她足足比他大了一岁。
“哈!我会走路的时候,你还在你妈的怀里吃奶呢!小弟弟——”她得意万分地嘲弄他。在他面前,第一次能将姿态摆得那么高,心情痛快极了。
织田操两道浓浓的剑眉又打结了,对她的“得意忘形”显得十分气恼,恼羞成怒,瞪着眼,语带蛮横地威胁她说:“有什么好得意的?你再笑,我就将你的嘴巴堵起来!”
他可不认为她比他大个几个月——就算大他一岁好了——就能成什么气候。偏偏她一副得意装大的模样,教他看了就有气。如果她以为“年龄”可以当做压制他的筹码,那她就大错特错!他从来不吃那一套,更别说她只不过比他大不了几个月——呃,大不了一岁——罢了。
“你何必恼羞成怒,我只是说出事实罢了。”杜小夜嘟囔着小声抗议,但显得气壮理直。
织田操那么蛮横霸道,也唯有这点“事实”才能稍微压抑下他的气焰——虽然这实在是很无聊又没什么意义的举动,而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