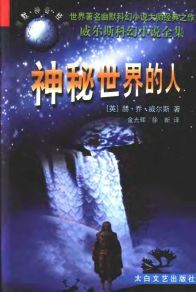世界悬疑经典小说-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霸不成?难道我们不是上帝您的骨肉?孰……孰知意志之玄妙及其威力哉?凡人若无意志薄弱之缺陷,决不臣服天使,亦不屈从死神。”
这时她仿佛发泄了满腔怨愤,累坏了,两条雪白的胳膊刷地放下,一脸严肃,回到床上等死了。弥留之际,嘴里还喃喃有词。我弯下腰,凑着耳朵一听,原来又是葛兰维尔那节文章中的最后一句:“凡人若无意志薄弱之缺陷,决不臣服天使,亦不屈从死神。”
她去世了——我难过得肠断肝裂,再也不堪独居在莱茵河畔那阴沉的破城里。我倒不缺世人所谓的财富。丽姬娅给我带来的财富,远比凡人通常注定享有的还多,要多得多呢。因此,我疲惫地辗转漂泊了两三个月,终于在风光绮丽的英国一个人烟稀少的荒芜地方,买下座寺院,修葺了一番。寺名不提了。我万念俱灰,才到了这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这座满目苍凉的堂皇巨厦,这片荒凉的庄院,还有不少跟巨厦和庄院有关的、素有来历的凄恻纪念品,倒跟我万念俱灰的心情很相配。寺院外部虽然面目未改,一片绿阴凋零残颓,可我好似孩子一样任性,或许暗怀一线希望,但愿减轻心头的悲伤,竟大事铺张,把屋内布置得比王府还华丽。这种傻事,在童年就已经养成癖好,如今仿佛活到凄凉的晚年,竟又重新干起来了。天呐,看看光怪陆离的花幔、庄严的埃及雕刻、怪诞的壁沿和家具、图案杂乱的金丝地毯,我觉得连初期疯病的症状都可以看出不少呢!我早就成了瘾君子,无论工作和习惯都透着鸦片梦境的特色。但决不能掉转笔头来细述这种荒唐的事。还是光谈谈一间鬼房间吧。当初我一时神经错乱,在圣坛前拜了堂,领着特瑞缅因那位碧眼秀发的罗维娜·特瑞梵侬小姐,当做新娘,当做萦绕我心头的丽姬娅的替身,就走到了那间卧房里。
眼下,新房中的构造和陈设无不历历在目。新娘的娘家势利成性,贪图金钱,竟听任这么可爱的一位姑娘,一位千金踏进如此装饰的房里,他们的骨气何在?上文刚谈过,房里的一切细节,我都丝毫不漏地记在心头,可我对重要大事却伤心得忘怀了;那种异想天开的布置一点没次序,一点不调和,哪会留下什么印象。这间房在城堡式的寺院中一个巍巍塔楼上,成五角形,很宽敞。朝南那面开着一扇窗子——偌大一块威尼斯不碎玻璃——只有一个窗框,漆成青灰色,阳光和月光透过窗子射进来,照得房里一切物件都蒙上了阴森森的光。这扇大窗的上半部搭出个花架,盘着老葡萄藤,缘着塔楼的巨墙往上爬。死气沉沉的橡木天花板,其高无比,构成拱形,精工描绘回纹图案,又是哥特式,又是德洛伊式(德洛伊,指上古时代高卢人与不列颠人中一种能妖术、会预言的德洛伊教教徒。其图案花样作五点状。),真是稀奇古怪,荒诞绝伦。这苍凉的穹隆正中心,垂下一根长环金链,挂着偌大一只撒拉森式(撒拉森,原指叙利亚与阿拉伯间沙漠中的游牧人,后又指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金香炉,千镂万孔的、五彩的火花灵若蟒蛇,川流不息地在炉孔里穿进穿出。
四处放着几张长榻,几座金烛台,一律都是东方式样。还有一张印度式卧榻——合欢床——低低的,实心乌木上雕着花纹,挂着一顶棺套似的床帐。卧房四角各竖一口硕大无朋的黑花岗石棺材,全是从卢克索(卢克索,中埃及尼罗河畔城市,以狮身人面像、方尖碑等古迹著称。)对面的皇陵中挖掘出来的,古旧的棺盖上雕满不知何年何月刻下的花纹。可天呐!最最怪诞的就数房里的帷幔。巍峨的四壁真是高不可攀,甚至高得不相称,从顶到脚,重重叠叠地挂着巨幅沉甸甸的帐幔——帐幔的料子看来就跟地毯、床帐、长榻的套子、乌木床的罩单、半遮着窗户的罗纹花窗帘一模一样。全是华贵无比的金布,一团一团的布满阿拉伯式的图案(阿拉伯人崇尚的一种壁饰图案,以树枝、树叶以及漩涡交织一起,称为蔓藤花纹。),或远或近的,每团直径约莫一英尺光景,在布上形成漆黑的花样。但只有从一个角度望去,才带着几分真正的阿拉伯式花样。经过一番设计(这种设计目前流行世上,其实太古时代就有了),这些图案便显得变化无穷。刚踏进房,只觉得奇形怪状;可往前走几步,这副怪样渐渐消失;在房里东转西转,就逐渐看到四下川流不息的都是鬼影,或是诺曼底人迷信的传说里的那一种,或是出家人邪梦中出现的那一种。帷幔后面不断猛烈地吹过一阵阵风,幻影幢幢的感觉就此骤增十倍——房里一切也就平添一种可怕的、不安的活力。
在这类厅堂里——在这种新房中——我和特瑞缅因那位小姐度过了蜜月,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我不由看出妻子就怕我这种喜怒无常的脾气——看出她躲开我,简直不爱我;可我心里反倒高兴。我把她恨得咬牙切齿,这愤恨只有妖怪才有。我霎时想到了丽姬娅,我的亲人,我的天仙,我的美女,我的亡妻,唉,心头这分惋惜不必提有多大了!我出神追忆她的纯洁,她的智慧,她的至高无上的神妙性格,她的如胶似漆的火热痴情。于是无所顾虑地燃着满腔熊熊情火,比她还炽烈呢。在吞了鸦片后的乱梦中(因为我吸毒成瘾了),我会出声呼唤她的名字,或者在万籁俱寂的晚上,或者白天,在隐蔽的幽谷山坳里,仿佛只要我心痒难抓地、热情如焚地诚意怀念亡妻,就好使她重新回到早已抛弃的人生道路上——唉,能永远如此吗?
约莫在婚后第二个月的月初,罗维娜小姐突然病倒了,一病就病了好久。高烧摧毁了健康,害得她夜不成眠;在半睡半醒的不安心情中,她谈到塔楼上这间卧房里的声音和动静。我断定这无非是她胡思乱想的缘故,要不恐怕是房里那幻影横生的感染力的影响。她终于渐渐复原——到底痊愈了。谁知没过多久,又病了,这次病得更凶,缠绵病榻了;她身体素来虚弱,这次病后,从此毫无起色。过了这个时期,病势可真严重,旧病复发,就分外严重,医生用尽一切医道,使出浑身解数,怎么也治不好。这慢性病愈来愈严重,分明就此牢牢缠住她,人力挽回不了啦,我便看出她那急躁不安的脾气,也愈来愈厉害;碰到些微小事,就吓得要命,这种动辄激动的情绪也愈来愈厉害了。她早先提过帐幔间有声音——轻微的声音——异常的动静,如今又谈到了,而且谈得益发频繁,益发执拗。
九月末梢,一天晚上,她格外强调这一烦心问题,引起我的注意。她刚从乱梦中醒来,我看着她那瘦脸抽搐个不停,心里又是焦急,又是隐隐恐惧。我靠近她那张乌木床,坐在一张印度式的长榻上。她半欠起身,认真地低声谈到当时听到的声音,可我听不到——谈到当时看见的动静,可我看不出。帐幔后面飒飒吹过风,我真想告诉她,那简直听不大清的声息,墙上那几乎没有变化的影子,无非是风一直飒飒吹过而引起的,但老实说吧,这连我自己也不敢全信呢。话说回来,眼见她脸上一片死白,心里就有数,尽管千方百计地想安她心,结果还是落空。看模样她快晕过去了,可身边又没个仆从好使唤。我想起卧房那头放着医生规定喝的一瓶淡酒,就三脚两步地走去取来。谁知刚到香炉光下,竟有两件惊人的事不由我不注意。只觉得身边轻轻走过什么看不清但又感觉得到的东西;眼里还看到香炉里射下熠亮灯光,正中金黄地毯上有个影子——貌似天仙的模糊淡影——这种影子可能给当作幻影。可是,我吞了过多的鸦片,醉得晕头转向,对这种事简直置之不顾,也没有告诉罗维娜。我找到了酒,重新回到卧房这头,斟了一杯,凑到这位人事不省的小姐嘴边。如今她倒有点苏醒了,伸手拿了杯子,我便倒身坐在附近一张长榻上,眼睁睁地看着她。就在这时,耳边分明听到睡榻附近地毯上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转眼工夫,罗维娜正将酒杯举到嘴边,我猛然瞅见三四滴亮晶晶的、红艳艳的流汁仿佛从房内半空中什么无形的泉源里流出来,洒进了酒杯;要不也许是我做梦吧。如果我看到的话——罗维娜可没瞅见。她毫不犹豫,将酒一口喝干,我忍住了,没把这事说出口,照我看,归根结蒂,无非是因为眼见罗维娜小姐吓得要命,再则吞了鸦片,三则时间又在晚上,幻想力就非常活跃,幻想丰富了,就势必引起这种联想。
可我没法蒙过自己的眼睛,就在那几滴红液洒进了酒杯之时,妻子的病情突然一下子恶化了;到第三天夜晚,奴婢准备给她下葬了,到第四天,剩下我一个人,陪着她那裹衾的尸体,坐在怪异的卧房里,我和她的新房里。——面前展出一片荒诞的幻景,吞了鸦片才有的幻景,忽隐忽现,影影绰绰。我眼花缭乱,凝视房内四角那四口石棺,凝视帷幔上那变幻无常的图案,凝视头顶上那只香炉中穿进穿出的五色火舌。一想到前几天晚上的事,眼光不由落在香炉光下那个地方。当初我在那儿见过朦胧影子,可如今不见了。我舒舒畅畅地吸着气,朝床上那苍白的、僵硬的死尸看去。于是丽姬娅的无数事迹忽然一一浮现——转眼间,势如山洪暴发,心头重新涌现当初看她这么裹着寿衾而涌起的那股说不出的悲哀。夜尽了;我仍然怔怔望着罗维娜的尸体,照旧满腔辛酸地想着深深迷恋的唯一亲人。
大约到了深夜,可能早一点,也可能晚一点,我可没留心时间,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呜咽,低低的,柔柔的,但又清清楚楚,我不由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只觉得从乌木床上传来——从罗维娜临终那张床上传来。我不禁迷信起来,害怕得要死地听着——谁知再也没听到第二声。我睁大眼睛,看看尸体有没动静——谁知一点也看不出。可不见得是错觉。不管声音多轻,到底听见过,何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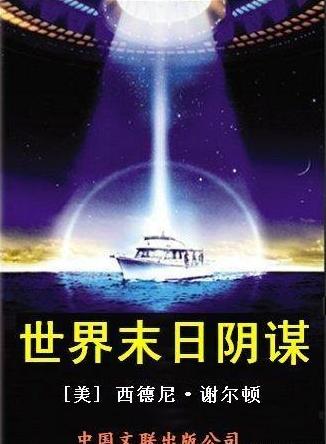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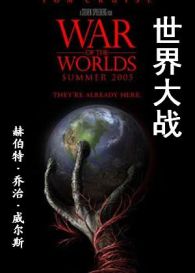

![[综漫]炸裂吧,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