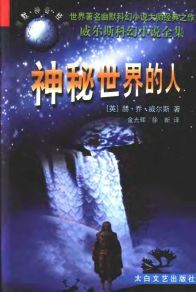世界悬疑经典小说-第1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的,我知道。”
“我正想找个房间住下。”
“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亲爱的。”她说道。她有一个红润的圆脸和一双极其温柔的蓝眼睛。
“我正准备去龙钟旅馆,”比利对她说,“但你窗户里的启事吸引了我。”
“亲爱的孩子,”她说,“你干吗不从冷空气里走到屋子里来?”
“你收多少房钱?”
“住一夜五先令六便士,包括早餐。”
简直太便宜了,还不到他想象的一半。
“你要是嫌太贵,”她补充道,“那么我可以稍微少要一点,你早上要鸡蛋吗?眼下鸡蛋很贵,你要是不吃鸡蛋,就可以少收六便士。”
“就五先令六便士好了,”他答道,“我很想在这里住下。”
“我知道你会住下的,请进吧。”
她看上去非常和蔼,就像一个最要好的同学的妈妈欢迎你到她家去过圣诞节。比利脱下帽子,迈进了门槛。
“就挂在这儿吧,”她说,“把大衣给我吧。”
在过厅里没有别的帽子或大衣挂在那儿,没有雨伞,没有手杖——什么也没有。
“就咱们两个人,”她说着。她领他上楼时,回过头来向他微微一笑。“你知道,我不是常常有幸把客人带到我这个小小的窝里来的。”
老太太有点儿疯疯癫癫的,比利心想。不过五先令六便士一夜这个价,谁还在乎那个?“我认为投宿的人会多得使你简直应接不暇的。”他客气地说。
“啊,是的,亲爱的,是的,当然是的。但问题是我有那么点儿挑剔、苛求——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啊,明白。”
“但是我总是事先准备好,这所屋子里的一切都是日夜放在这里,以备万一会出现一个合意的年轻先生。每当我有时打开门,看见门外站着一个正合我意的人时,我是多么愉快啊。亲爱的,这是多么巨大的愉快啊!”上到楼梯的半中间时,她一只手扶着栏杆停了下来,转过头,苍白的嘴唇向跟在后面的他微微一笑。“就像你这样的人,”她补充道,一双蓝色的眼睛慢慢地从头扫过他的全身,一直看到脚,然后又从脚看到头。
在二楼的楼梯口上,她对他说:“这层楼我住。”
他们又上了一层楼。“这一层楼全归你住,”她说,“你的房间在这里,我真希望你喜欢它。”她把他领进了一间小小的然而很可爱的临街的房间,进门时顺手打开了电灯。
“早晨,太阳光从窗子直射进来,珀金斯先生。你是叫珀金斯先生,对吧?”
“不,”他说,“叫威弗尔。”
“威弗尔先生,真好听。我在你被子里放了一个热水袋给你烘一烘,威弗尔先生。你不认为在铺着干干净净的被褥的一张陌生的床上睡觉,有个热水袋是个极大的安慰吗?你如果觉得冷,随时可以点上煤气。”
“谢谢你,”比利说,“非常非常感谢你。”他注意到床罩已经揭开,被子的一侧被整齐地掀起,就等着有人钻进去睡觉了。
“你来了我真高兴。”她热切地看着他的脸,说道,“我都开始担心了。”
“没事,”比利欢快地说道,“你别为我担心。”他把箱子放在椅子上,打开它。
“吃晚饭吗,亲爱的?到这儿来之前你搞到东西吃了吗?”
“我一点也不饿,谢谢你。”他说,“我想尽快上床睡觉,因为明天我得早起到公司去报到。”
“那好吧,我走了。你最好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不过你上床以前,能不能费心到楼下客厅去填一下住宿登记表?法律规定人人都得填,咱们在这个时期可不想干犯法的事,对吧?”
她向他微微一挥手,迅速走出去,关上了门。
看来女房东有点精神失常,不过这丝毫也没有使比利不安。反正她不仅毫无危害——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很明显心肠很好。他猜想她很可能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或者是有过类似的遭遇,一直没能从这个打击中解脱出来。
就这样,几分钟后,当他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洗过手之后,便匆匆下楼走进了客厅。女房东没在客厅里,但壁炉中炉火熊熊,那只德国种小猎狗仍在炉前睡着。房间里暖洋洋的,使人感到十分舒服。我可真走运,他搓着双手,心想,这儿可真不错。
他见住宿登记簿打开放在钢琴上,因此就拿出钢笔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在这一页上,他的名字前面只有两个人登记过,就像人们看见旅客登记簿时常做的那样,他读起前面的登记来。其中一个叫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从加的夫来的;另一个是从布里斯托尔来的格里高利·坦普尔。
真奇怪,他突然想到,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这名字有点熟。
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颇为不常见的名字的呢?
是小学的一个同学吗?不是。是他姐姐众多的男朋友中的一个吗?也许是的。也可能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不是,不是,都不是。他又一次看了看登记簿。
克里斯托弗·穆尔荷兰
加的夫市大教堂路二三一号
格里高利·坦普尔
布里斯托尔市梧桐大道二十七号
事实上,细想起来,第二个名字好像也和头一个名字一样很耳熟。
“格里高利·坦普尔?”他念出声来,拼命地回想,“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
“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在他背后一个声音答道。他回头看见女房东手里端着放茶点的托盘飘然走进房内,她把托盘高高地端在手中,好像托盘是勒在一匹欢跃着的马身上的缰绳。
“不知怎么这两个名字很耳熟,”他说。
“是吗?太有意思了。”
“我几乎可以肯定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两个名字。你说怪不怪?也许是在报上见到过,他们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吧,是吗?我是说有名的板球手啦,或足球队员之类的。”
“有名人物,”她把托盘放在沙发前的一张矮茶几上,说道,“啊,不,我想他们不是什么有名人物。可是他们长得非常漂亮,两个人都很漂亮,这点我可以肯定。他们个子高高的,年轻、漂亮,亲爱的,和你完全一样。”
比利再一次低头看着登记簿。“嘿,我说,”他注意到了上面的日期,说道,“最后一个登记的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是吗?”
“是的,确实这样。而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是在这之前几乎一年之久——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
“哎呀!”她说道,一面摇着头,一面轻叹了一声。“你要不说,我是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间真是一晃就从我们身边过去了,真快,不是吗,威尔金斯先生?”
“我的名字是威弗尔,”比利说,“w—e—a—v—e—r。”
“啊,当然是这样!”她往沙发上一坐,大声说道。“我真笨,我向你道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就是这个样子,威弗尔先生。”
“你知道吗,”比利说,“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十分离奇的地方吗?”
“亲爱的,我不知道。”
“嗯,你看——这两个名字,穆尔荷兰和坦普尔,我不但好像记得,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名字还似乎有那么点儿奇怪的联系。就好像两个人因为同样的什么事出的名似的,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就像……嗯……就像,比方说,像邓普西和突尼(邓普西(william h。dempsey)和突尼(james j。tunnney)均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著名拳王。),或者像邱吉尔和罗斯福。”
“真有趣,”她说,“现在你到这边来吧,亲爱的,挨着我坐在沙发上,你喝杯好茶,吃块姜汁饼干,再去睡觉。”
“你真的不该这么费心,”比利说,“我并没有想让你这么费心。”他站在钢琴旁,看着她张罗着茶杯茶碟。他注意到她有一双白皙、小巧、动作灵活的手,涂着红指甲。
“几乎可以肯定我是在报上看到他们的名字的,”比利说,“我马上就会想起来的,一定会的。”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似乎记得可又记不起来更让人着急的了。他不愿意丢开不想。
“咳,等一等,”他说,“稍等一等,穆尔荷兰……克利斯托弗·穆尔荷兰……这不就是伊顿公学那个学生的名字吗?他在西部徒步旅行,可突然……”
“要加牛奶吗?”她问道,“要糖吗?”
“要。可突然……”
“伊顿公学的学生?”她问道,“啊,不是的,亲爱的,不可能是这样,因为我的那位穆尔荷兰先生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肯定不是伊顿公学的学生,他是剑桥大学的学生。过来坐在我旁边,在这可爱的火前暖和暖和。快来呀,你的茶点全都准备好了。”她拍拍身边沙发上的空位子,向比利微微笑着,等着他到她身边来。
他慢步走过房间,在沙发边上坐了下来。她把他的茶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好啦,”她说道,“多好,又舒服又暖和,是吧?”
比利小口喝着茶,她也一样。约有半分钟左右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但是比利知道她在打量着自己,她的身子半朝着他,他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越过茶杯沿看着他。他不时地闻到一丝好像直接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奇怪的气味,这气味一点也不令人讨厌,而且使他想到——咳,他也说不清这气味让他想起了什么。是腌核桃仁?新鞣出的皮子?还是医院走廊里的气味?
“穆尔荷兰先生是个喝茶大王,”良久她又说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人像亲爱的、可爱的穆尔荷兰先生那样喝那么多的茶。”
“我想他不久前才离开这儿的吧,”比利说,脑子里还在琢磨着那两个名字。现在他敢肯定自己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两个名字的——是在报纸的大标题上看到的。
“离开了?”她弯起眉毛说道,“可是亲爱的孩子,他根本没有离开,他还在这儿,坦普尔先生也在这儿,他们在三楼,两个人在一起。”
比利慢慢地把茶杯放在桌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女房东。她报以微笑,然后伸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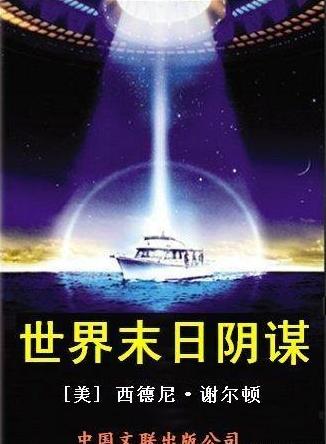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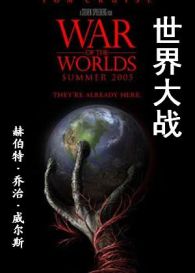

![[综漫]炸裂吧,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