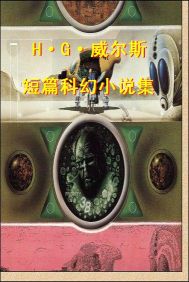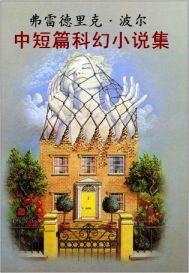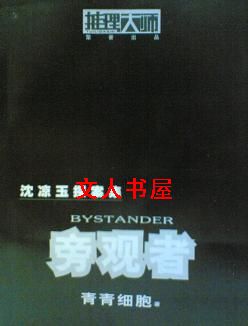王小波全集-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科的学者所做的一样,大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客观地报告。一个发现一经报道,就与研究者没有关系。它的正确与否,自有实践和别人来检定。专业作者只求别人知道他的发现,却不肯做努力去感动别人,震撼别人。发现的正确与否,与读者的情绪无关。这种着眼点的区别,读者在读了李博士的书后自会有所体会。
李博士的某些研究中,使用了社会统计学较新的方法,比如随机抽样、LOG…LINEAR、LOGIT模型等。如今的读者在科学修养方面,已有很大提高。社会学方面的读者,这些知识自应掌握。而其他专业的读者,也不至于不能理解。因为作者相信,概率统计作为各学科的通用工具,已被很多人掌握。
在她的另一些研究中,采用了个案调查的方法。我国一位老一代社会学家说,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因为人在社会上,有出生,有死亡,有婚丧嫁娶,有前因有后果,完全可以自圆其说。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可以互相了解,这就需要对各种文化给予不带偏见的完整说法。这也是所有的读者都爱看的。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又有不同之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社会,大家都在其中生活。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只有少数专业人士能够触及,而是人人有份。人对于人的认识,容易带有偏见。比如自我中心、文化中心主义等等。
我国的社会学,师承自现代人类学鼻祖马林诺夫斯基。遥想马翁当年,提倡走出书房,到天涯海角,跳出主流文化的圈子,那是何等的胸襟。人类是一个整体,是所有的人,大多数的人不等于人类全体。但是我们所知的往往只是我们所处的文化,和我们一样的人,并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看成|人类全体。这样的看法是不完全的。当年孟夫子说: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种说法把某些人视为非人动物,实在有失公允。
李银河博士的书中,对于在Xing爱婚姻等方面处于非主流文化中的人给予一定的重视。比如对于自愿不育者、同性恋者、独身者、离婚者等,都有专章述及。这绝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对上述人士的做法表示同意,而是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一贯态度。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所谓推己及人之说,于是中国人仿佛只有一种文化,所有的人只有一种行为方式。其实不同的亚文化始终存在,只不过我们一贯对此视而不见而己。
总禁不住要给实证的研究作辩护,其实可能是多余的。在报刊上看到有人抨击不生育文化,说不宜提倡。李博士谈到同性恋文化,要是有人说她提倡同性恋就坏了。社会学研究同性恋文化,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说的文化,属于存在的论域,跟提倡没关系。实证的科学,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不管同性恋可不可提倡,反正它是存在的,因为有人在搞同性恋。假如只研究可提倡的东西,恐怕我们研究的事,大半都属虚无,而眼前发生的事倒大半不知道。
当然这本书里说到的绝不止是同性恋。像择偶标准、浪漫爱、婚姻支付、青春期恋爱等题目,就与更大范围的人有关系。作者的研究对于婚姻Xing爱方面的各种观念、各种亚文化,都给予重视。也希望读者对于除自己所持的观念,所处的文化之外,别人的观念和文化也有所了解。这正是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所希冀于社会的。
《中国人的Xing爱与婚姻》,李银河著,199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最近,蜚声海内外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陆女社会学者李银河博士的一部新著:《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李银河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文化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传统文化的本质,来自于村落。在中国,有一个现象不论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中国农村住得很紧密,起码和外国农村相比是这样。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的事别人都知道,别人的事你也知道。这就是信息共有。如果按人类学里信息学派的意见,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据我所知,李银河当初想用“村社文化”这个说法,但是别人说,“村社”这个词已经有了,不能赋予它新的意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很为李银河丧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说,“村”是什么意思不必解释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这和她要说明的现象很吻合。在村里,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无所不知,又无所不传。所以一个自然村简直就是个人信息的超导体,毫无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什么事别人都知道,所以简直什么事自己都做不了主。这种现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外国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这个感觉相当犀利,但只是感觉而已。罪感当然来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会觉得在他面前是个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觉得有好多人在盯着你,耻感何来呢?如果没有信息共有,耻感文化也无法解释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个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要花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坚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虐狂,实际上又远不是这样——有好日子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
李银河认为,传统观念、宗族意识等等,在现在农村里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为它们保存在个人的头脑里。实际上,它们是保留在村落文化这个半封闭的大匣子里。这也是个有意义的结论。我们知道,在苏格兰有个半封闭的尼斯湖,湖里还有恐龙哪。在中国村落里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学没有合法的权威性。真正有权威的是村落。办事都要按一定规矩办,想问题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这既不是因为古板,也不是因为有族规,而是因为有一大群人盯着你。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更加合乎实情。她描述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你怎么挣钱,别人不管;但你怎么过日子,大伙就要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日子当然难有崭新的过法。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所依据的是在山西、浙江两地的调查。她的见解十分敏锐,遗憾的是实证功夫稍有欠缺。假设她的调查不是在这两地的两三个村子,各百十户人家里,而是在散布在全国的上百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里完成,就更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要求近似扳杠。因为她用的是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第一手资料,面对面交谈,通过翻译都会遭人诟病。人类学的前辈大师米德女士在萨摩亚实地调查多年,只因为听人转述,就遭人耍了。考虑到这种情况,谈了百十户,谈得扎实,也就不错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献里找出个说法,然后在调查里验证一番,而是自己来找说法,到调查里验证,这是非常好的。其实她阐述的现象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北京城里没有村落,但有过胡同、大杂院,有一些人员很少流动的单位。在这些地方,隐私也不多,办个什么私事,也难说全是个人决策。因为这类现象并不陌生,你看了这本书,不会怀疑村落文化的真实性。
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实际上,要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这真是至理名言。据我所知,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在村庄里,这种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是朴素的。作为学者,她不是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那一种,也不是学富五车、旁征博引的那一种。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这种明白会被人看成浅薄也罢。从表面上来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内容,比方说,题目有没有人重视啦,一年发了多少论文啦,写了多少学术专著啦,但是这些在她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