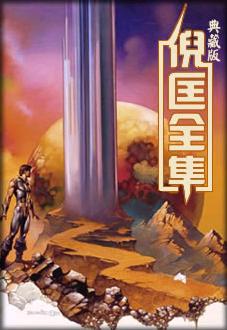迎春花-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人道:“你们还用照镜子?”
“我们就不该翻翻身,享享福?”
“你夫妻俩都有镜子。”
“谁说的?我的在哪?”
“你是你老婆的镜子,你老婆是你的镜子。你们俩对着看看,脸是一个谱,这不是永远打不碎的镜子吗?”人们一想任保和他媳妇的麻脸,响起放鞭炮般的大笑。任保却面不改色,回骂道:“你他妈的混蛋!你老婆样儿俊,脸可没我媳妇的腚片白。”
“那你们两个该把头装裤裆里,不见日头也就白啦!”“真不象话,说些什么!”女人们提抗议了。
任保还是回骂道:“操你妈,爹和你拼了!”
“打架可得往院子跑,还得叫你老婆打着问敢不敢啦,不然没给妈打孩子的拉架。”
又是一阵哄笑。这时曹冷元扛着扁担走过来。春玲对任保说:“镜子放下吧,这是分给冷元大爷的。”“好哇,能给别人我就不能要?小玲子!你个青妇队长多大的官衔,有这末大权力?”任保恼羞成怒,要耍无赖了。
春玲气得眉梢一竖,黑眼睛瞪得象杏子一样圆,理把头发,说:“你别出口伤人!这不是我曹春玲的权力,是村政府!”他从孙若西的手中夺过分配名单,大声读道:“曹冷元,雇农,军属,镜子一个!江任保,你听清没有?”
江任保目瞪口呆,无言对答,越发不讲理地喊道,“啊!你们以军属压人!我江任保穷得要命,你们当干部的眼瞎啦!”
曹冷元忙阻止春玲道:“玲子,咱不要!给人家。”“大爷,你别管。”春玲强硬地激怒地说:“江任保!你说以军属压人,我们就压你。人家军属就该比你……”她本想揭他几句老底,又改了口:“你也该想想,哪次救济少了你任保?这次还没轮到分给你,你就非想多要不可!人家军属就要这个镜子你还有意见,叫大伙评评这个理!”
大家都斥责任保不对。孙若西站在一边,有些吃惊地看着春玲那板紧的红脸。
任保没话再顶,硬充好汉地说:“军属有什么了不起,我参军也不是一次啦,谁叫你们不要?老子明儿再去!”他把镜子向桌上一摔:“给你们军属!”
()
圆镜喀嚓一声,碎成两半了。
在春玲一开始和江任保争执时,妇救会长孙俊英就溜进了厕所。她空蹲了一会,听外面吵声平息了,才煞有介事地提着裤子返回来。
一条桑木扁担,全身呈青灰色,光滑得能映出人的影子。扁担中间,深深地凹下去,只剩很薄的片片了。曹冷元坐在院里的石条上,出神地呆望着它,两只暴出粗筋的紫硬干瘦的手,颤抖着来回抚摸它,渐渐地,从他那干涩的眼眶中,涌出大滴浑浊的泪珠。
老人怎能不激动呵!整整三十个年头,他的生活都是陪伴着这条扁担度过的。三十多年前他自己是个壮实的青年,扁担是条粗糙坚硬的木杠子,在这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冷元的双手把木杠子磨光了,肩膀把扁担中间快要磨透了!这是血肉和硬木的磨擦,是筋骨同木头的搏斗呵!
曹冷元本乡在北面昆嵛山里,父母早亡,他从小当牛倌。二十三岁那年雇到山河村来放牛。日子不久,这个不言不语,干活顶两个人的小伙子,被蒋殿人看上眼,雇到家里当长工。
的确,蒋殿人待长工不错,饭管饱,吃的也不算坏,工资比别人还稍高一点。曹冷元拼死拼活地干,力气又大,引起主人的重视,待他就更好一些。为此,蒋殿人也就辞掉了两个长工。
冷元三十几岁那年,手中有了点积蓄,蒋殿人在西面海阳县过来的一群逃荒的人中,挑了个孤身无依的寡妇,给曹冷元成了亲。冷元也就在山河村落了户。
冷元的妻子时年二十九岁,相貌端庄,性情温淑。虽然冷元把十多年的积蓄花光了,但穷长工能说上这样的好媳妇,真是难得。他心满意足了,更加感激东家,干活越发卖力了。
人愈穷,愈少食缺衣,孩子生得越多。三个年头,冷元妻子就生了三个孩子——一胎是双胞。日子越过越难,工钱哪里够全家糊口的?妻子把孩子丢在家里抓泥,出去讨饭;有时去蒋殿人家洗衣、做饭,赚口吃的。有年冬天,冷元到牟平城为东家粜粮,回来时妻子已死两天了。
她怎么死的?是上吊勒死在梁头上的。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其实也无人去追究原因。反正在那年月,为生活所迫自杀的穷人到处有。但村长蒋殿人为此却不依了曹冷元,说老婆是他逼死的,要绑他上衙门。结果在人们劝解下,蒋殿人毕竟是出了名的好村长,没有把事情闹大。曹冷元就更感恩东家一层了。
妻子死后留下四个孩子,最大的才七岁,最小的出世才一个月的女孩子,妈妈死后不几天就饿死了。曹冷元每天把三个孩子关在家里,自己去给东家干活。在这一带当长工,一年三百六十天几乎没有闲时候,春夏秋农活不用说,大雪纷飞的隆冬,更要忙着上山打柴、搬草。
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冷元越来越苦了。欠东家的债愈来愈多,工资分文也拿不到了。他当长工能在东家吃饭,可孩子呢?老吃糠咽菜,屎都拉不出,他得用草棍去扒。冷元要求东家给他一些粮食回家做饭吃,这样自己受罪可省点给孩子。可是得不到应允。因为长工吃不饱就没有力气干活了。他实在无法,就背人拿点剩饭回来。但很快被蒋殿人老婆发现了。曹冷元就早上的饭多吃些,中午拿上山去的干粮不吃,留给孩子。在地里紧张地劳动一天,中午不吃饭,那怎么受得了呵!冷元的腰杆早开始驼塌了,经过一饿一累,更加弯曲下来,强壮的体格开始衰弱了。有一次他在深山里挑起二百多斤的柴担,一起身就眼前发黑,空肚子直叫,他多需要啃几口冻硬的玉米粑粑呵!但他吞了口唾沫,用力压下食欲。那三个孩子的六只饥饿的眼睛,一刻也不能从父亲面前消失呀!
狂风暴雪无情地吹打,冷元又饥又冷,浑身哆嗦,艰难地在峻岭上负重行走。当走到牧牛山的顶端,那光秃秃的雪山宛如巨大的冰峰,冷元再也支持不住,腰欲折,腿欲断,脚下一滑,他急忙抱住扁担,一直滚跌到山沟底下。
昏迷了许久,冷元才从雪堆里挣扎起来。他跪在被雪快埋没了的山神庙跟前,悲怆地呼喊:“山神哪,山神!冷元多年在山里爬,和你交往,为你烧过香磕过头,你快睁睁眼,显显灵,叫我的孩子吃上口饭啊……”
神仙是“显了灵”,在东家门口等他的是皮袄裹着不见肉的蒋殿人老婆。她直骂到口干舌燥才走回炭火熊熊的房间里。
曹冷元僵直地站了好一会,泪水和胡须上的冰碴凝结在一起。此后,每顿饭都有了定额,多吃一口也没有。但他还是忍着饿,留中午的干粮给孩子。实际上他的胃已经饿坏,老吐酸水,吃饭也困难了。
曹冷元不知为神仙烧过多少香纸,磕过多少头,可是得不到一点荫赐。孩子生病无钱治,加上饿,又死去一个。他也病倒了,带着病去冯寡妇——那时她男人还没死——家里祈祷。这位交际广大、远近闻名的年轻巫婆,数说了一番,接过奉献的礼物,说曹冷元妻子死时烧纸少了,得罪了土地老爷,要他上那里去求救。
山河村东头的土地庙,长年香火不断。冷元借钱买了香纸,跪在大块石板砌起的小土地庙前,苦苦求道:“天老爷,地老爷!我一家大小活不下去啦,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再不能叫我剩下的两个孩子死啦!”
在风尘中,庙里居然响起嗡嗡的回声:“命苦命好,前世注定。尽忠效主,自有好报!”
冷元吓得满身出汗,起身就跑……此事传开,轰动远近乡里,在庙前搭起台子,为土地老爷唱了三天大戏。香、纸烧过的灰,把庙前庙后三亩多地都盖黑了。
惟有冯寡妇满心喜欢,在家对着镜子试着姘头蒋殿人为报答她这次的恩情——是她生计使他藏在庙里回冷元的话——送给她的大红绸子褂儿。
直到抗日战争的革命风暴吹起黄垒河的波澜,曹冷元才开始以疑惑的眼光去看神仙庙,对命运发生了怀疑。接着,一系列的变革接踵而来,一个比一个更有力地冲击着他的心胸。一九四二年,冷元把大儿子从地主的长工屋里找回来,带他去找着曹振德说:“大兄弟!我总算明白过来,穷人的神仙是共产党,不是土地老子、山神爷!叫吉福当八路军去吧!”……
“爹,爹!”一位穿戴新气的细皮白脸的青年媳妇,怀抱孩子走进院门,亲切地叫道。
冷元微吃一惊,从深沉的往事回忆中猛醒,起身招呼道:“哦,嫚子回来啦!爷爷看看大孙女,回去看姥姥,长胖了没有。”他接过孩子。娃娃睡着了。他喜欢地亲着,对儿媳妇说:“你怎么不在家多住几天,你爹妈好吗?”“好,都好!妈催俺早点回来,忙时候……”儿媳妇应着,惊讶地看着老人两颊上的泪水,“爹!你身子又不舒服?”“不,没有。”冷元转身往屋走着,急忙擦了把脸,“唉,我是看着这条使过三十年的扁担,想起那些苦日子来啦!哎,嫚子,快进屋歇歇吧!”
这女子是冷元二儿子吉禄的媳妇,名桂花,结婚一年多,头胎孩子前天满一百天,她是回娘家去了。
“爹,街上那末热闹,分那末多东西,咱得的什么呀?”进屋后,儿媳妇寻视着问道。
“人家要给的可不少,我没全要。东西有,就用;没有,也过得去。”冷元说着,见儿媳妇的脸色有些不高兴,就把孩子递给她,从怀里掏出那个粉红胶边的小圆镜,用衣袖擦了擦,笑着说:“咱们分的东西,除去那条扁担,我还特意给你领个镜子。喏,你看看。”
桂花一手接过,不满意地说:“唉,还是碎的!真可怜……”
“碎的也一样使唤,总比没有强嘛。”冷元安慰道,“嫚子,可别嫌少,这点也来得不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