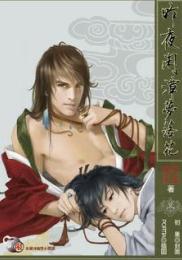落花之美-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亮晶晶的,形形色色,数不胜数。而且都极力向外扩张,成了真真正正的飘窗。时间稍长,就有红锈和着雨水顺墙而下,在浅色的外墙淌出长短不一的污痕。无论多漂亮多考究的公寓楼,也照样趴满这拖着一条条脏尾巴的铁格窗。恰如一身崭新的皮尔卡丹西装打了无数补丁,或少女身上漂亮的连衣裙哗一下子溅得满身泥巴,说有多么难堪就有多么难堪。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十七层竟也加了铁窗,问其故,他说一到十六层都加了铁窗,小偷会顺着铁窗爬进来的呀!得得,人人自危,户户铁窗,端的“铁窗生涯”!我当时住二楼,更是非加铁窗不可。虽然我刻意仿照日式木格拉窗样式并使之紧贴外墙,但终究不是优雅的拉窗木格而是大杀风景的钢筋铁棍。窗外若是白玉兰或木棉花紫荆花倒也罢了,无奈前面不远又是对面楼的铁窗。更恼人的是那铁窗里陈列的又不是盆花,而是本应羞答答晾在卫生间里的诸多小物件,花花绿绿,迎风招展。还有搭着滴脏水的地板拖布,甚至伸出扫帚拼命拍灰抖尘,飞飞扬扬,扑鼻而来。本来正诗兴大发文思泉涌伏案疾书之际,一眼瞥见这番场景,顿时卡住噎住。以至我终究未写出一首浪漫好诗一篇抒情美文,只能为提职称写干干巴巴的学术论文,心里好不气恼。总之我恨铁窗。恨自家的铁窗,恨别人的铁窗,恨全城的铁窗。我暗暗在心里发誓:若我做了市长,下的第一道市长令就是取消铁窗,让所有市民和整座城市终止“铁窗生涯”,何其快哉!
遗憾的是,没等我设法当上市长,我就北上来了青岛。所以来青岛,固然原因多多,但青岛极少有铁窗至少是一个原因。在青岛得到住房后我当然没安铁窗。向外望去,了无隔阻,蓝天寥廓,白云悠悠,颇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感。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那一窗梧桐。
于是想念那一窗梧桐。试问,一套室内装修和陈设不亚于“五星级”的高档公寓而窗口面对邻楼的防盗窗或一堵墙,一座简陋的平房而窗外是枝影婆娑的梧桐,你要哪个呢?我反正是要后者。当然,未必非一窗梧桐不可。也可以是一窗翠柳一窗槐花或一窗雪岭一窗松涛。古人诗句中的“窗外落晖红”更是令人心驰神往。不过,作为一介教书匠,实在没有经济实力买一座别墅坐拥如此窗外佳景,只能寄希望于退休了。我早想好了,退休第二天就坐长途公共汽车去乡间租一间茅屋。准确说来是租个窗口——春天窗口有一两株杏花间晃动喜鹊身影的杏树,夏天窗口有三五棵爬着牵牛花的向日葵,秋天窗口两三棵柿子树结满黄得透明的大柿子( 最好还有正偷吃柿子的小松鼠 ),冬天窗口但见无数小蝴蝶般的六角雪花款款雕就满树的雪挂。我就坐在一把藤椅上,手拿一杯清茶从早到晚望着窗口……如此越想越美,差点儿咬着被角笑出声来。
苦命的狗
也是因为狗年,我特别记起了我养过的一条狗。
那是一条极普通的狗。既没有美国总统布什爱犬的王者之尊,又没有杨志军笔下藏獒的勇武之姿。它实在太普通了,普通得只能说是普通的狗。
那也是我养过的惟一的狗。大体是我在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一期间养的。当然不是作为宠物养的——连宠物为何物都不晓得——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夜间需要有个动静壮胆,就养了一条看家狗。黑毛,眼睛上边各有一小块白毛,俗称四眼狗,我和弟弟给它取了个很威风的名字:虎虎。虎虎命苦,从来都吃不饱肚子,总是瘪着肚子在地上到处嗅来嗅去。这也怪不得我,怪不得我们家,因为我们也基本吃不饱肚子。父亲倒是挣工资,但在离家百里之外的一个公社工作,一个月四十七元五角,八口之家,且两地分居。有一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把家属下放农村,于是母亲和我们兄弟六个就像图钉一样被死死按在了那块半山区的沙土地上。穷得连口粮都领不回来,偶尔吃到一两块猪肉,香得我和弟弟差点儿抱着脑袋晕倒在地。虎虎当然就更可怜,能喝到一口刷锅水就大喜过望了。因为刷锅水要喂猪,年底卖猪换口粮。
狗不嫌家贫。虎虎从不到别人家去,就那么瘪着肚子看家护院。我和弟弟上山打柴它就跟着。冬天放学后,我和十来岁的大弟弟拖着我们叫爬犁的雪橇出门。过了铁道,过一条河,再过一片庄稼地和荒草甸,一直往南走去,进了山还要往里走很远才能找到干树枝。虎虎一路跟着我们,或前或后,或远或近,或快或慢,灰头灰脑,屁颠屁颠的。东北的雪一点儿都不含糊,动不动就深过膝,越往山里越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用绑在长竿上的钩刀钩树枝,弟弟跟在后面捡,拖回放爬犁的地方。钩得多了,我就跟弟弟一起拖。大多是从坡下往坡上拖。拖着拖着,天就麻麻黑了。空旷的原生杂木林,除了雪就是树,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偶尔传来的猫头鹰叫声和掠过树梢的寒风,什么声音也没有。虽说习惯了,但我和弟弟终究是孩子,还是有点怕。怕了就叫“虎虎——”。也怪,每次虎虎都不知从哪里飞一般应声而至,歪脑袋蹭我们的腿,伸舌头舔我们的手,甚至立起前肢亲我们的脸,眼神乖顺、温和而又凄惶空漠。我们搂住它的脖子,把冻僵的手伸到它脖子的毛里取暖。有时脚一滑,就一起在雪中滚下坡去。
下山天就更黑了。出了山,下坡没了,爬犁重了,我们望着远处自家如豆的灯光,像纤夫一样一步一挪。大概盼着回家吧,下山时虎虎一直颠颠跑在前面。跑出很远又跑回来,但见月光下白皑皑的雪地里一道黑影由远而近,三两下就蹿到跟前。那时候我觉得虎虎是那么矫健,真个虎虎生威。有时候显然跑到家了,又放心不下似的折回来接我们。这回不再远跑,摇晃着更瘪的肚子,几步一回头在前面带路……
后来不知为什么,它开始追鸡,追得鸡扑棱棱满院子跑。再后来的一天,当我从###里路外的学校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村里两三个大人正从门前山脚一棵歪脖子老柞树上往下放一条吊起的狗——虎虎!我没跑上去,没问什么,也没有回家,背着书包直接走去山的另一坡,靠一棵树蹲下,脸伏在双膝间一动不动。我一边默默流泪,一边想虎虎从来不曾鼓起的肚子,想它细瘦而温暖的脖颈,想它冰天雪地里朝我奔来的身姿和眼神……我的苦命的虎虎!
此后我再不养狗,虎虎成了我生命旅程中的一个惟一,一个定格。
刻录记忆的上家站
可以说,天上有多少星辰,中国版图上就有多少火车站。中国人没人不进火车站——始发站,中转站,终点站,快车站,慢车站,停车站,通过站,枢纽站,大站,小站。但真正属于自己的恐怕只有一个站,只有那个站才让自己梦绕魂萦情思绵绵。
我也有那样一个火车站。站很小,但有一个独特而温馨的名字:上家站。站的确太小了,一间放着三条长木椅的候车室,一间摆着两张桌子的办公室兼调度室,一个巴掌大的售票口,一个旧式店掌柜模样的站长常常亲自售票,售完少则几张多则一二十张票,人就不知去了哪里。没有冷若冰霜的检票口,没有插翅难飞的铁栅栏,没有人吆五喝六,没有人查验行李,没有罚款,没有没收,车来了就上,下车了就走,即便据说美妙无比的共产主义,我想也不过如此了。春天的清晨,小站笼罩在如一方白纱巾的淡淡的雾霭里;夏日的黄昏,小站那棵老榆树被夕阳镀上迷彩服般的金晖;秋天来了,小站匍匐在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和黄灿灿的谷浪中;冬季降临,小站如小雪人一样蹲在冰封雪飘银装素裹的大地上。
()
小站伸出四五条路。向西,一条荡漾着牛粪味儿的土马路在一丛丛马兰花和蒲公英的簇拥下伸向远方迤逦的火烧云;向北,一条小路很快爬上陡坡钻入绿得呛人而又喜人诱人的青纱帐;向南,沿着田埂走进屋后开满土豆花房前爬满黄瓜秧的村落;向东,一条羊肠小道拐过山脚下我家的院落和草房,再过一道壕沟一口水井和一座柴草垛,蜿蜒潜入一片光影斑驳的松林。早上,乡亲们沿着这四五条路聚来小站去县城赶集,有的挎着鸡蛋篓有的提着樱桃筐有的扛着羊崽猪娃,等车时间里互相说说笑笑问短问长。傍晚时分下车归来,三三两两低语着很快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小站也随之沉浸在寂寞、孤独与清冽的月华中。
小站刻录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的光盘,承载了我的迷惘、快乐和忧伤。我曾和弟弟从小站上车去三十里外的县城买二斤蛋糕,再步行四十里去看望年老的外婆;曾望着小站疾驰而过的直快列车梦想迟早自己也像车上的大人一样远走他乡;终于有一天自己怀揣一张入学通知书从小站扑向省城一座高等学府;四年后又怀揣一张报到证从小站远去香飘四季的南方。较之离开小站的得意和兴奋,更多时候是对回归小站的思念和渴望。上家站,一如其名,上家,回家,那里有我的家。有彩霞般美丽的杏花,有小灯笼般红艳的海棠,有烟花般璀璨的山楂,有香喷喷的烤玉米,有脆生生的嫩黄瓜。更有母亲的咸鸭蛋,有祖母的烧地瓜,以及她们脸上皱纹和白发……无论从一百里外的省城,还是从两千里外的京城,抑或数千里外的羊城,一路上所有火车站都是删节号,都是虚线。只有你——我的上家站才是惊叹号,才是句点。其他站都不是站,是站的只有你。其他站只有售货车争先恐后的叫卖声,只有你才有亲人望眼欲穿的期盼和淳朴真诚的笑脸。而离开时只有你才有亲人泣不成声的叮咛、偷偷揩去的泪花和一网兜热乎乎的熟鸡蛋……
起初离开你是那么欢喜那么激动,后来离开你是那么不忍那么感伤,而回到你身边的等待越来越难耐越来越漫长。你是中国以至世界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