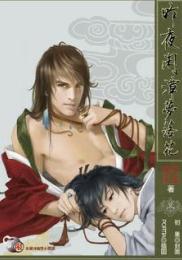落花之美-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语 》到川端康成无不如此。村上春树在我们眼中俨然另类,他本人也力图割断同传统日本文学的血缘关系而跟人家美国菲茨杰拉德大套近乎。其实他骨子里也还是个纯种日本人——作品中写得最到位最感人的还不是那份无可名状又沁入骨髓的无奈、寂寥和悲凉?还不是对已逝岁月和死亡的缅怀、伤感和咏叹?
又如诗人笔下的花。一千二百多年前日本编了一部诗集叫《 万叶集 》,那时候因受中国六朝隋唐文艺风尚的影响,咏花诗大多咏梅花,以致梅花成了花的代名词。而一百多年过后,梅花的“花王”地位渐渐由樱花取而代之。提起花即指樱花,“花见”( 赏花 )者,赏樱也。中国人爱梅,主要爱其生命力顽强——“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日本人爱樱则爱其生命力脆弱——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来去匆匆,暴开暴落,既爽且“酷”,于是有了“人中武士花中樱”之说。而且较之樱花盛开怒放云蒸霞蔚之时的灿烂,更中意把玩其随风飘零大势已去之际的凄婉。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在和歌俳句中借此抒发无常、落寞的人生况味,表达对生命本质在于衰亡的自觉与感慨。进而将其升华到审美层次——凋零美、凄清美、萧疏美、枯淡美、寂寞美、衰颓美,使得以悲为美或者说悲剧情结成为日本民族主要审美心理定势。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日本人的文学观、自然观、价值观、生死观,理解了许多从常识看来匪夷所思的现象。
所以,当年轻朋友问起我“日本美”美在哪里或者何谓“日本美”的时候,我不无极端地回答:美在落花,落花之美!
日本的乡下人(1)
一次同上海朋友聊天,我问上海话中骂人骂得最狠的是什么,他略一沉吟,缓缓道出三个字:乡下人。并解释说乡下人不专指地域或出身意义上的乡下人,若某人少见识欠修养,即使世居外滩,也可称之为乡下人。我听了,心想国人中到底上海人文化素质高,骂人都骂得较为斯文。若是齐鲁燕赵辽东,同样的意思就成了乡下佬、乡巴佬、老土、老屯、土老帽儿,甚至土老鳖,听了多叫人憋气。
乡下无疑指农村,乡下人即农村人。但在我的感觉中,二者又大有区别。“乡下”似乎很文学很温馨很撩人情思。提起乡下或乡间,脑海中很容易浮现出祖母的皱纹、房后的杏花、村头老柳树下的轱辘井、弥散在夕晖中的袅袅炊烟……而“农村”则往往同贫穷落后连在一起。尤其当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险”——“三农”问题足可令人闻风丧胆。
按理,中国的城里人无论如何都不该奚落乡下人。因为绝大部分城里人都来自乡下的某块田野,不少西装革履的工商精英和风流倜傥的社会名流脚上都曾沾有牛屎。况且历史上农民地位并不低。“士农工商”,农乃百业之首。“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娶年轻貌美的村姑当老婆绝非易事,只好讨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半老徐娘为妻,远远没有如今某些大款又是小秘又是二奶快活。翻开史书,农家子弟出入将相彪炳千古者比比皆是。我总怀疑农民政治地位的沦落始于上个世纪下半叶。一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管理制度就使乡下人一辈子忍辱负重大气不敢出,经济上除了交税纳贡也似乎大凡好事都不沾边。
这么着,来日本后我就较为留意这边的情形。首先留意的是其乡下人的社会地位。古时日本的乡下人不如中国。日本引进了中国的种种制度,惟独科举和宦官制度拒之门外。因此历史上日本一无阉党之乱的政治烦恼二无范进中举的乡里欢欣。朝廷幕府官职基本世袭,无“学而优则仕”一说,范进们再苦读也中不了什么,生在乡下就只能在乡下滚爬,不被武士试刀时一刀砍了脑袋就算不错了。可如今不同。如今乡下农民人数在总人口中虽已降至5%,但其政治能量足以干涉“朝政”——通过“农林族”国会议员左右国家政策。日本大米关税率高达490%,甚至发誓“一粒米也不进口”。为什么呢?因为“一粒米一张票”,农民手里攥着国会大选时的5%选票。这5%可小瞧不得,颇有影响的日本共产党的铁杆支持者才2%左右,再大些的政党有5%支持率也该弹冠相庆了。而乡下这5%是执政的自民党旱涝保收的“票田”,一投就是五六百万张,足可左右部分国会议员的沉浮进而影响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自民党对乡下人一直笑脸相迎小心侍候,根本不敢吹胡子瞪眼,同时赏以名目繁多的财政补贴( 不是名目繁多的税收和“乱摊派” )。乡下人的社会地位焉能不高?
其次留意的自然是生活景况。具体收入我不晓得,但看他们住的房子,我猜想肯定比城里人活得四肢舒展。我去过几位日本教授家,也去过国家公务员家做客,均属“中流”以上家庭。但住房面积都不宽敞。卧室多大我没窥看,而客厅一般都摆不下像样的沙发,书房更是小得转不开身。以致我暗暗幸灾乐祸:还是咱们社会主义制度好嘛,学问如何另当别论,至少我的书房可以背着手作沉思状来回踱步,房钱又没花几个。然而跟日本的乡下人就绝对比不得。中国乡间,村长村支书的房子一般是全村最好的,以这个标准衡量,日本普通农民的房子至少不在乡长甚至县长大人之下。绝大多数是二层楼,颜色或青灰或粉白或嫩黄,样式或传统或西洋或和洋结合,足可同青岛东部海滨的别墅或广州二沙头“高尚住宅区”里的独门小楼相媲美抑或过之。大门旁停的小汽车少则一辆多则三四辆,院里花草拥径,彩蝶翩翩,猫懒洋洋眯着眼睛晒太阳;院外一畦青葱,半亩瓜豆,几株柿树,数架葡萄,好一派和平气象。每次路过我都羡慕不已,两眼直勾勾看着发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日本的乡下人(2)
触景生情,难免想起东北乡下的姑母姑父。姑父原是骑兵连长,随四野大军从东北平原一路跃马扬刀呼啸南下,一直杀到海南岛,继而转战广西十万大山剿匪,可谓九死一生。后来自愿解甲归田。我看过他一身戎装的照片,何其雄姿英发,足可让如今的彩发靓女一见倾心一见倾身。而去年暑假我回去看望他的时候,除了当年骑马骑出的罗圈腿,一切都已荡然无存。他太穷困潦倒了!也是因为刚下过雨的关系,进得了村进不得他家的院——泥泞得无法下脚。仍是多少年前的土房,房顶苫的草有一块没一块的。院里是泥,屋里还是泥,屋里屋外全是泥,我的鞋也成了泥鞋。他告诉我正在建新房——县里因其当年战功特批了一块免费地皮——并带我去看。墙倒是砖的,但较小,又矮,相当寒碜,还没建完好像就已破旧了。建房本是喜事,但我一点也喜不起来。姑父似乎也喜不起来。喜从何来呢?地里的玉米一年才卖一千元挂个小零头。建房款有一半还是他这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几次厚着老脸捧一帽兜军功章跑几十里路去县政府讨来的。
话说回来,日本的乡下人固然令我羡慕,但日本的乡下风景看多了,总觉得其中缺少了什么。“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至少墟里烟没有了,家家改用液化气;“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村巅”,鸡已不存,狗仍在吠,但吠的已不是进村时需拿条柳条棍吓唬的大黄狗,而是脖子上系着小铃铛甚至身披花衣的小宠物狗了。叫声甜腻腻半事务性的,让人觉得有点滑稽。而悠然漫步之间突然觉察身后一辆本田“雅阁”正鼓着两个大白眼珠子闷声不响( 这种时候日本人绝不按喇叭 )逼你让路,更是扫人雅兴。是的,日本的乡下景物是少了什么——少了地道的乡下性,少了传统的田园牧歌情调。若陶渊明还活着,绝不至于放着好端端的七品知县不做而溜回这等非城非乡的地方荷什么锄种什么豆。
非我矫情,此刻我更怀念齐鲁及东北大地的乡下风光。那生龙活虎一浪浪扑向远方地平线的红高粱,那气宇轩昂齐刷刷腰插红缨白缨玉米棒的青纱帐,那点缀着一簇簇凤仙花香飘十里的香瓜地和地头的瓜窝棚,那长着车前草开着马兰花的田间土路,甚至随着炊烟飘往村外的牛粪味儿,都让我故国神游。作为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后代,其实这些才是我们的情感资源、悟性资源和文学艺术资源。难道我们也要学日本的样子让现代化这台水泥浇注机把大好田园风光弄得不伦不类吗?想到姑父,我衷心希望;想到后者,我一阵凄凉。呜呼,吾谁与归?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藏的美学与露的美学(1)
我总觉得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最大区别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藏”与“露”。
西方人讲究“露”。当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仍由皇帝或皇帝的老婆或皇帝的娘金口玉牙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人家西方就已经在两院议会里公开争得面红耳赤。说话时西方人也一口一个“I”直言不讳,而我们说到要紧处往往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或干脆来个“沉默是金”。再如艺术,洋人起初用汉白玉鼓捣雕塑,女子丰|乳肥臀,男子棒棒毕现。后来不再搬弄刀斧,索性在画布上涂抹——前不久去东京上野公园观看维多利亚王朝裸体画展,但见美女如云,到处玉体横陈千娇百媚,看得人心花怒放,心想皇帝老儿到了夜晚怕也不过如此了。那么中国如何呢?据说某朝以“深山藏古寺”为题公开招聘画家。应试者画的多是山林间探出一角飞檐,惟一人画一老和尚担水上山——不用说,此君得以录用。
当然也不是说东方的中国人老是这么藏而不露。远的不晓得,十年“文革”就彻底暴露一番。“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直闹得斗得全国沸沸扬扬昏天黑地。西方暴露的是四肢五体,顶多原形毕露,而我们连灵魂都裸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