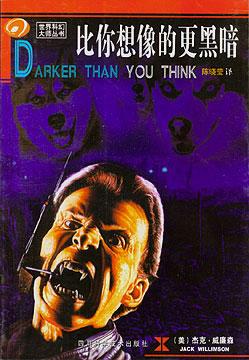红高粱家族-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爷爷说:“警备局的宋顺不是五兄弟的把兄弟吗?”
女人说:“你以为这种酒饭朋友靠得住是怎么的!青岛那边一出事,老娘这边就像坐在刀尖上过日子一样。”
“五兄弟不会供出你来,那小子牙关紧,当年在曹梦九那儿走过热鏊子的。”爷爷说。
“你来干什么?听说你打了日本的汽车队?”
“吃了大亏!我操死冷麻子他亲娘。”
“你别跟他们纠缠,那些人一个个鬼精蛤蟆眼的,你斗不过。”
爷爷从腰里摸出那包银洋,摔到桌子上,说:“给五百颗,红屁股眼的。”
“还红屁眼蓝屁眼,五兄弟一出事,我这儿早干啦,老娘又不会下枪子。”
“你少给我卖关子!这五十元你先花着,你想想,余占鳌亏待过你没有?”
“我的哥,”女人说,“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妹妹跟你又不是外人。”
“你别惹我生气!”爷爷冷冷地说。
“你们出不了城。”女人说。
“你就别管了。给五百颗大粒的,再给五十颗小粒的。”
那女人走到院子里听听动静,一会儿进了屋。她推开墙上的一扇暗门,拿出一盒子黄灿灿的手枪子弹。
爷爷找了一根袋子,装好子弹,捆在腰里,说:“走啦!”
女人拦住他,说:“你打算怎么走?”
爷爷说:“从火车站那儿,,爬过铁道去。”
女人说:“不行,那儿有炮楼,有探照灯,有狗,有岗哨。”
爷爷冷笑着:“试试看吧,不行就回来。”
爷爷和父亲沿着黑暗的巷子,溜到火车站附近,这里没有城墙。他们躲在铁匠铺子的墙角上,看着灯火通明的站台,站台上岗哨林立。爷爷对父亲耳语一声,扯着父亲向西回转。站房西边是一个露天货场,铁丝网从站房那儿一直拉到城墙头上。炮楼上的探照灯来来回回扫着,照得十几道铁轨耀眼的明亮。货场上竖着一根高竿,竿上亮着一盏牛蛋子形状的大电灯,绿荧荧的,照得万物变色。
狗 道。10
父亲趴在爷爷身边,看着铁丝网里边来回游动的岗哨。
一辆货车从西驰来,粗大的烟筒里喷着一簇簇强劲有力的暗红色火星子,车灯光像一道河,从远处哗哗地流过来、没被轧压的铁轨也嘎嘎吱吱地叫。
爷爷和父亲爬到铁丝网边上,用手掀动,想弄出个窟窿钻进去。铁丝绷得非常紧,一个铁蒺藜骨朵扎进了父亲的手掌。父亲低低地呻唤一声。
爷爷轻声问:“怎么啦?”
父亲轻声答:“扎手啦,爹。”
爷爷说:“过不去,回吧!”
父亲说:“有枪就好了。”
爷爷说:“有枪也出不去。”
父亲说:“有枪先把牛蛋子灯打碎!”
爷爷和父亲退到一个黑影里,爷爷摸起一块砖头,用力扔到铁道上。岗哨一声怪叫,开了一枪,探照灯立刻扫过来,刮风一样的机枪响声把父亲耳朵震得半聋,子弹头打得铁轨金星飞迸。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高密县城大集。虽是战乱年代,老百姓还得活着,活着就要吃穿,就要买卖。出城的进城的,摩肩接踵。早晨八点钟,一个名叫高荣的小伙子到县城北门上了岗,他严格盘查着进出的人。他觉得对面的日本兵非常不友好地看着自己。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赶着一只小山羊从城里往外走,老头脸色漆黑,眼睛发青;小孩子的脸色则发红,流汗,好象很紧张的样子。
来往行人很多,都在门口被卡住,高荣一丝不苟地盘问检查。
“到哪里去?”
“出城,回家!”老头说。
“不赶集啦?”
“赶完了,买了只羊快病死了,便宜。”
“你什么时候进的城?”
“昨下午就进了,住在亲戚家,一大早就买了羊。”
“现在到哪儿去?”
“出城,回家。”
“走吧。”
爷爷和父亲赶着那只小羊,出了城。小山羊肚子沉重,挪蹄艰难。爷爷用一根高粱秆子抽打着它的屁股,它咩咩地叫着,痛苦地扭动着尾巴,跑向通往高密东北乡的土路。
爷爷和父亲从墓碑下起出枪。
父亲说:“爹,把山羊放了吧?”
爷爷说:“不,赶着它走,赶回去杀了,咱爷俩过个中秋节。”
父亲和爷爷正晌午时赶到了村头,他们遥远地望到近年来修整过的环绕村庄的高高的黑土围子时,就听到了村里村外激烈的枪炮声。爷爷想起临去县城前村里尊长张若鲁先生的担忧,想起自己连续几天来的预感,知道这桩祸事终于降临了。他暗暗庆幸一早出县城的正确,虽然担风险,但毕竟赶上了,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
爷爷和父亲把半死不活的小山羊抱进高粱地。父亲动手拆开逢住羊腚眼的麻绳。父亲拆着麻绳,想着在那女人家往羊屁股里塞子弹的情景,五百五十发子弹,塞进小山羊的屁眼,把山羊肚子坠得下垂如弯月。父亲一路上直担心,一会儿担心子弹把羊肚子坠破,一会儿又担心山羊把子弹全部消化掉。
父亲撕开细麻绳,羊屁股像一朵梅花,猛然绽开,蓄积良久的羊屎豆子劈哩啪啦落下来。小山羊拉了一堆屎,瘫在了地上。父亲惊讶地说:“爹,坏啦,子弹都变成羊屎啦。”
爷爷提着羊角,使山羊直立起来,然后上上下下地墩着,光灿灿的子弹,从失去括约力的羊屁眼里,扑扑噜噜地冒出来。
爷爷和父亲捡起子弹,先压满枪膛,又装进口袋,也不顾山羊是死是活,从高粱地里,斜刺里往村子前边插过去。
鬼子已经把村庄团团包围,村子里硝烟弥漫,有几处黑色的烟火在升腾。父亲和爷爷先看到藏在高粱地里的小炮阵地。共有八门迫击炮,炮筒子半人多高,炮口一拳头粗细。二十多个穿土黄|色军衣的日本人正在放炮,一个精瘦的鬼子拿着小旗指挥着。每门炮后都有一个鬼子,劈着腿骑着小炮,双手拤着一个带翅膀的、明晃晃的小炮弹。瘦鬼子一劈小旗,鬼子们一齐松手,把炮弹掉进炮筒里。炮筒里一声响,炮口蹿出一股火,炮筒子往后一缩,一个明晃晃的东西早上了天,吱吱地叫着,落到围子里。围子里先冒起八股烟,接着传来八声合成一声的巨响。那些烟柱里,像开花一样溅着黑糊糊的东西。鬼子又放了一排炮弹。爷爷如梦中醒来,抡起匣枪,一枪就把那个挥小旗的日本人给放倒了。父亲看到子弹穿进瘦骨子干萝卜一样的脑壳里,才意识到:战斗开始了。他懵头胀脑地开了一枪,子弹打在迫击炮的底钣上,铮然一响,又向别处拐了弯。操炮的鬼子抓起枪,啪啪地打着,爷爷扯着父亲,钻着高粱空子溜了。
日本人和皇协军开始攻击了。皇协军在前,弯着腰,串着高粱空,漫天盖地地胡乱开着枪,日本兵跟在后边,腰也弯得很低。
好几挺机枪在高粱地里咕咕咕咕地叫着。围子上鸦雀无声。等到皇协军们冲到围子跟前时,围子里飞出了几十颗歪把子的手榴弹——爷爷不知道,这是若鲁老大爷集资去冷支队的兵工厂买回的次品手榴弹——手榴弹一齐爆炸,皇协军倒了几十个,没炸着的转身就跑,日本人也转身回跑。围子上蹦起几十个人,端着土枪土炮,急忙放了一阵,又赶紧缩下头。围子上又安静了。
后来,父亲和爷爷知道,村北、村东、村西,都进行着同样激烈、又同样具有荒唐色彩的战斗。
鬼子又开始打炮了,炮弹准确地打在那两扇包着铁皮的大门上,一炮一个洞,又一炮一个洞,咕咚咕咚一排炮,大门被炸得七零八碎,门口开了一个大洞。
爷爷和父亲又袭击了鬼子的炮兵。爷爷放了四枪,有两个鬼子兵倒了。父亲放了一枪。父亲瞄准的是一个骑着炮筒、双手拤着炮弹的鬼子。为了保险,父亲用双手攥着勃郎宁,瞄着鬼子宽宽的背搂了火,但父亲看到子弹钻进鬼子的腚眼里。鬼子一怔,身子前倾,压住炮口,呼隆一声巨响。父亲在地上弹跳几下,头上一片窣窣乱响。那个鬼子被拦腰打断,迫击炮炸了膛,一个滚烫的炮栓,飞了几十米,落在了父亲头前,差一点没把父亲砸死。
多少年后,父亲都忘不了这战果辉煌的一枪。
村围子的大门被炸碎,一队日本马兵,挥舞着马刀,向村子里冲去。父亲三分胆怯七分羡慕地看着那些漂亮英武的大洋马。乱糟糟的高粱棵子绊着马腿、擦着马脸,洋马烦恼地乱跳,很难跑快。马队冲到大门洞时,所有的马拥挤在一起,踢踢蹋蹋,像进马圈一样。从门楼两边,飞下来无数的铁耙木犁,碎砖烂瓦,大概还有滚烫的高粱稀饭,马兵们一个个鬼叫着捂住了头,那些洋马惊得扬蹄顿足,有的蹿进村庄,有的逃回来。
爷爷和父亲看到马兵进攻的惨像,脸上都绽开古怪的笑容。
爷爷和父亲的骚扰招来了成群结队的皇协军。后来马队也参加了清剿。有好几次,日本马刀在父亲头上闪着寒光劈下来,但都被高粱棵子挡住了。爷爷的头皮被一颗子弹犁开一条沟。密密匝匝的高粱救了爷爷和父亲的命。他们被追赶得像兔子一样贴着地皮窜。半下午的时候,爷爷和父亲跑到墨水河边。
爷爷和父亲清点了一下子弹,又钻进了高粱地。他们往前走了一里路左右。就听到前面一阵吼:同志们——冲啊——上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口号声过后,军号又嘀嘀哒哒吹起来。好象是两挺重机枪在高粱地里咕咕叫起来。
爷爷和父亲异常兴奋,扑着那重机枪声飞跑过去。到了跟前一看,人影没有一个,只见高粱棵子上拴着两只铁皮洋油桶,桶里有两挂鞭炮正在爆响。
军号声和口号声又在旁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来。
爷爷轻蔑地一笑,说:“土八路,就会来这一套。”
铁皮洋油桶咚咚响着,震得老熟的高粱粒子簌簌落下。


![[HP]贵族时代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2/24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