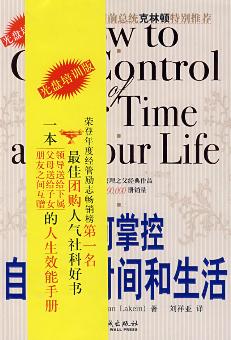和生命约会40周孕妇周记-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孕妇们喜欢扎堆,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可以交流各自不同的感受。直到我自己变成了孕妇,看着肚子一天天鼓胀起来,才知道了扎堆的理由。因为此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自卑。是的,走路时两腿发直;推门进屋时要先把肚子塞进去;两条胳膊用力甩着,否则就不能把自己沉重的身体运送到前方去……远远地看一个孕妇,是一个渐渐膨胀起来的皮球。不——我惨痛地发现,孕妇不是像诗人讴歌的那样美,反而是很丑!她们无力面对自己身体的丑态,尽量地不去想,却在张望他人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胆怯与自卑。所以,她们更喜欢和同类在一起!
那一天,我去吃饭,在人声鼎沸的餐厅里发现我的对面坐着两个沉默的人,只用手指和眼神交流。他们看到对方的一招一式都能心领神会,还各自发出灿烂的微笑。突然,我的心抖了一下:只有两个哑巴才能这么和谐地交流。如果一个是健全人,他一定会有负担,感觉自己是“屈尊”了,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平和自然。
像是现在。我的身旁走着的是肚子大小不一的孕妇。她们找到我,我找到她们,各不嫌弃地聊聊天,散散步,吃顿饭,倒也有说不上的愉快。突然想:难道,这种所谓的“平等”就是人类的共性?
我们很少会同情一个睡在纽约中央公园中的乞丐,但我们会同情一个甘肃难民。发达国家的乞丐也许在喝啤酒、吃鸡肉、骂总统,而我们的同乡也许连包谷面糊糊都喝不上。中国人找对象时所谓的“门当户对”,其实也是一种平衡心理的反应。找到同类,似乎是可以获得安全感的一种途径。
平衡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一种让人流泪的天真。现在,远方有战争,近处有空气污染,我却这样固执,要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管它刚发生过怎样惨烈的悲剧。孕妇就是这样固执——怀着一种发疯的力量,支撑着自己,要把这样一条路走下去。
我们说着说着,突然同时闭嘴,心照不宣地看了对方一眼。她那还没有出口的话,我已经懂了。她说:我害怕……其实,我说,我也害怕……在所有的害怕之中,有一种害怕是最厉害的——那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会突然死去。而我们都没有勇气将这种感受说出来,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已经心领神会了。我们的心都颤抖了一下——这一瞬间,我知道,这就是同类在一起的微妙!
而我,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眼泪,才能让我的丈夫明白——我现在的内心多么恐惧!而他,依然像个少年般,两袖清风地自如来去。他和我已经有了隔阂。尤其是,当我的肚子里那个孩子已经开始慢慢长大之时;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他亲热了;尤其是,他似乎对我的肉体产生了畏惧之感……我们其实已经很生份了。现在,他很难走进我的内心。而我也不想关心他的脑袋中想些什么。这样的时候,能够和我达成默契的,竟然是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孕妇。
我们走在一起。相互搀扶着,左右看着往来的车辆。我们都挺着肚子。一样的脚步蹒跚。面对结着冰的道路一样地犯着愁。终于,我们还是紧紧地拽在一起,一步步地走了过去。终于,我们走到了没有冰块的道路上。我们同时都舒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孕期就是一个漫长的夜晚。身处其中的女人几乎是处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个时候,我多么渴望看到身旁的同类。
甚至到了这样的情况:走在大街上,我可以很敏感地从人群中把孕妇分离出来。好像那些街道、树木、车流、商场都是衬托她的背景,而她和她所携带的肚子却是镜头中最清晰的那一部分。我看到她从人群中凸现了出来,茫然地走在自己的心事里。无论她走到哪里,我都能迅速地将她从人群中显影出来。围绕着她的一切,在我的眼中都变得模糊了。我观察她的肚子,以此判断她的难受程度。她看不到我的目光,而我,却像她的亲人般,替她设想着挺着肚子的不易。
日子 我成了一个惊叹号(4)
怀孕40天之后,我把头发剪成了短短的学生头。此前,我是满头的金丝卷发。突然从一个妖娆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中学生,我自己都感觉到不适应。用手摸摸后脑勺,短短的硬茬子直扎手。现在,我的肚子还不是很大,穿孕妇裤嫌早,可是一般的裤子又都穿不上,只好买了两条腰部肥大的牛仔裤。
看别的孕妇,有的穿老公的裤子和毛衣,有的穿一件粉红色的宽大马甲,有的头上还别着发针或头花,画着淡妆,各有各的一番情趣。她们并排走在了一起,说着笑着走着,也是一道风景。
有一次,在孕妇学校,我看到一个怀着双胞胎的母亲,穿一件大红毛衣,将肚子顶成了一个燃烧的锅。她是黑色的短发,因为出汗,又没有洗,耷拉在脸颊上一缕一缕的,可她却满心焦灼,为了那肚子里一上一下的孩子——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头发已经成了毡片!我不忍心看下去,索性就转过了头,看窗外的枯树。有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些满头黄发或者红发的女子。有的还是大波浪小波浪,不禁替她们担忧:希望那些化学药剂没有伤到她的孩子。
和我见面的这个孕妇倒很乖。把以前上过色的头发用发带扎起来,可以看到黑黑的新发已经长出了一指。头发是洗过的,很蓬松。浑身收拾得都很利索——这就好。我长舒一口气。
后来,我发现,孕妇的眼神是专注的,很聚光。神情是木然的,很痴情。孕妇是一个陷入深度恋爱的人。看自己之外的别人,都是灰尘。对距离自己一米之外的事物,都丧失了兴趣。孕妇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像是一群鸭子。一群约会的鸭子。
黄帽子
一顶帽子,黄|色的。是那种明亮的黄——皇帝喜欢的颜色。现在,它浸泡在柔软的绒线上,编织成了一顶软帽,裹在了我的头上。出门的时候,我给自己戴上了一顶黄帽子。不仅是为了取暖,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那璀璨的颜色让我成为一个亮点。当我脚步迟缓地行走在十字路口时,我希望那些司机能很远就看到我,减慢速度,从我的身旁绕行。
怀孕十三周后突然发现,自己不仅反应变得迟钝,而且还常常发愣。目光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僵直地呆在那里,像一个哲学家。后来,丁丁出生后,我常常会在他的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难道,表情也会遗传?或者,他也在思考?其实,我的大脑里一片漆黑。是像深夜广场那样的空旷漆黑。我无法自控自己的迟钝。我深深地陷落进一种担忧中:害怕自己有哪一点小小的疏忽,会波及到肚子里的孩子。
那一天逛商店,突然看到货架上有一顶黄帽子,马上想购买。不为别的,单为它那耀眼的颜色。这样的明黄,确实有种格外的纯粹。这种逼人的色调最终被皇帝选中,不是没有道理。而走下神坛的明黄|色,如今流落到民间一顶普通的帽子上,效果很是迷人。我试着戴上了它,镜中之人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精气神,似乎一下子长高了许多。
看了很多书,都写到孕妇对颜色极其敏感。一般的孕妇都喜欢柔和的粉红或者天蓝,讨厌浓黑或者血红,而我却独独对这明亮的黄|色有心动的感觉。
黄|色——从皇帝的宝座上流落坊间后,竟然有了另一种含义——超出颜色的含义——特指一种不道德。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是皇帝老儿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道德的黄,或者不道德的黄,其实都是黄。我喜欢阳光。喜欢黄|色。看到这顶毛绒绒的帽子,我更加喜欢!如果没有人为的道德介入,这种颜色多么温暖。这是从阳光中剥离出来的温暖颜色,是吉祥的金子的颜色,是戈壁晚霞辉煌的颜色。
记得一次和一群朋友去吃大盘鸡,回来时车驶在高速公路上,路旁是一群风力发电站。那时,正是夕阳西下,道路上的车辆都停了下来,大家都来看这难得一见的戈壁、夕阳、大风车。我们身旁停下来一辆豪华大巴。一群个子矮小的南方人纷纷手持摄像机,对准晚霞狂拍;另一辆吉普车上下来了一群年轻人,又是打灯又是撑支架,原来是要拍情侣照。镜头中是一对维吾尔青年,青春迫人,睫毛翻飞,天生一对。加上那辽阔的戈壁晚霞,高耸的白色风车,简直就是一副油画!而我也被那晚霞的金边所吸引,久久不愿将目光收回。
夕阳在云层中将最后的辉煌要收拢回去,红黄的光线将浓黑的云团边际烧成明亮的金黄。这种金黄是含了饱满质地的那种沉甸甸的黄。有种火焰燃烧到最后时不管不顾的味道。而开阔的戈壁像一个沉睡下去的大锅,我们只是一些沙砾,被风吹着,到处跑。那辉煌的金边只停留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几乎就几分钟,很快,金色消退而去。呼啦一声,夜幕就拉了下来,天空变成了深深的蓝黑色。
年轻的时候,发狂地喜欢黑色。感觉只有一身黑,才能技压群芳。而现在,突然喜欢起大红大紫大黄。有人说:你老了!老了吗?我对着镜子看自己: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自己。老,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现在,我已经要安心地接受“老”这个现实。
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多么排斥“生孩子”!想到好端端的生活中,要凭添一张吃饭的嘴,一个花钱的小机器,凭什么啊!啊——凭什么!那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她们都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老。没有老到足够接纳一个孩子,就最好不要生孩子。虽然,孩子是上帝的创造物,但当他通过你的身体时,你的一点拒绝就会让他自卑。看那些游来游去的小蝌蚪多么急切,它们向着一个环状透明体奋力游去,死命地用头互相撞击,你就知道什么是生命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日子 我成了一个惊叹号(5)
而现在,一想到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