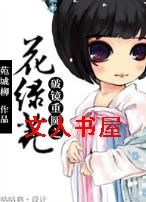髑髅之花-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卢瑟理笑得更加厉害。他的一只眼睛被剜去了,用仅存的另一只眼对抗着圣徒的俯视。“您是因为手刃前任教皇而成为圣者的人,因为血洗哥珊而被人民称作革新英雄的人,因为战斗和杀戮而跻身不朽的人。所以在我看来您只是一个会写字的屠夫,而战败者作为猪羊死在屠宰场上,本来也就天经地义。”
身后的卫士一脚踹倒了他,正要拔剑割掉他的舌头,贝鲁恒微微摇头,示意让他再说下去。
但卢瑟理再也没有开口。
开口的是他旁边,他原本倚靠着的那名男子。“求求您,大人,”卫士来拉他时,他突然发疯一样哀嚎起来,“求求您,饶了我,不要杀我!我不想死……不要杀我!”
贝鲁恒对他投以异常惊讶的眼神,而旁听席上,向来不苟言笑的梅瑞狄斯主教也挑起了唇角。“你认为还轮得到你说这话吗,哈茂?”
——哈茂?
云缇亚的笔刷地一扭,在名单上扯出一条歪歪斜斜的长线。
——哈茂?这个眼见着自己的部下被一批批处死,像吓傻了一样无动于衷,轮到自己又开始苦苦哀求的男人?让圣廷头疼不已的敌手,由圣徒亲自审判的叛军首领,某些人不惜牺牲全家也要袒护的对象,传闻中英勇正直的骑士,哈茂·格伦维尔?
“求求您,不要杀我……把我流放到边地,一辈子挖矿,做苦工,当奴隶,哪怕送我上前线都行……啊啊,我的财产,请您都拿去,我已经向仁慈的主父深切忏悔,甘愿捐献出自己的所有积蓄,求您饶恕我的愚行,放过我吧!”
“他根本没有钱。”主教哼了一声。“家徒四壁,那栋十几代以前留下来的破宅子折合起来也只值一两百辉币。”
“我有金块,用箱子装的,很多很多,都藏在只有我才找得到的地方。圣廷这两年不是军费很吃紧吗?”
“您别听他胡扯,他要有黄金,手下不至于临到决战还只穿破烂皮革。”
贝鲁恒的胸膛微微起落,似乎在叹息。这时卫队长面有难色地跑过来,原来卢瑟理在之前的刑讯中两条腿已经断了,根本站不住,绞刑没法继续。于是贝鲁恒站起来,叫卫士把自己的座椅抽走。“让他跪在这上面。”他说。
他走下审判席。不断叩头求饶的男人忽然挣脱卫士,沾满尘泥的手抓住他的衣裾。
“我知道奈拜七层楼那么高的琥珀船沉在哪里。我知道极北之地的黄昏古国埋藏着一城池的宝石。我知道茹丹深月妃主带到大陆来的财富现在为谁所有。”太长的额发和胡须掩盖了大半张脸,只有发红的鼻翼狂热翕动。“看在我自首忏悔的份上,看在我们两人的交情上,求求您,高抬贵手。我愿用我所有的一切,交换这条微不足道的性命……”
“他崩溃了。”梅瑞狄斯下了结论。
贝鲁恒垂下目光注视着这个他熟识已久的人,有一种极为深闳的悲哀在他眼里无声地生长。“我给你一个机会,”他轻而清晰地说,“你愿意接受神断吗?”
哈茂蜷曲成一团的身躯猛地抽搐了一下。
主教平板的脸上皱起一道古怪的神情,有点像是笑,但仿佛笑容本身在这里也是只配得到嘲讽的东西。
“这个人连死的勇气都没有,又哪来的胆量和法庭的神裁武士战斗呢?圣者,这儿当然是全遵照您的意思——可是您不觉得这样实在太过荒谬么?”
贝鲁恒只是望着哈茂。
“不……”男人瑟缩着,将头颅藏在圣徒的影子里,“……我做不到。”
贝鲁恒轻轻合上双眼,许久后才缓慢睁开。那种无上渺远的悲哀消失了,好像从始至终不曾存在过。“好吧。”这一次,他不再坚持己见。“你可以再多活几天,直到被解送回哥珊。不过哈茂,到那时,我想你会怀念我今日的慈悲。”
“谢谢大人,”哈茂·格伦维尔扯着嗓子喊道,“谢谢大人……”云缇亚好半天才听出他声音里那剧烈的颤抖是在狂笑。极度不适的感觉从胃里一直向咽喉涌来,而阿玛刻则在一边攥紧了拳头。她走上前去,对着哈茂那被头发胡子盖得乱七八糟的脸就是一脚,男人顿时在地上鬼哭狼嚎地翻滚起来。云缇亚皱着眉扭开视线——
他瞥见了卢瑟理的眼神。
没有愤怒,没有痛苦。没有悲悯。
无比的平静。脖上套着绞索、跪在座椅上的谋士,在注视自己痛哭求饶的主君时,竟有一丝坦然而从容的微笑。
这是让无辜的平民因此牺牲血亲的男人——
这是让数以千计的部属死而不悔的男人——
那个黑色的异族神祇在云缇亚胸中再次尖啸起来。
他匆匆抓起笔,胡乱一划,把直到哈茂之前的所有名字都一把勾掉。“请允我先行告退。”他对贝鲁恒说。后者没有阻止。小步快跑穿过重重围拥的人群,交织着惊讶、鄙夷、震怒的脸孔在身旁拥挤不堪。一波一波的高呼下,他背后哈茂的哀叫很快被冲刷得模糊一片:“哎呀……好痛!这位大人,求求您,别再打了……饶了我吧……”
恍惚间人群最激烈的涡流中心绽开一道极细极轻微的声响,仿佛一个水泡破裂,一朵花颓然凋谢,一个震雷炸开后最安静的小小瞬间,他不能分辨那到底是叹息,还是因绝望而极力压抑的深长啜泣。
钟声结束了这一切。
云缇亚一直跑到僻静无人的巷子里,伏在水沟边上抠着喉咙呕吐,可终究没能吐出任何东西。直起身来的那一刻,忽察觉到有人在沉默地凝视他。
他蓦然转头。
是之前在巷尾看到的那个僧侣。站在他视野的边沿,兜帽的阴影里露出尖削有力的下颔。隔得太远,纵使云缇亚眼力极好,也无法肯定那苍白的唇线是不是挑着语焉未详的笑意。
他追上去,想与他攀谈,但马上失去了僧侣的踪影。巷道曲深,只剩下茹丹人独自在这里,隐隐地,倾听着钟鸣从无数个黑暗的尽头折返而来的回声。
两天的时间足够把上百具尸体清理干净。在贝鲁恒为自己翻译的第三本东方诗集写下跋语的那个黄昏,无数只乌鸦如黑云降临旺达,仿佛听了冥冥中某个预言,来赴这场盛大的饕餮。那场景让他想起传说中的鹭谷,当曦红之星将天际染成血色,几乎大半个北地的夜鹭都群集而来,像远古诸贤的魂灵一样掠过村庄上空,飞往纯白之城哥珊的方向。后来有人说,那预兆着一位圣人的诞生。
是夜,旺达的监狱长匆匆跑来,向圣者报告了一些情况。贝鲁恒平静地安排下去。之后,他没有继续睡,而是在床上坐到天明,去了关押哈茂的囚牢。
……铁铸的牢门才推开一条缝,顿时一股浊恶气味迎面扑来,连油炬的火光都为之怯缩了那么一个瞬间。
男人瘫在墙角阴影里的躯体下意识地抽动。
“饶了我。”他嘶声唤道。
狱卒向贝鲁恒微微欠身。“他只会说这么一句。”
贝鲁恒让他下去。火炬慢条斯理燃烧,无边的阴冷湿暗簇拥在这昏光周围,没有随从,没有看守,没有其他犯人,年轻圣徒垂眼望着沦为阶下囚的旧识,鲜红的额印闪灼发亮。
“不要再做戏了,哈茂。这里只有你我两个。”
哈茂缓缓地抬起头来。
肮脏蓬乱的头发盖住他眼睛,却挡不住那里逐渐明锐起来的、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神光。两天前审判庭上那个彻底溃散崩碎的人形,正一点点组建成完整的本来面目。“……哦,”他的胡须动了动,“您还真是穷极无聊。”
“无聊的人是你。”贝鲁恒说。“你打算用那种方式戏弄我?还是说扮演的本身令你乐在其中?”
“您纡尊降贵到这儿来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啊,不,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亲爱的大人——”他从不称他为“圣者”,即便庭审时那场戏码也是如此,“怎么啦?您只是想向我证明这双不朽之眼是多么明察秋毫吗?”
贝鲁恒素无波澜的目光静静停留在死囚身上。“哈茂,”他低声说,“我很遗憾……”
“——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一只破碗向他飞来。圣徒没有闪躲。碗里的秽物溅上袍裾,而他仿佛浑无知觉。
哈茂笑了,牙齿雪白。“听着,贝鲁恒,”毫不避讳地直呼面前这个人的名字,“除非你现在就向我施展神迹,让病者康复,让死者苏生,让斩首的斧子柄上开出鲜花,让外面遍地血水都化作牛奶和甘露——否则就别这样看着我,别用这种高高在上泰然自若的眼神看着我!”
他知道这番话不会收到任何效果。
那无边无底,无法用言辞来概述的悲哀再次从殷红的瞳孔中蔓延开来。没有人能忍受贝鲁恒的注视,没有人能抵抗,大地沦陷,鲜血滚涌的海洋阒静无声,瞬息间将万物没顶。“既然这样,”轻而又轻的声音如同海面上浮沫徊旋,“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空旷寂寥的镇广场上,哈茂看到了贝鲁恒所说的人。
确切地说,已经是一具尸体。
尚未干枯的身躯吊在绞架上僵直晃动。乌鸦围着他,见有人靠近,呼啦一下全都散去,镇长微微谢顶的圆胖头颅耷拉下来,把他被啄得空空洞洞的眼眶藏在了黑影当中。
哈茂仰头望了他许久。
“很好。”他一字一顿。“这就是你对我的惩罚。”
“他被处死的原因不是隐瞒你的行踪,而是杀人。”
哈茂没有说话。
“昨天夜里,他听说了你在审判庭上的表现,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便和疯了一般,用预先磨尖的汤匙刺伤看守,抢过刀将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子全都杀死,连剩下的那个女儿,也被砍伤了一只手。”贝鲁恒顿了顿,那一瞬间,漫长的沉默。
“他只是不想再活下去。所以,我满足他。”
哈茂的拳头在镣铐里发出指节挤压的咯咯声。
贝鲁恒忧伤地望着绞架,而当他的眼神收回来,转向哈茂时,却变成了一种不冷不热的哂笑。“你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想断绝没落网的部下营救你的念头?或者只是嘲讽我,向我证明你的勇气,证明放弃尊严比坦然就死更需要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