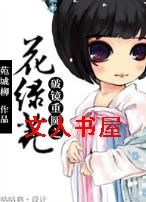髑髅之花-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果然不出您所料,圣者……”躺椅边上的另一人轻轻冷笑,“细作这么快就现原形了呢。”
云缇亚盯着贝鲁恒椅边那个人,对方则用若无其事的笑意来回应他的冷眼。
海因里希。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他忘了这是那天被公开鞭打后第二次见到贝鲁恒,“我军的私事用不着一个降卒来插嘴。”
“他不是外人,”圣徒说,“至少这件事上不是。”
离进驻冬泉要塞不过十来天,贝鲁恒外貌变化之大远超过云缇亚想象。他整个人都像被菟丝紧缚的树木一样迅速憔悴下去,面颊和颈部开始浮肿,身子却瘦了一圈,头发也和肤色一样黯淡无光。但他的额印越加鲜亮,在他的眼睛里,云缇亚发现那举重若轻的魄力并没有离弃他。
有人端来一盆凉水喷在珀萨脸上,令他慢慢苏醒过来。原本英俊的面孔此时满是泥污和瘀伤,无比狼狈,他抬头环视着在场众人,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关于在第六军里安插眼线的事,吉耶梅茨将军并没有透露给我们这些下属,但既往所有军件都有抄本秘密备案。”海因里希当着贝鲁恒的面打开一只黑色小匣,从近十层蜡封的皮函中取出一张薄纸,字迹随性,像是封私信。
“念。”贝鲁恒说。
降将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起来,他的声音如同剑锋振动,冰冷的气流贴上房间里每个人的喉骨。云缇亚只觉芒刺在背,他并不知道这就是贝鲁恒曾有意拿给珀萨看的那封,信里充满了对参谋才干的赞扬,以及对圣徒绵里藏针的善意提醒,不管怎样看,这离间都幼稚得像是出自五岁儿童手笔,但此刻听在耳中,渐渐浸润出一股别样的寒意,刺骨而令人窒息。
“是我叫阿玛刻去偷印信的,”珀萨忽然开口,“这事都是我一手策划,她不知道内情,更不用扯上别人。做过的事我自然会承认,至于没做过的,我想有人比我更清楚。”
“珀萨大人不可能是细作。”萧恩说。他言语仍和往常一样,掷地有声却波澜不惊,“就算今天他做出什么不可饶恕的行为,但他之前对您的忠心,大家都看在眼里,当初在鹭谷起兵,难道不是他替您铺路,说服龚古尔等三位大人?第六军能走到今天,他的付出仅仅在您之下,没道理轻易就——”
“有心从中渔利的人,总是很乐意先搅出什么乱子来吧?”海因里希微笑着转向贝鲁恒。“啊啊,只是胡乱揣测罢了,我不太了解具体状况,也对不了质——不过您可以考虑交给专门负责录取口供的人员,让他们来处理?珀萨大人为了自己的清白,必定会全力配合的。”
云缇亚手脚一阵发冷。他太清楚海因里希的手段,以珀萨的性子,宁愿一头撞死也决计受不了那屈辱。瞥了一眼贝鲁恒,后者似在托颔深思,双瞳里却有精光闪现。他知道圣徒正在下决定。
早已在脑中徘徊千百遍的话语涌到舌尖,当它真正凝固、呼之欲出时,形体却突然又如此怪诞,不可言喻、难以捉摸。
但他无法再迟疑了。
他跪了下去。有一股未知的强大力量在压迫他的双肩。“圣者。”他叫道。
贝鲁恒直起身,有点讶异地望过来。
云缇亚在心里召唤着那语言。他怕自己再耽搁片刻,许久以前酿造起来的勇气就会像生命舍弃弥留者的肉体那般舍弃他。“……里通外敌的人是我。”
当这句话离开他的喉咙时,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在四周。云缇亚双膝跪倒,如面对着一尊具态化的神祇那样全身匍匐,额头紧贴地面,此前他的余光匆匆掠过珀萨的脸,那张珊瑚雕塑似的面孔满布惊愕。这是他第一次在珀萨脸上看到这种表情。
母亲血泊中的笑容,透着微光的岩洞,阿玛刻的哭泣——所有被他甩在身后、却仍跟随着他的事物,这一刻终于失去了全部的质感和重量,纸那么薄,羽毛那么轻,在风里静静燃烧凋落,化为乌有。
“按照律令被处刑的,应当是我。”
贝鲁恒站了起来。
“说,”他命令道,“继续说!”
“您明白珀萨根本不会是那种人,然而需要一个对象来承担这一切。珀萨偷取印信是事实,我看管不力也是事实。如果有人要为此受惩处,要背负上叛徒的罪名以稳定军心,就由我来做!少一个云缇亚,不会对大局造成任何影响,但珀萨是军中的元老,是您最倚仗的人,没有他,第六军的命运或许会整个改写!留下他的命,岂不是划算得多吗?”
熟极而流的台词。相信我,他对阿玛刻说,你们不会有事,我保证。
生死对他来说无足轻重。他曾轻掷生命,也曾想过为了某个人活下去,但这些在贝鲁恒的怒火面前都成了多么可笑的事情。当圣徒当着所有人的面用马鞭狠狠抽打他的时候,他看见对方眼里毫不掩饰的杀意。终于他活了下来,而人们将其称为慈悲。
他用母亲的挚友、茹丹之主、自己最尊敬的人的头颅所换来的慈悲。
“你应该明白的,”沉寂的另一端,是贝鲁恒在冷笑,“出卖机密,假造军件篡权,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云缇亚感到某个在虚空中盘旋的阴影正将全部重量压到了他的脊背上。他不能喊叫,甚至不能战栗。
“……磔刑。”他极轻微,但极清晰地说。
所有分裂肢体的死刑统称为磔刑,军队里通常采用的是轮磔,即用铁锤将受刑者的四肢关节和骨骼逐一砸碎,然后将其手脚扭曲,绑到一个大型木轮的辐条上,悬挂示众,任其被日晒雨淋,鸟兽啄食,直到慢慢咽气。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刽子手会被允许仁慈地对着受刑者的胸口或头颅来上一击,尽早结束他的性命,但更多时候,人会挂在那上面喘息数天,死亡成了一种漫长而遥不可及的慷慨施与。
“即便这样,你依然要去替死吗?”
你一直在逃避,云缇亚。你只是在重复你母亲的道路。因为这血河太深太宽,你逾越不过,而你已摈弃一切,无法回头。
你只是跟着某个幻像行走,并相信它能实现你所有的心愿。
你只是用信念麻痹自己,用坚持迷惑自己,用决绝来说服自己能贯彻始终,至死不渝。
多么可笑。
“……是。”云缇亚说。
这答复脱口而出,任何其他的言语瞬间化作了灰雾和齑粉。有一双深杳冷寂的眼睛在黑暗里凝望着他,流淌出无声的痛楚来,只是一刹那,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这凝望下也开始变轻,和那些往事一起被风吹散了,火焰飘忽,往各自不同的轨道坠去,缓缓地黯然熄灭。
他听见贝鲁恒的袍裾拂过他身边,却没有作停留。
“我对你说过,”圣徒在珀萨面前俯下来,扶住他被绳索反绑的双臂,“我俩之间的交易早在我和圣廷兵戎相见的那一刻就结束了。”
珀萨抬头与他对视。“是,”他笑了,“我知道。”
“你本可不至于此。”
“第六军不只属于你。你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光辉,这些都不仅仅属于你一个人。你把我从烂泥里拉出来,让我为你效命,让我亲手一点点构筑起它们,为它们的日益盛大而喜悦;你让我认为,我这辈子还能干成一件有价值的事——可你现在要把它们都毁了,你对我说‘交易结束’,然后将我九年来的所有努力都弃若敝履!不,贝鲁恒……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毁掉我最珍重的东西。”珀萨紧盯着他,眼里泛出犀利的光,“就算重来一次,重来无数次,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做出和今天一样的选择。”
“不值得。”贝鲁恒说。
珀萨再度笑了起来。“如果我后悔了,那才叫不值得,”他声音有些颤抖,但那不是寒战,而像是剑在剑鞘内的振动,“如果我就此放弃,那我以往的一切决定,一切付出,都将失去任何意义……”
贝鲁恒徐徐起身。
他的脸陷在光与影明晰的交界中,一半昏暗一半亮得刺人,没人能看清他的眼神。
“我满足你,珀萨,”圣徒说,“磔刑,立刻执行。”
他转过去,瞥了一眼云缇亚。后者仍然保持着跪伏姿势,纹丝不动,整个身子僵硬得像块岩石。
房门打开了。片刻后,要塞内部开始沸滚。士兵们在各层跑动,嘈杂声从上面一直汇流到底下的大厅,有人在怒骂,有人则失口惊呼,监刑的亲卫宣布着什么,可这反而被一片泥泞似的纷乱淹了下去。忽然这一切都有了极短暂的一瞬屏息,死寂之中,撕裂出一声野兽般凄厉尖哑的惨叫。
云缇亚永远不会忘记那声音。
那是阿玛刻的惨叫。
他近乎蜷缩地匍匐着,试图将身体全部缩入某个并不存在的影子里。直到他发觉贝鲁恒就站在他身前。一种无以形容的恐惧吞噬了他。这并非对死亡的恐惧,他曾经以为只要一个人不怕死,就再也没有可害怕的东西。但这种恐惧仿佛流沙,牢牢将他向深处脱陷,最终令他化为一粒渺小的沙砾,被无垠荒漠席卷抹灭,与恐惧的本身融为一体。
“……云缇亚。”圣徒叫道。
云缇亚没有动。
“你太天真了。”
贝鲁恒走了出去。血的阴影在要塞里汩汩弥散开来。
******
有时候清楚自己爱上某人,就彷如一颗露珠从凝结到坠落,由始至终的完满,都包含于如此短暂的时间。
当她什么都未发觉时,她是海寇的女儿,佣兵团蛮勇彪悍的狂战士,戴着镶牛角的护鼻盔,穿毛皮衬里的锁子甲,在篝火旁一边歌唱,一边用烤肉擦拭皮靴;而待她恍然明白过来,已经是血天使旗下飒爽美丽的女将领,在部队的簇拥下骑行穿过山原,风掠过她的脸,从海洋奔向大地。
她一直觉得自己和那风一样,不可能永远呆在一个地方,这世上只有它的道路,没有归宿。
她所在的佣兵团解散了。同伴还活着的天各一方。她背着木盾准备到北方的冰海去寻找永不沉没的龙船,武圣徒的军队经过她的旅途。马背上黑衣的年轻人攫取了她视线,她兴致勃勃朝他喊叫,而他面容清冷,目不斜视。
当晚她